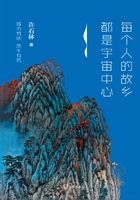当我掘开唐古拉山的腹地,从历史的深处挖出掩埋了近半个世纪的一段事时,它还是那么鲜活,醇香!
——题记
长年在世界屋脊青藏公路上奔驰的几支汽车团队,都毫不例外地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运输线。
我所在的那个汽车团,组建于解放战争的枪炮声中。全国解放后赴朝参战,归国后落脚华北,执行国防施工任务。1955年奉命上高原,当时上级的承诺是:临时执勤三个月,再返回原驻地。
承诺经常有不能兑现的时候。如今已经是四十三年了,他们仍然在青藏线上奔驰着。从三个月到四十三年,把多少白皮嫩肉的新兵熬炼成了脸膛黑红的“老高原”。
在我们团里,几乎人人都会说出这样一首顺口溜:
抗过美,援过朝,东海岸边洗过澡,天安门前出过操,唐古拉山抛过锚。
“唐古拉山抛过锚”,这也值得炫耀?值得骄傲?是的,值得骄傲!值得大书特书!
那一次在雪山上抛锚整整二十五昼夜呀……
这是高原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季——1956年12月29日,我们汽车团运载一批进藏物资,由副团长张功和一营营长张洪声带领从西宁出发,直奔拉萨。
这支车队共75台汽车,装载390吨战备物资,驾驶员、助手再加上跟车干部共204人。
车队出发后的第三天,他们在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兵站送走了1956年,迎来了1957年元旦。新年的第一天,空气清冷,红日高悬,大地铺满金灿灿的朝阳。车队告别晨曦中的都兰,夹裹着雪水河的寒气,向着前方行驶。
公路边半裸的河床在车轮下渐渐变瘦。
驾驶室里的日历被一张张碾碎。
元月10日。车队从唐古拉山下的温泉兵站出发。当日的行车计划是:行程152公里,晚上投宿于山那边西藏的安多买马兵站。
这一天的全部路程都在唐古拉山上。没想到,车队出发后只行驶了四五十公里,天空就突然飘起了雪花。最初谁也没有把下雪当回事,照样行车。不料,那雪越下越大,风也刮得一阵紧似一阵。事后有人问了气象站,得知这风有十级左右。暴风卷着雪片、沙石,像棉絮团块一般飞旋在车前车后,车窗玻璃被砸得叮咣乱响。公路全部被一道道雪墙淹没,驾驶员什么也看不见了。
糟糕!车队遇到了百年罕见的暴风雪,被迫停驶,东歪着一辆,西窝着一台,车辆哩哩啦啦地在唐古拉山的坡地上摆了三四公里长。
此处,海拔5000米,气温大约在零下50度。
车队面临着一场估不透的严峻考验……
山上的积雪大部分没及膝上,雪厚的地方达一米左右。所有沟坎、山谷、悬崖,都被雪填平了,人和汽车如果贸然行动,一旦掉进雪窝就别打算出来。
张洪声顶着暴风,从车队的头走到尾,看到的情况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几乎人人都得了高山反应症,严重者靠着驾驶室连半步也不想动。大部分人则呆立车前,没有了主张,等待着领导发话。
张洪声艰难地走上一个积着厚雪的高坎,双手卷成喇叭简,放在嘴边,对大家说:
“除了重病号留下看车外,其他人都自找工具,挖雪开路!”
于是,一场近乎原始的清除雪障的劳动开始了;有的用铁锹铲雪,有的用脸盆舀雪,有的用撬捧打雪,有的用汽车挡地板推雪,还有的索性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扒雪……
雪很厚。路更长。
战士们的忧虑挂满山间。
两天过去了,车队才往前挪动了一公里。有的车已经耗完油,停驶了。
张洪声作了最坏的打算:一旦突围不出去,就让大部分汽车熄火,把油料集中到一台车上,想法开下山到兵站去求救。
路,在指战员们吭哧吭哧的粗声喘气中,继续缓慢地延伸……
正是在这个时刻。一营教导员张广林坐的救济车拉着一车柴油赶上来了。原来10日早晨车队从温泉出发后,迟了一个小时才上路的张广林发现山上弥漫起了大雪,他估计会有麻烦事出现,便从兵站装了一车油。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大雪把车队捂在山上,这车油肯定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如果车队安全无事,把油卸到山上道班就是了。张洪声见了张广林,一把攥住他的手,说:“你拉来的是救命油呀!”
夜里,黑乎乎的世界屋脊格外阴森,寒心的暴风不知从荒野的什么地方窜出来,释放出狼嚎鬼叫的怒吼。
火,浸入骨髓的寒气只有火才能驱逐走。
战士们翻箱倒柜地搜罗到一些劈柴和擦车布,又扒开路边的积雪拣了点牦牛粪什么的,堆放在一起,泼上废油,点燃起一堆篝火。
这时候,火是雪山的心脏。有了它,兵们就有了家的感觉,就有了方向,有了信心!
熊熊燃烧的篝火,烧红了唐古拉山!
张洪声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不能生这么多的火!于是他逐车地对驾驶员们说:灭掉一些火吧,太浪费了!
大家都忍耐一点,尽量往一堆挤,这样可以省下些柴禾。我们在山上熬的日子还不知有多长呢!
篝火烧完了一个黑夜,又一个黑夜……
滞留山上的第五天,吃的东西没有了,同志们一个个都蔫头耷脑,十分饥累。早上起来后,驾驶员们陆陆续续往不远处的道班走去,道班卖稀饭,一碗一元钱。那时候的一元钱呀,几乎等于一周的伙食费!但是他们还得硬着头皮去买,填饱肚子是大事!车队有限量,只许每人一次喝一碗稀饭,驾驶员小李喝了一碗稀饭,只填了那空肚子的一个角,根本不解决问题。他又去到别处找吃的了,哪儿能有什么东西可以填饱他空空的胃囊?他不知道。他漫无边际,毫无目的地走着。如果能遇到一只被暴风击落的飞鸟;如果能碰上一只被酷寒冻死的地鼠;如果能拣到一碗牧人遗弃的残汤剩菜……他相信他会像在老家过年时吃饺子那样香香甜甜地饱餐一顿。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暴风,只有狂雪。
小李满怀希望的、却又一次次失望地在雪山上走着,转着……
突然,他发现前面山洼里有一缕烟雾在清冷的天地间弯弯曲曲地飘散着。他的心里一热,有烟必有人!好些天了,他除了和车队的战友们以及那四五个道班工人照面外,就再没有见过什么人。
心里好憋闷呀!现在也许要见到他上山以来碰到的第一个“外星人”了,脚步不由自主地迈得快捷了。
小李来到山洼里一看,原来这里停放着两辆地方的汽车,两个司机蹲在一个避风的坑洼处,用脸盆熬着面糊糊。他们先发现了小李,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点儿的司机搭话了:
“解放军同志,我们的车抛锚了,缺吃少穿,每天只能熬点面糊糊打发日子。”
小李指着远处的山头说:“我们的整个车队都抛锚,雪不停路不开,我们就无法下山!”
两个地方司机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就把面糊糊给小李分了半盆。小李推辞不接,那个年龄大点儿的司机硬把脸盆塞到小李怀里:“都是抛锚受罪的人,谁跟谁呀!这点面糊糊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去只能给你和同志们塞牙缝!”
小李端着半脸盆面糊糊回到车队前,驾驶员们虽然饥肠辘辘,可是你推他让,谁也不肯吃一口……
车队的处境越来越严峻,吃的问题需要立马解决,车辆的油料眼看就要断线,有些战士的手脚也开始冻坏了……张洪声心急如焚,他对张功说:
“我们必须派人下山设法与西藏军区或兰州军区取得联系,不然我们会冻死饿死在山上的!”
张功也满脸惆怅地说:
“派谁去呢?哪个驾驶员有这个能耐和胆量?”
“我已经考虑好了一个人选。”
张洪声说的这个人选就是一连三排副排长王满洲。
王满洲给张营长最初留下好印象是在团队上高原执行第一趟任务途中。当时,车队行驶到柴达木盆地的橡皮山下,途中小憩,张营长听见前面荡起洪亮的号子声,那声音像钻天杨一样,直上青天。他上前一看,只见一个粗壮结实的汉子正在组织战士们推车上坡。战士们每把车往前推动一步,就用三角木顶上车轮。再推,再顶……直至一步一步把车逼上坡顶。推车的动作完全合着那汉子号子声的节拍,铿锵,整齐,显得他的指挥格外气派,有力。事后,张营长一打听,方知那汉子叫王满洲。后来,张营长又多次与王满洲接触,更了解他,知道他在战士们中间之所以有很高的威信,缘于他高超的驾驶技术,是全连的技术能手。
这时,张洪声对副团长说:“我考虑再三,把下山联络的任务交给王满洲。他会出色地完成任务。”
随后,张功找到王满洲,告诉他:“我坐你的车,咱们一起下山到安多兵站去。”
王满洲挑了一台技术状况最好的车,加足油,开着下山了。
不见鹰飞翔。
雪峰把车轮托得很高很高。
雪山上没有路,只隐隐约约有一行歪歪扭扭、深深浅浅的手推车轮印以及零零散散的脚印。想必是道班工人留下的痕迹。但是他们没有铲除公路上的积雪(无法铲呀!)。张副团长坐在王满洲身旁。不时地指着车前的印迹对王满洲说:“那是道班工人给我们引路,你就跟着它走,准保没错!”有时印迹突然不翼而飞,肯定被大风卷走了。他就对王满洲说:“慢一点,停车!咱下车找找路……”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暴风雪封困的唐古拉山上,下山尤其难。路面陡又滑,路线也不清楚,翻车、陷车随时都可能发生。王满洲稳把方向盘,轻踩油门,汽车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扑撞着路上不时出现的雪墙。好不容易遇到一段较平缓的路,他才能换上高速档快走一会儿,更多的时候是三步一停,两步一推……
三十年后,我就唐占拉山这次暴风雪的遭遇分头采访了已经从青藏兵站部部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张洪声,以及接任张洪声就任部长的王满洲。重提艰难岁月,他们都感慨万千,但又显得十分平静。
张洪声说:“在当时那种道路险要的情况下,我们派人开车下山当然是一件冒风险的事,弄不好就会车翻人亡。但是,我们被逼上了梁山,别无选择。派人下山虽然有风险,却有可能救出两百多人。呆在山上等待援军,等来的必然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