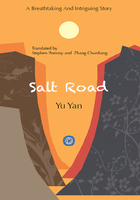当他走进门来,望住她,直接对她说我等了你四天之时,她内心充满感受。女人的心有一半是用来装爱情的。她的心的那一半久久空置,康新来填补了它。她呆呆地听他讲,似乎是在斟酌和选择。不,照常理你已没有这个权利,你已不是年轻人,也不是单身,你已没有不断选择的权利。你几乎没有了。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你肩头,你本该目不斜视,心不旁骛,一往无前地走下去的,可是你脚步蹒跚了,你踟躇了,你犹豫了,你左顾右盼了,甚至你干脆停下来,向斜叉里走去。然而40岁的爱情是笼中的野兽,地下的烈火,你不敢让它咆哮,不敢任它烧上天空,你要捂住它,麻醉它,即使在情人面前你也不敢放纵,否则它会吃掉你,烧光你,让你暴尸荒野。
录入员尹小丽一早就在外边大呼小叫起来。她刚刚洗完晒在门前的衣服就被偷了。她只是回宿舍化了化妆,只是10分钟的时间,出来就发现门前晾着衣服的绳子空出两大截来。她尖叫着,哎呀,有小偷!有人偷衣服了!
藏大伟一夜失眠,直到清晨才刚刚睡着。当他猛听到窗外尹小丽的喊声时,他觉得自己只是打了个盹儿。
一排平房宿舍的人们都被惊动了,纷纷探出头来。有关心的就问一问怎么回事,不关心的就只顾盯着绳子招招摇摇的精致内衣裤看。
只有藏大伟边穿着鞋边冲出门来,他富有经验地向西边围墙一指,叫道,快,先看看那边!他身后,李民民披着衣服跟出来,也叫道,大伟,眼镜!藏大伟头也没回,消失在拐角处。尹小丽紧随其后,也似箭离弦而去。
808所的院墙四面皆有洞,靠近宿舍区的西面墙更是有两个洞。几年来所里的东西什么都丢过,从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到日常生活用品。以至年年都要把可能丢失的东西打入预算了。有时小偷们见有人来也不躲避,公然能把几根木头或者一捆钢筋“咚”地扔出墙,自己再坦然地钻出墙窟窿,扬长而去。几年来,墙洞全是靠所里的职工自发地堵,由于材料简陋,窟窿也是屡堵屡掏,屡掏屡堵,没有穷尽。
藏大伟钻出洞去,一目了然就见一个贼腋下夹着色彩明艳的一卷衣服在几十米外的田里奔跑,尹小丽在他身后大叫,站——住!
春郊旷野,田野已是一片葱绿。藏大伟怦然心动,顿觉喉头处一股热流涌上来滑下去,翻腾不止。民民,你令我心痛!昨晚她哭了。她竟哭了!就在他感到无比舒畅兴尽而至的时候,在他充满了感激释放了渴望之时,他的手触到了她的眼泪!
远处那贼闻声站住,回过头来,尹小丽腾地跳进田里,一步一陷地往前走去。那贼一时不知所措,在田地中央像个束手待擒的空降特务。
藏大伟双手叉腰等在墙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他问她,民民,怎么了,为什么哭?
不料那贼又突然跑起来,恐怕是料定只一个女的追不上他。藏大伟哭笑不得,只得骂一句娘,飞腿追过去。
三个人在春天的绿地里跑,像三只野兔子。土地松软使不上劲,但跑在前面的尹小丽却显得轻捷矫健。年轻的18岁,令人羡慕!藏大伟当年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著名的短跑手,几乎全校人都认得他,因为他跑步时嘴里总是啊哧有声,啊——哧!啊——哧!全校运动会上,他跑百米啊哧百米,血盆大口,形成特色,女同学们叫他“大河马”。
尹小丽跑着跑着就慢下来,她大口喘着气,两手叉住腰,求援地回头看藏大伟,藏大伟超过她去,冲她一挥手,叫道,别停,跟上来!
808所半数以上的老九们都是“牛郎”,分别以每周、每月、每年一次的频率探家,平日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吃食堂,住宿舍,坐班车。这种日子也有个惯性,时间长了,好像身体里的生物钟也跟着变了,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比单身汉有寄托,比团聚汉有自由,比流浪汉有着落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但自然而然地滋养着集体的互助精神,更使藏大伟那身侠肝义胆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妻女不在身边,“后”顾之忧就变得十分的后。而所里一切令人不平不满的事就变得十分的前。发生什么矛盾都可能有人来找他,他也肯定会义不容辞地去调查、排解以至出面上告。
他自己也喜欢自己这个角色。这是他一生注定要扮到底的角色。自小理想化的教育,严格正统的家教为他树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人生准则:正直,诚实,大公无私。
那贼看来是真的累了。在藏大伟和尹小丽的接力追击下,他的步子错乱,拖沓起来,有几次差点儿嘴啃泥栽倒。然而,在他前面不远处就是二队的村子了,现已改叫二村。那人一跌跌撞撞踏进二村,立刻就换了个人似的,越跑越快了。藏大伟死死跟住他,直追到村子后街一家门前。他停下来,等尹小丽。
直到这时,他才觉得浑身的筋骨舒展开了,一夜郁积的压抑和梗阻也终于驱散了。她不肯说明她为什么流泪。不说就不说吧。然而他懂。他懂得一个女人若是愉快就绝不会这样哭。她哭得哀怨,一种无力反抗的无奈的哀怨。长夜中他恍然有悟,白日间他在民民的推拒中感受到的不仅不是爱,不是期待和顺从,而且还似乎是一股惊恐的敌意,是的,是敌意,是女人抗拒陌生男人的一种近似推护贞洁的力量。民民?!——晚饭时他喝了一点酒,吃得全身热乎乎的,她没有能够抵挡住他。也许是他强迫了她?也许是她的躲闪撩拨了他?也许是他报复了她白日间的行为?也许是她利用他惩罚了自己?
藏大伟十几年来第一次在他和民民之间感到了有关性的难题。这是他对谁也说不出口的一个难题。
远远地,他看见尹小丽进了村,腰弯成90°,大口吸着气。
他原地做了两个扩胸动作,然后做转体,一转身却看见直通前街的路上闪过一个人,身影十分熟悉。
又矮又胖的行政处长杜守福手拎两个塑料油桶,双肩下溜,秃头暴眼,扑腾扑腾地进了前街第二个门。
当藏大伟和尹小丽从偷衣贼的鸡窝里找回衣服匆匆闯进前街第二个门的时候,还听到了屋里响亮的应酬的笑声。
藏大伟让尹小丽等在院子里,自己上前叫门。一个老大婆从东屋迎出来,狐疑地打量着他。杜处长在吗?他问。
老太婆摇摇头。
他眼一瞪,说,我亲眼看见他进来的!于是顾不得礼节,一把撩开了东屋门帘,没人;再去撩西屋的,杜守福已挺身等在门口。
干什么?!杜守福虽感意外却十分威严。他的工作原则的最大特点是,以职务的高低区别待人,而技术职称在他眼里则如同草芥,因此科研所大部分老九都不在他眼里——不是领导者当然就是被领导者,因此也意味着被他这个行政处长领导。
找你!藏大伟拨开他进了西屋。那两个20斤装的塑料桶还放在当中地上。他过去拧开盖,每个桶都闻了闻,是花生油。40斤花生油。
杜处长,你哪儿弄的油。藏大伟问道。
这不是我的油。杜守福说。
我问你,油是从哪儿来的?
我说了,这不是……
我亲眼看见你提进来的!
你空口无凭!诬陷好人!……这是人家自己的油,还想送给我呢!
旁边一个老汉垂着眼皮,不相称地吸着一支过滤嘴香烟,无言地点点头。
藏大伟气得发蒙,又追问一句,那你干什么来了?
你有什么权利审问我?我们是亲戚,还不许串门啦?
藏大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对所里的后勤部门,老九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开始仅仅是失望,后来就变成了愤怒,可惜那愤怒只是敢怒不敢言的怒,因此常常怒得失衡,伤了自己。在808所,做后勤工作的人们要比任何人都神气得多。比如吃食堂,同一份菜打在后勤职工腕里是凸凸的,打在别人碗里是凹凹的:又如每周未坐班车,次次都是等后勤职工和家属们坐好了才开到其他人站队的地方;到服务社买东西,肉肥菜烂,假如别人问一句,还有好点儿的没有?售货员就敢反问一句:你这样的还想吃什么?……就为这些,藏大伟都快把后勤各方面得罪遍了。
他憋着气把院里的尹小丽召进来。
一见又冒出个尹小丽,杜守福吓得眼珠于险些掉下来。你们想干什么?
尹小丽一言不发,抽出两条纸巾,各在两个桶里蘸了些油,然后再把油汪汪的纸巾放进小塑料袋里扎好。
藏大伟说,不想干什么,就是带点油样回去,交县里食品研究所化验化验,是不是和808所食堂的油同一个缸号。
杜守福愣在后面,头皮汗津津的。眼珠子最可怜,几乎全暴在眼眶外边,无遮无拦的。
回去的路上尹小丽问,老藏,人家食品所能给化验吗?
化什么验,吓吓他。
尹小丽笑说,你还缸号不缸号的,听着真够专业的。
专什么业,就听我老婆买毛线的时候老问缸号、缸号的……
一下子提到民民,藏大伟喉头处又热了一下。如果能够忘掉昨夜,再也不提起她,只在自己的世界,同事们的世界里,他该是多么轻松啊。他侧过脸来看看尹小丽。刚才见到她跑,身轻如燕,弹跳和爆发力都不错,还有那种迫人的青春气息,于是他说,不错。
什么错不错?尹小丽问道。她出了不少汗,睫毛上有黑色的水珠滴在脸上。
藏大伟掏出一团灰乎乎的本色难辨的手帕递过去。给,擦擦脸,快成李逵了。他说。
尹小丽立刻大惊小怪地笑起来。脏死了!谁用你的抹布呀!
她掏出纸巾在脸上蘸来蘸去,然后冲他扬起脸,娇娇地问,老藏,我擦干净了吗?
民民从来不化妆,也从不撤娇,她是个严肃的女人。她带得女儿小小年纪也从不撒娇。有时女儿冲爸爸稍稍一放赖,民民就呵斥道,什么样子?不许这样儿讲话。民民认为,女人应该自重,自强,不靠男人也能把事情办好。藏大伟喜欢这样的女人,喜欢民民的坚强,他觉得这种吃苦耐劳、咬碎牙齿也不诉苦的女人更让人怜爱。不过,他有时也想,民民如果撒起娇来,会是什么样呢?
尹小丽在问他,老藏,你想什么呢:
他绷起脸,问她,你相信不相信我?
她也绷起了脸,无限忠诚地说,当然相信。
那两桶油,我是亲眼看见他提进去的。可这家伙说我诬陷他……他说。
尹小丽一挺胸说,我们两个做证!
再说,就算我诬陷他,怎么就能那么巧,那家屋里就真有两桶油在当中摆着?
老藏,你放心,虽然我没亲眼看见,但这伪证我做定了!尹小丽扬起头,得意地又补了一句,咱哥俩谁跟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