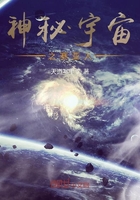加拿大天气干燥。丽君刚来加拿大裱画,裱了就裂,裱了又裂。她一天二十四小时站着看画,一一瞌睡就听叭嗒一声画又裂了。有一次困极了,裱反了,再揭就破,幸好玉琪用点睛之笔把破损处补上几笔。这幅画挂在画展上,那作者很吃惊:我怎么画得这么好?
“学生一年就一个Show的机会,还要请亲朋来看,总要帮他们裱好。”丽君说。
这些天丽君的头发有些蓬乱,她一一无修饰从不打扮。玉琪说话:她不打扮也好看!说女人打扮,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缺陷。当然,在玉琪眼里丽君没有缺陷。不,玉琪常常说丽君傻乎乎,所以把书,店也交她经营,让她多一些独立生存的手段。虽然从丽君来加拿大,玉琪就为妻儿做好了一切的保险,万一自己有个意外,人生地不熟的妻儿都能一直过下去。玉琪说:男人在海外应该更有责任心。丽君笑:光有责任心还不行,还要有爱心。玉琪笑,所以,到了下辈子我情愿做女人。
海外的女人常常存私房钱。丽君不存,说:有了玉琪我什么都有了。
我看到玉琪送丽君的生日礼物——一艘豪华游艇,上边写着:丽君号。我想,对于玉琪,有了丽君也什么都有了。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家里住的一位朋友明天要去美国哈佛大学。朋友那间屋里堆了一地的东西——洗头液、洗手液、洗衣粉、香皂、两袋米、一瓶油、两只锅、切菜板、大大小小的刀、各种杯碗盆碟、刀叉匙筷、洗生菜用的小筐、洗碗用的海绵、擦桌用的毛巾、二十四卷一捆的手纸、大包的面巾纸、半米多高一包的餐巾纸……丽君用一一大布围在朋友脖颈上,玉琪拿把推子给朋友理发,真好像一父一母好生照料儿子呢。玉琪笑指朋友:“儿子”考上哈佛了,我们当父母的为“儿子”送行啊,你得用功读书啊!我说不是用功读书,是用功读“须”(京剧念白把“书”念成“须”)。
那一地的东西,都是丽君买来让朋友带上的。丽君忙乎这些快活得过节似的,正好像儿子考上了哈佛。朋友自己从来没想到要带这些,只有母亲为儿子送行,才会这样准备。虽然那朋友比丽君要大二十来岁。
丽君对谁都有一种母爱。
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昨天朋友走了。丽君撤走了一张餐椅。她看看剩下的四把餐椅,说:怎么还多出一张椅子——她只想到玉琪、莱斯理和我要坐,忘了她自己也要坐。
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莱斯理有点感冒。早晨丽君给他冲了碗感冒冲剂,莱斯理嫌苦不喝。丽君端起碗就把药喝了。我说你没病喝药干什么?她哈哈笑着,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是不愿意在自己手里浪费东西。
我想起她给客人买的那一大堆东西。幸亏是坐轿车过关到美国,否则叫人怎么搬上飞机?
三色冰淇淋
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玉琪总喜欢去几乎不大有人去的地方。今天傍晚玉琪、丽君和我走出乡村公园,走到乡村一方空地上。那里停了一辆警车。一个两岁小孩奶声奶气地嚷嚷着,用双手拍打警车的门。他妈妈给他塑料奶嘴也不要,哭闹着就是要进警车。那警车,一方蓝,一一晃,有一种摇动的快感。手抚着两边的芦苇,好像抚两边的琴弦,密密的琴弦。远远看去,对着阳光的芦苇荡,一派银白;背着阳光的芦苇荡,一片暗黄。银白沙沙,暗黄沙沙,了无人迹。
只有我们。
再往前是原始森林了。脚跟前,有大动物走过的脚印。
我说,如果大老虎来了,杨玉琪再伟大也不行了。
丽君说:有玉琪我不怕老虎。
玉琪说:她怕我不怕老虎。
前边有几棵倒下的柳树,有一种不屈的生命感。玉琪说:你们看,多好!
我想,老柳树容易成精,到夜里就变成美人了。反正一个人我是决不敢来的,三个人我也有一点害怕。
玉琪说:这片芦苇荡最大的好处是:没人。我来过好多次了,你们看这柳树,艺术魅力就在不经意中。
我想起新四军走进沙家浜,又想对着芦苇荡喊:快出来吧,我们看见你啦!真觉得人的想像其实也局限很大。让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片芦苇,录下每一个人的想像就可以测定这个人的经历。
我们已经走进了原始森林。加拿大把锯木厂的下脚料加工成又薄又小的碎片,在林中地上铺成小路,脚踩在上边又防潮,又保暖,又松软,好像环保地毯。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碎木片的路边,一路放过去。游人本能地踩在“地毯”上,顺着一棵棵方白,一方红,三色冰淇淋一样的鲜艳好看,怪不得小孩不肯离去。
警察也在车旁笑着看小孩。他高大憨厚,笑笑的眼睛里洒下一片暖暖的善意。他抱起那小孩,放上车顶,感觉里,好像NBA篮球赛中,球员把篮球放进球筐那么居高临下。小孩挂着泪水就笑了,笑得大张着嘴,流着冰糖样透明的口水。
小孩在警车顶上围着车灯爬来爬去,好像那警车顶是儿童游乐场。警察站在车旁作保护,好像游乐场的服务员。
警察的形象常常就是国家的形象。这就是Canada!我取出照相机正要照警察和小孩,警察谦逊地躲开。我邀他一起照,他立刻就走过来。
告别了警察和小孩,我们的车开进一个陌生的小镇。玉琪得问一下路。在车道上很少有问路的——你停车问路,后边的车就不能开了。小镇车少,但后边也有了两三辆车。后边那辆车里,一男士轻悠地拍打驾驶盘,好像你们要问路就问吧,决不按响喇叭催你。我想起在国内流行一一句话:一份好心情。好心情是一种教养、一种素质、一种全社会缔造的氛围。
我们在小镇随便走进一家家商店。这家布店,卖一方方小花布,很好看,我想或可用来做洋娃娃。牌上写着一元钱四条。我挑了四条去交款,对方说不对,一元钱十条。我说那上边写着一元钱四条。对方说你再去拿六条,我说不,一元钱就是四条。对方说刚刚改成一元钱十条了,那牌子上还没改。
这样一个私家小店,就一个妇女。顾客自己愿意拿四条就交一元钱,本来她收下钱也行了。所谓的四条还是十条,还不是她自己订的。然而她就像恪守法律那样恪守自己制定的价规。
又进一个私家小店,有一半是旧物。旧物独有的品味往往新商品很难具有。一种小碟,玲珑精巧,上边贴着条:一元。两只叠在一起,我拿了一只。交款时,店主叫我再去拿一只。我说我只要一只。店主说一元两只。我说这条上写着一元一只。店主说这碟两只叠在一起收一元。哦!
像这样诚实的国民,还需要警察吗?不过,正是有这样的国民才有这样的警察;有这样的警察,就有这样的国民。
树往前走。这路这树,呵护你关爱你又全然不着痕迹。
如果这小路用砖来铺,那就情趣全无。
如果一路插上常规的路牌,那就在原始中插进了人工。
现在,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自由地走去,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越走越远。我偶一抬头,看见前边露出一片开阔地,咦,还有一辆白色轿车。咦,那不是我们的车?
玉琪笑:你已经走出原始森林了。
走出了?原来,那碎木片的路,那一棵棵树,就是引导游人从那头走进,从这头走出的。
这种不知不觉被呵护的感觉啊!
我觉得加拿大就像那种老实人,做得很多很好,但不会宣扬,不为人知,评不上先进——当然,我讲的只是我的感觉。联合国评最适合生存的国家,加拿大连续四年被评为第一。
现在,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芦苇荡。阳光下,微风里,银白的芦苇翻卷,好像银白的宠物狗快活地翻动着它的卷毛。
我轻声叹息:真好。
玉琪说:我有这么多好东西向你推荐,我觉得很自豪。
我笑:你带我看这么多加拿大的好地方,你大概拿了加拿大的回扣了。
前方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人坐在打开的车后厢上绑四轮一排的冰鞋。他向我们滑来,快活地招呼我们:“Have a nice day!”
谢谢!我们这一天真的很美好!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玉琪的车14日给撞了。他当即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把自己的车号告诉公司。玉琪把撞坏一点的车开到修车的地方,保险公司开来一台红色的丰田车借给玉琪用。这辆红车干净得叫我觉得没有人气。原来玉琪那辆白车,里边总有矿泉水、面包、面巾纸,一进车就有吃有喝,像家一样,面包渣掉一地更觉得自由惬意。
不过坐在那辆红车里,实在觉得在加拿大出什么事也很方便。保险公司前几天来电问及车用得怎么样了?今天又来电问有没有服务好?而今天,我们已经坐进我们的白车里了。那辆红车么,保险公司开回去了。
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玉琪今天要去旧金山三天。他打电话给一家出租车公司,请来一辆车接他,送他去机场。再让公司在15日什么时候到机场去接他回家。其实玉琪有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请哪位学生接送一下杨老师,学生会多高兴呢!玉琪不,尤其不愿麻烦学生。麻烦了别人,总要还情。麻烦出租公司只要还钱。出租公司派车到家接玉琪再送到机场,只要三十元。
想起有一天夜晚,我们车经多伦多市中心的政府办公楼,好像每个窗户都亮着灯。黑夜的背景上,这些窗户亮得好像是用金箔做的。玉琪介绍,加拿大政府规定,下班后办公室都得亮着灯。
当然,加拿大的水电太充足。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昨天和丽君、玉琪一起去一家叫Moores的宽敞高档的店。玉琪要买长裤。我的腿走累了,走出病了。看看店堂里没有坐处,只好坐上一张大桌子,那是用来给顾客量西服的。经理的脖子上挂一根皮尺,来回照料顾客。我看他内行到几乎不用皮尺,目测就能说出你的裤长、腰围等等,只在需要精确的时候才动用他脖子上的“饰物”。
坐了会儿,我觉得写字桌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两位西装革履的男士在量铺在桌上的西服袖口。因为我坐在桌上,他们只能把西服尽可能铺得不要碰到我。他们就没一个人叫我下来!他们是应该可以叫我下来的。
我忽然想起在多伦多一家超市门口上挂的牌,上面写:You are the boss!你是老板。
我乖乖地下来了,歉意地走开了。
玉琪那边已挑选了一条长裤,我们都说好。经理走过去一看,说这裤料子不大好,不要买。等他找到更好更合适的再买。居然有经理叫顾客不要买自己的商品!
昨晚我太累,早早地睡了。今早下楼走到厅里,沙发上摆着一条崭新的裤子。玉琪说,昨晚九点多经理送来的。
我想,我们常常说开心或者不开心。谁都希望开心,也就是活得好,活得更人性更美好。我又想起那辆三色冰淇淋一样的警车。
不知不觉的呵护
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们走在窄窄的小木板上,桥是用木条连成的,走起来一步一晃,有一种摇动的快感。手抚着两边的芦苇,好像抚两边的琴弦,密密的琴弦。远远看去,对着阳光的芦苇荡,一派银白;背着阳光的芦苇荡,一片暗黄。银白沙沙,暗黄沙沙,了无人迹。
只有我们。
再往前是原始森林了。脚跟前,有大动物走过的脚印。
我说,如果大老虎来了,杨玉琪再伟大也不行了。
丽君说:有玉琪我不怕老虎。
玉琪说:她怕我不怕老虎。
前边有几棵倒下的柳树,有一种不屈的生命感。玉琪说:你们看,多好!
我想,老柳树容易成精,到夜里就变成美人了。反正一个人我是决不敢来的,三个人我也有一点害怕。
玉琪说:这片芦苇荡最大的好处是:没人。我来过好多次了,你们看这柳树,艺术魅力就在不经意中。
我想起新四军走进沙家浜,又想对着芦苇荡喊:快出来吧,我们看见你啦!真觉得人的想像其实也局限很大。让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片芦苇,录下每一个人的想像就可以测定这个人的经历。
我们已经走进了原始森林。加拿大把锯木厂的下脚料加工成又薄又小的碎片,在林中地上铺成小路,脚踩在上边又防潮,又保暖,又松软,好像环保地毯。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碎木片的路边,一路放过去。游人本能地踩在“地毯”上,顺着一棵棵树往前走。这路这树,呵护你关爱你又全然不着痕迹。
如果这小路用砖来铺,那就情趣全无。
如果一路插上常规的路牌,那就在原始中插进了人工。
现在,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自由地走去,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越走越远。我偶一抬头,看见前边露出一片开阔地,咦,还有一辆白色轿车。咦,那不是我们的车?
玉琪笑:你已经走出原始森林了。
走出了?原来,那碎木片的路,那一棵棵树,就是引导游人从那头走进,从这头走出的。
这种不知不觉被呵护的感觉啊!
我觉得加拿大就像那种老实人,做得很多很好,但不会宣扬,不为人知,评不上先进——当然,我讲的只是我的感觉。联合国评最适合生存的国家,加拿大连续四年被评为第一。
现在,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芦苇荡。阳光下,微风里,银白的芦苇翻卷,好像银白的宠物狗快活地翻动着它的卷毛。
我轻声叹息:真好。
玉琪说:我有这么多好东西向你推荐,我觉得很自豪。
我笑:你带我看这么多加拿大的好地方,你大概拿了加拿大的回扣了。
前方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人坐在打开的车后厢上绑四轮一排的冰鞋。他向我们滑来,快活地招呼我们:“Have a nice day!”
谢谢!我们这一天真的很美好!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玉琪的车14日给撞了。他当即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把自己的车号告诉公司。玉琪把撞坏一点的车开到修车的地方,保险公司开来一台红色的丰田车借给玉琪用。这辆红车干净得叫我觉得没有人气。原来玉琪那辆白车,里边总有矿泉水、面包、面巾纸,一进车就有吃有喝,像家一样,面包渣掉一地更觉得自由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