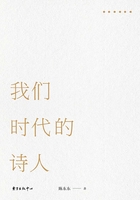但这些都只是作者为他的画布涂抹的“底色”,而作者真正的寄意却是描绘那划破暗夜的一颗流星一女看守乔安萍的美好形象。这是一个从外地“流入”农场调农村姑娘,她纯洁如水晶,朴实如泥土,善良如天使,天真如鲜花。她的身上,劳动者淳朴的天性闪着光辉。可就是这样一朵明丽的小花,来到了严酷无情的环境,并且被委派为看守土牢的民兵。于是,最善良的人要扮演最凶恶的角色,美的灵魂与恶的环境相撞击,演出了一幕令人肺腑酸柔的悲剧。她出于纯洁的天性,爱上了她的****对象一小说中的“我”。一个是看守,一个是囚徒,爱情的种子不死,善良的心灵相通,她倾心相许,以她的真与美铸成的爱情之光,想照亮这黑暗的角落。但微弱的生命之光,与如磐的夜气太不协调了,政治的狂风揉碎了这朵可爱的小花。她以通敌罪被凌辱,欲死不能,终于沉沦下去。“出卖”她的,正是她的情人;她的情人无罪,因为他怀疑美的存在。其实,乔安萍与她的情人石在,虽。然表面看来,一是看守,一是囚徒,实质上都是****路线构筑的土牢里的囚徒。只是一个已经变形、一个尚未变形,最后都发生了变化。
小说着力表现乔安萍身上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她同情囚徒;她抚慰“我”因母亲去世引起的悲她诚实无欺,不愿冒功受赏;她甘冒生命危险,为情人送信……而这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通过她与环境的巨大冲突去表现的。“她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合乎人性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天真幼稚的幻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变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这种撷取矛盾的方法,这种表现的角度,是张贤亮所独有的。这样写,就比那种真接描写****路线的危害深化了,写出了反常的社会现实如何压碎了正常的美摩的心灵。
应当指出,这部作品是有缺陷的。作者过多地侧重于个人细致感情的刻画,而没有把个人的悲欢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社会力量联系起来,使人感到境界较狭小,离生活太“近”了一些。
三、在悲剧冲突中检视心炅
如上所说,张贤亮是擅长于表现“伤痕上的美和痛苦中的欢乐”的;但这必须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正确地处理美与真实的关系。如果抛开严峻的斗争,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那样制造出来的“美”,只能是虚假的和贫血的。张贤亮追求美,但他首先追求真实。他说:“在这种题材上强加笑料或涂抹华丽的色彩,只会。令人啼笑皆非。这里,美和欢乐,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从库电佐夫的独眼和毕尔逊的断臂说起》)。这种“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的见解是深刻的。张贤亮努力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一见解。他的小说虽然有强烈的美感,但首先给我们的还是强烈的真实感。在他的作品里,“情节是构想的,但感情和细节却完全货真价实”,“在艺术虚构上我不敢弄险”,“在描写情节的每一个场景和人物动作时,都依据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同上)。敢于正视现实,面对矛盾,才使他笔下的“伤痕美”具有了深厚的根基。由此又使我们看到张贤亮创作的另一突出特点,那就是在悲剧冲突中检视心灵。
沐阳同志在《在严峻的生活面前》一文中,曾正确指出,张贤亮是以“写人物的心灵和人物的命运见长的”。在张贤亮的作品里,人物心灵与人物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在命运变化中写心灵,又在心灵变化中写命运。他的人物命运,往往浓缩在几个悲剧冲突之中;他的人物心灵,又常通过冲突得到检视,得到展现。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小说写的是邢老汉的命运,而“命运”是截取了老汉一生中最典型的几个断片——感情活动最强烈的片断,矛盾冲突最内在的片断。这里,“命运”也就是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发展线索。
邢老汉是中国农民中的“这一个”。他善良、勤劳、诚实、软弱。他对生活索取得那么少,可最少的索取也被剥夺了。邢老汉“扛了十几年长工”,解放了,他有一种翻身的喜悦。他穷得娶不起媳妇,而******给他送来了伴侣。迟到的爱情虽然苦涩,却也不乏乐趣。然而,这女人“家是富农”,“别说迁户口,就是逃荒的证明也开不出来”。她悄然离去了,给老汉留下了悲哀和寂寞寂寞的邢老汉又与小黄狗为伴,小黄狗又被打死了,于是,在“四害”横行的年月里,邢老汉和他的影子一同消失了。作品着重插写邢老汉的精神活动:他短暂的家庭生活的欢悦和失去这欢悦的痛苦;他把小狗作为精神慰藉和这慰藉失落后的孤独和悲哀。
邢老汉之死是真实的。他无病而死,死于寂寞,死于厌世,死于失掉了精神支柱,死于无法理解那变了形的现实。在表现极左路线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的危害上,它是格外深沉的。****路线不但危害了功臣老帅、知识分子、千万干部,而且连最普通的农民也深深地伤害了,可见它是多么荒谬,多么悖理!
另一篇作品《在这样的春天里》,也同样具有这种把人物置于悲剧冲突中,去探索他们内心世界的特点。春天来到了边疆农场,可春天是多么吝啬啊!主人公“她”,所谓“坚持反动立场”的“****”子女,一个政治上的受歧视者,不但早已耽误了自己的青春韶华,失去了被人爱的权利,而且还受到了风刀霜剑的摧残。如果说,当初由于政治的原因,那个曾经爱过“她”的拖拉机手退还了定情的信物时,她还哭泣过,那么,现在她几乎不会哭了。然而,大自然的春天毕竟来了,她还年轻,听说快要“落实政策”了,那个丧偶的失意的技术员不是暗示过,有朝一日会要她的吗?于是,她找了“站长”。但等待“她”的却是肉体遭凌辱,可怕的“腐蚀千部”的罪名!原来,这样的春天比冬天更冷酷。象《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一样,这篇小说也是把“焦点”凝结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创痛的描绘上。
张贤亮不但善于选取最能揭示人物灵魂的矛盾冲突,而且在展开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对比手法,大大增强了对人物精神世界挖掘的深度。在《灵与肉》里,父亲在豪华的饭店劝许灵均出国之时,许灵均想的却是三十年前父亲抛弃他的辛酸往事;当宋秘书说“你的太太一定很漂亮”时,他想的是土屋里的贤妻秀芝;当父亲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旅行箱时,他却看了看自己尼龙袋里的“茶叶蛋”,睡在席梦思床上,想的是马槽在马槽里痛哭失声,却又想起远在天涯的父亲;父亲买的是高级瓷器,他买的是泡菜坛子……可以说,这篇小说无处不在对比,《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也是把片刻的欢乐与无边的寂寞拿来对照。至于在《吉普赛人》中,“卡门”和“我”的心理对比,就更加丰富了。
在冲突中检视心灵也好,在对比中深挖精神也好,作者都是为了追求美,追求真实,追求美与真实的协调统一?他决不嫌足于表雨的真实,而要力求达到内在的真实。就目前张贤亮的作品来看,典的人物大多在炼狱中煎熬,被巨大的痛苦缠绕,但他总是从这痛苦中提炼美的元素。他要追求的艺术境界,似乎让人想起了拉奥孔雕像群。在那里,人物被毒蛇缠绕啃啮,在巨大的痛苦和冲突中挣扎,但塑像却能达到“高度的表情的真实与高度的美的统一”。张贤亮的目标,正是这种“统一”。
四、意境和诗情
让我们先读一读《灵与肉》的结尾:
“他终于看到了学校。他家门口正站着。几个人向大路上这辆马车眺望。秀芝围的白布围裙,在柔和而苍茫的暮色中就象一点皎洁星光,很快地,那里。人越聚越多,最后,他们看出了是他,全都向大路上奔跑。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她就象迸射出的一团火,飞也似地向他扑来。她越跑越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读完这一段,你的眼前是否呈现出了一幅“高原游子回归图”呢?你是否感到了,这图画中的色彩十分丰富,小女孩象“一团火”,白围裙象“皎洁的星光”,还有那马车,暮霭,人群……如果我们再联想一番,为什么“人越聚越多”,为什么“一团火”会向许灵均扑来?我们从这幅图画中,难道不能更深刻地领悟到,许灵均为什么要固执地回到这苦寒的高原?画面是这般的小,容量是这般的大。这就是小说中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