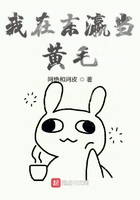麦垄间,里星点点的长着迎春的小草。姐姐一一指着对我说:“看,这是麦萍萍,怪像荠菜的,别挑错了;这是羊蹄甲,一种开黄花的野花儿:这是猫儿眼,有毒,不小心吃了会要人命的。看,这才是荠儿菜,叶子有的边沿像锯齿,有的叶子干脆像把小勺儿,它们开黄花,淡淡的,米粒般大……”我记着姐姐的话,自己便去找着挑。春天的土地,那么酥,只轻轻一剜,一棵嫩生生的荠菜便被挑了上来,用手轻轻一抖,抖掉白须根上的黄土,搁笼甩,再去寻着剜。不大工夫,便挑满了一笼,压一压,再挑些进去,这才走出麦田。在地边,妞姐说,别急,倒出来捡捡,看有没有草混在里头。果然,有些跟荠菜非常相像的麦萍萍便混在里面。拣净,压实,我们这才高兴地走回家去。荠菜儿,择净洗净,可以用来仅饺子,也可用来包包子;还可在沸水里轻轻荡一下,捞出来调着当菜吃。那味道,清香里微带着点苦味,好吃极了。
野小蒜,是又一种堪称上好的野菜。挑野小蒜,要数清明前后或立秋以后最好。一场杏花雨,麦苗儿齐膝高了,在地畔上便可找到野小蒜。那叶子,一从从的,尺把长,绿茵茵的惹人食欲。野小蒜,其味如韭,形状乍看去也像韭菜,唯一的区别是韭叶扁平,而野小蒜叶子则像葱叶那样,呈细细的筒状。采野小蒜无需用铲子,只需用手攥着它的根部,一揪便可下来。野小蒜可以加盐醋等调料后当菜吃,也可包包子,烙菜合,那味道,鲜辣中透着香味,很能刺激起人的食欲。麦收前后,野小蒜便显老了,不好吃;等立了秋,才又发嫩,这时去釆最合适。“九月韭,佛开口”,这是关中人对立秋后的韭菜特别鲜美的赞词。用它来形容同一个时令的野小蒜,我看也是最合适不过了。
苜蓿芽儿,也是早卷一味上好的野菜。这昏蓿芽儿可谓信息特灵,不等百草发芽,它就急忙忙地顶破地皮儿钻了出来。不几天,个儿便长得一寸二寸高,这时去采最好。由于采时是用手一棵棵地掐厂来的,所以家乡人就把采这嫩荇蓿芽儿干脆叫作“掐苜蓿”。掐来的苜蓿芽儿,先要捡去柴枝枯叶,再淘净了,便可用,或煮煮伴上蒜泥凋成凉菜;或用而粉拌一拌,上笼蒸成疙瘩;或用来做汤;也有拌入面粉蒸成菜馍的。这苜蓿芽儿,采得勤,也长得快。今天刚采过,隔一两天再去时,又是一地绿茵茵的了。我敢说,这苜蓿芽儿,绝对称得上野菜巾的正品。它不仅在缺菜的早春填补了餐桌的空白,而且,在饥荒岁月,曾救过多少人的性命啊!
还有油菜綦儿。清明前后,当油菜开始绿臻臻地抽薹展叶,忽地窜起泸尺高时,将它的苔儿掐了来,跟嫩叶儿一块用开水稍稍煮过,切碎了,调上盐醋,拌上蒜泥,尝一口,脆、嫩、香便都有了。找油菜萏儿,不一定要去油菜地里找,那地畔上,休闲地里,有的是。
这里,不能不提一提榆钱儿和刺槐花儿。榆钱儿,是榆树的果荚。但这种子,不像一般草木种子那样,先抽枝绽叶,冉开花,最后结实,而是在榆叶儿尚未来得及绽露时,它已一串串地坠个满树,煞像一串串绿色的硬币。每当榆树挂钱的季节,孩子们便会猴子似的在榆树上爬上爬下,在树干间攀来攀去,将一串串榆钱儿捋下,装得袋溢篮淌的。这榆钱,生吃时甜甜的黏黏的,对孩子来说,这边吃边采带来的乐趣,实在不亚于一次丰美的盛宴。当然,带回家,就会被一律儿拌上面蒸成疙瘩吃。榆钱儿刚败,剌槐花儿又开,简直像“接力赛”似的。这刺槐花开时,整个树冠就会变成一大朵洁白的云絮,还不断散放出一阵阵浓烈的甜丝丝的香气,惹来成群结队的蜜蜂围着它唱。以槐花为蜜源酿出的蜂蜜,便是有名的槐花蜜了。这时,孩子们自然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釆花的队伍中去。他们爬上树,用梢头绑有铁丝折成的钩儿去钩,眨眼工夫便能弄得一大笼。然后择净淘洗拌面蒸疙瘩,凡吃过的,没有谁不想再吃两回、三回的。
还有种野菜叫扫帚菜的,也是不能不说儿句的野菜名品。每3麦收前后,在棉田地垄,人们总能看到一汪汪如同直竖着的小扫帚那样的绿色植物,那就是扫帚菜苗儿了。其所以这么叫它,除却它的形状绝似常见的用细竹苗儿扎缚的扫帚模样外,待它长大长老后,人们把它砍下,稍稍扎缚后,也是既实用又轻便的扫地工具了。这扫帚,在关中,在北方农村,都是普遍应用着的。可在初夏,当它还比较矮小时,去揪下它的鲜嫩的枝叶,用来下锅或做菜,那麻麻的清香,也足以让人胃口大开的。
野菜,家乡原野上的野菜,给我留过多少美好的记忆!想起野菜,我便会立即想起家乡的那广袤的原野,想起那或坦荡或起伏的土地!这是一块春花遍野、禾黍荡香的土地,一块慷慨奉献从无休止的土地,是诞生过神奇的遐想,美好的愿望的土地!正是自这块土地起步,我由春天走向秋天……
想起野菜,便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想起那如翡翠般挺立、云絮般摇曳多姿的榆柳桑槐,想起田头地边那云霞般璀璨耀目的野草野花,想起童话般迷人的苇地草滩!榆的柔钡,槐的坚直,野花的真率,小草的无畏……给过我童稚的心灵,多少启迪和熏陶啊!
想起野菜,我便想到我不曾见过面的祖父祖母,想到父亲母亲、兄嫂、姐姐,想起如同他们一样淳朴、勤劳、执著、无畏的家乡人民!他们世代生活、繁衍、劳作在这片黄褐色的土地上,播种、耕耘、收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千年万代,不曾稍辍!不正是这样的袓先,这样的父老兄弟姐妹,源源地供给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棉麦稻粟,顽韧持续地推动着社会之轮滚滚向前的吗?!他们只知贡献,而绝少索取。现代文明,总是那么吝啬地、迟缓地步入他们的领地!然而,除过偶尔一声叹息外,他们绝少产生过要离开,甚至要遗弃这片土地的念头!对于命运的无奈,使他们更容易知足,如同一把野菜也会让他们多皱的嘴角绽开一丝温暖的微笑那样……
野菜,令人终生怀恋的野菜啊,你就是这样将家乡的原野土地,一草一木,还有众多的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深深嵌印在了我记忆的屏幕上,给我回忆,给我恋情,也给我勇气和力量!
伴随生活的脚步,愈来愈不大容易吃到当年那种新鲜的带有泥土味儿的野菜了。然而,野菜给予我的情感,却是任何时兴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在我心灵情怀的殿堂里,供奉着无数尊美的神祇,这野菜,便是其中高高的一尊!
1982年10月20日
涝池
光光的打麦场边,有一个圆圆的涝池。
每逢暴雨,那满场的雨水,便哗哗注入涝池里;暴雨过后,便有了满当当一池浮着草节儿、木棒儿、羊粪蛋蛋的黄褐的积水。
哥哥用绑着长把儿的笊篱捞上漂在水面上的脏物,这水,便又渐渐沉淀成一池碧沉沉的清水。
好深的水啊,需用长长的竹竿才能探得着底。那些天,不必再给老黄牛去深深的水窖里打水喝了,只需把它拉到涝池岸边,它便会咕唧咕唧地喝个饱的。嫂子用笼提着积攒了好多天的衣服来涝池边上洗,咣咣响的棒槌砸得水花溅得好远,也惹来几只喜鹊儿在头顶嘎嘎地盘旋着叫。绿皂荚白色的泡沫漂在水面上,被太阳照出七彩的虹,闪闪地耀着眼晴。
绿翅膀红肚儿的蜻蜓,吱吱地打着旋儿,并不时倒立在水面上。小淘气们将猫扔到水里,看它从这边浮往那边,最后爬上岸去,一抖擞身子,抖出一团水雾来,便一齐开心地大笑起来。
那时,我们没有见过大湖,更没见过海,每每来了邻村的小伙伴,便都要忍不住问人家:“你们村的涝池有我们的大吗?”为此,常常还会跟对方争个半天。
涝池,大雨过后积满了水的涝池,其实是高原孩子心目中的大海,是一片神圣而又有趣的所在。
如果久旱不雨,这原本丰腴的涝池,便会日渐瘦沉下去,最后只剩下筛子大一汪儿青青的水,就像爷爷操劳一生,最后萎缩了的身躯。看着涝池这时的可怜模样儿,我们只差点儿没掉下泪来。恨不得对着它大声地问:“涝池,你饿吗?渴吗?”
我们盼云,盼打雷,盼下雨,盼涝池快点儿丰腴起来……不几年后,大塘库出现在了高原上,它可要比我们见到的最大的涝池还要大上几十倍的,那盛着的是从远远的河里抽来的水,是能足足灌溉几十、上百亩土地的!
高原的希望,就跟蓝天白云一块儿,泡在那清湛湛的一库水中。可我们,仍旧时时会想起儿时筲陪伴我们度过许多个夏伏的涝池,想起这片我们童年心目中的大海……
1982年6月
眼晴,爱与恨的启蒙
很久以来,我就想写一写我的眼晴。
这不是因我的眼晴有仆么特别之处。譬如说魅力呀,双眼皮呀,黑白分明的眼瞳,一顾一盼,传神于阿睹之中呀,等等。不,不是,都不是!
恰恰相反,我的眼晴属于非美的病态一类的,既窄小又近视。记得儿时,姑姑便常开玩笑说:“喜儿(我的小名)的眼晴,是用指甲掐出来的!”由于小时害过几次眼疾,还由于此后疯狂般的书癖,我的眼晴近视了,参加工作后即使配了数百度的眼镜戴着,也没能完全矫正过来。上学时,尽管个头在班内不算小,但每逢分座位时,还得央求老师给以朝前坐坐的特殊照顾。看戏看电影,也需想方设法儿的去弄张稍稍靠前的票。去书店买书,也得常常拉着一位视力较好的同学或同事一块儿去,以便到时借光。在外面赶路,对于稍远的熟人,由于不大能看得清对方的眉目,也往往失却了应有的礼貌。知情者原谅说:“没什么,那是眼晴不好使啊!”不知情的便怨你的架子大,或者说你不懂起码的规程礼式。所以到后来,我便渐渐总结出一套应对的办法:出家门口,有远远朝我走来的人,我便笼统地招呼一声:“你来了!”或者“你好”之类;如是在街上行走,听谁喊一声自己的名字,即使一时还难以凭声音辨别是谁,也立即响亮地搭讪—声。这办法,还有点管用。但有时也会弄出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弄得彼此都尴尬异常。
说了这些,无非是说眼晴不好使。但我毕竟还有眼晴,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眼晴,绝不能跟肓者相提并论的。
那是解放战争的炮火已隆隆逼近我的家乡关中,国民党军队还在顽抗的岁月。在我家居住的小镇上,不时有胡宗南的部队过往或进驻。一次,他们“号”了我家一间房,同时还占用了我家的灶房做饭。我家的面缸炊具柴火一应东西还没来得及搬走,他们便做开了饭。他们几乎什么也不带来,就用我们的面粉、柴火,连母亲刚刚择好的一盘大兑芽儿也炒给了他们排长吃。我给母亲报告,母亲怕得什么似的,急急用手捂着我的嘴,低声说:“不要说,人家听见了,要闯祸的!”那时,我虽然还不足十岁,但由此从心里认定了:他们不是一伙好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