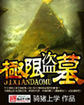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伟大革命运动,把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这个社会革命运动同时发展变化的新文学运动,也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开端。“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整个艺术部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新文学艺术,出现了像鲁迅这样的伟大作家,造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就辉煌期,给新文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学运动的成果,其决定和支配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的文艺理论的指导,尤其突出的是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思维,使作家、艺术家对于文艺如何更紧密地与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真实地反映人们所实际参加的现实生活,推动历史的发展变化,有助于时代的变革前进,有了新的自觉的认识。“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成就离不开这一点,就是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成就,也与此有密切关系。
一、深入反映和推动现实的理论动员
如果把《新青年》创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看成是运动的准备的话,那就是说从1915年就开始了新文学运动的酝酿期。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经过一段动员,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渗透到文学领域,新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并实际发生了“五四”运动,这可以说是新文学的运动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影响作用于新文学,直到1925年革命形势发展引起新文学战线发生分化,这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期。本题所论的现实主义在时间上即指这十年期间的现实主义理论倡导。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推动下发生的,这就决定这个文学运动的重要文艺思想潮流,不能不是强调文艺与现实人生结合,并推动社会变革,而这种思想在文艺理论上又必然表现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动员。
首先是在理论上公开地提出了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本来是与文学艺术创作一起发生、发展的,但由于人们对于它的自觉认识和把握比较晚,特别是在理论上的明确概括和标识更晚,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知其所求而不知其所名的情况下。如果说,法国1855年因库尔贝的画展,有了明确的“现实主义”的名称;那末在中国的文坛上,现实主义这一名称被正式定名强调是在“五四”时期。20世纪初年,首用为王国维,他称之为“写实派”。
陈独秀在1917年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高扬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其二即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这里的“写实文学”,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当时叫法;与他自己在其他文章中所倡导的“写实主义”一样,都是对于现实主义原则的强调。
当时,新文学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齐力提倡“写实主义”,形成了比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现实主义思想动员,成为左右文艺运动的重要潮流。
李大钊1919年12月发表《什么是新文学》,明确提出作为新文学的首要特点“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把新文学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并特别强调现实主义的历史地位的重要理论阐述。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倡导现实主义的前后,胡适从理论上多方面阐发过文学“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表现自身“亲见亲闻”、“亲身阅历之事物”的意义;鲁迅则从创作实践上率先垂范,写成了《呐喊》、《彷徨》等现实主义新文学的伟大杰作。直到1921年,当时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从召唤有更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出世的愿望出发,发表改革宣言,大力提倡现实主义,指明中国当时“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还太少,宣告:“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
其次是强调这种现实主义新文学要以真实的生活为内容基础,而特别反对以观念性的旧道德理论为内容基础。当时对于“文以载道”的批判指摘,就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发生的。
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家,当时为了造成革命的文学战线,使新文学与依附于旧时代、表现旧思想的文学彻底区别开来,他们非常集中地攻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口号。
“文以载道”是宋人对韩愈所进行的古文运动的文道结合主张的一个公式性的概括。在唐代韩愈以文章弘扬孔学的道统,就其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文风,变绮丽的骈文为朴实的散文,使文章摆脱形式主义的桎梏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是应该给予一定历史地位的。但是就韩愈的所载之“道”的内容实质来看,其大体不外乎是孔学经典中标榜的“君臣父子”、“仁爱忠信”的一套教义。这种东西在韩愈时用以攘斥佛老、维护统一,还有一定意义。但是“文以载道”的口号流延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表,现世的孔教信徒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公式,要求文还是古时的文,载的道还是韩愈所载过的那个道,这就是实行文化****主义,既不允许创立新时代的革命文学,也不许新文学表现新思想、新道德。所以要不要“文以载道”的口号,实质不在于文中是不是都有必载之道,而在于要的是哪个阶级的文与道,究竟承认不承认革命新文学及其表现的思想体系为合理救时之道。“五四”时期新文学战线反对“文以载道”,是以无产阶级为盟主的各革命阶级的文学联盟,同以传统口号为护身符的封建顽固派,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生死斗争。
在当时的运动中,批判“文以载道”的各家都是很注意讲道理的,很有一些分析的精神。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肯定了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指出“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气所趋,乃使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俗论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但陈独秀认为新文学并不是过去那种的热衷于“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前锋人物刘半农,彻底揭露近世八股文人之所谓“文以载道”,不过是“奉《四书》、《五经》为文学宝库,而生吞活剥孔孟之言”,“堆砌之于纸上”。他认为这类东西根本不能成其为文,再加上文之“骨底”缺乏天然之美,结果必如“丑妇浓妆,横施脂粉,适成其为怪物。”郑振铎和茅盾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传统之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并不能全面标示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反倒成了抹杀真正文学作品的借口。
从上述反对“文以载道”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当时的反对者并不是一般认为文中可以无道,或以为作家可以无自己所认可的所载之道,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主张文中要有新思想。这也可以说是文中之道,但不是古人之道,而是革命之道。不过,新文学理论家不要过去的现成口号,而是自己应势创造。这是新兴的革命势力向现实吸取力量的具体表现。第二,新文学运动的理论表述者,为了在范畴上确立文学的特点,把封建正统向来不予承认的小说、戏剧等纳入文学范畴。这决定他们就不能以载道的与否来论文,因为许多稗官野史、传奇杂剧,多有离经叛道之言,如要按载道派的观点看来,必因其有违道统而不加承认。而新文学由于是不载旧道的,也必然因此不被承认。这就是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家自有其道而又反对“文以载道”之说的原因所在。第三,“文以载道”之说的现世许多标榜者,把道视为文学的惟一内容,根本不理会文学的内容是以生活事物为基础的,不承认道必须附丽于生活,“神与物游”,形成生活、思想感情、艺术的三者完美融合;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比较重视文学中的物,坚持了“文学是人生的反映”的唯物主义文学观,并强调文学中的思想表现应该讲究方式,作者要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指出“小说而具讲义的性质,实非所宜。”《寄胡适之》。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新文学的理论家反对陈旧的“文以载道”的主张并不是提倡文学的思想真空,而是要表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入讨论,新文学内部的分歧愈加明朗化。因为作为新文学思想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要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文学,在扫去了旧文旧道之后,认为应该在文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宣传现实革命的各种真理性的主义,这对于同盟中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为目标的右翼人物,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必然引起他们的惊恐和反对。这时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于1919年7月出来高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文学上实际是反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反对实际的革命主义。他把反动派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攻击反对,反说成是“嘴里挂着”“过激主义”的人引起来的,他认为要“根本”解决,只有“少谈主义”,或把主义“摆在脑背后”,才能解决问题。这实际是用他的实验主义来代替一切革命的主义。
如果说“五四”前夕文学战线上的“新青年”一派的人物曾共同争取过文学的现实主义,反对贵族的古典主义,那么当运动前进了之后,同一的流派中也发生了分化,胡适由于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原因,则由原来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变成了以现实主义对抗马列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在历史前进运动形势下的胡适由于狭隘地执著于改良现实具体问题,而不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所以他的现实主义最后也化为乌有了。这可以视为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一次大分化。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保卫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思想方向,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在1919年8月致书胡适,《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有社会上大多数人共同努力,有一个“理想的主义”,才能“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因此只要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高谈却没有什么不可”。这是捍卫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实际也是主张文学中也不能不表现革命的主义。这也是坚持了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并使其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运动相结合。同年十二月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明确提出新文学中应该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认为这是重要的思想“根基”,没有这个基础,很容易变成“偶然一现”、“热闹一阵”的花木,“外力一加摧残,恐怕立萎!”李大钊批驳胡适反对一切革命主义之后,号召人们认清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变动”,不要怕扣上“邪说异端”和“过激党”的帽子,要“认定我们的主义”,从事“实际的运动”,并“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这里已经很有一些革命现实主义的内容了。李大钊坚持革命的文化战线和新文学当以革命的“学理”和“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主张,对新文学运动起了统一、振作军心的重要作用。
再次是从反对把文学变成有闲文人脱离现实的单纯游乐工具主张,发展到有助于现实革命,从而加强了文学与现实运动的联系,大大提高了文学在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准备中,为使文学革命更好地配合社会革命,不仅反对为旧传统载道,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消闲遣闷的单纯游乐工具的倾向。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把“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作为文学革命任务之一,原因在于这种文学不关注社会人生,“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后来的茅盾与郑振铎都坚持反对那种把文学当游戏的“名士派”、“礼拜六派”,指出这种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的重要原因。“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理论有一个基本倾向,就是从各个角度推动新文学创作与现实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凡是有碍于此者,不论来自哪里,具有怎样的权威,都是要受到批判否定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在各方面的进一步深入,从1922到1924年,党内早期的革命理论家,针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形势,提出很多前期运动中所未能提出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观点以文学应当成为作用与推动革命的列宁主义原则为中心,表述了革命文艺的领导问题、方向问题、属性问题、任务问题、作家思想问题等重大原则问题。有些问题虽然只是提出了要求,尚由于多种原因未得深入、详尽的阐明,但它却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运动中的进一步体现,其意义与影响都是非常重大、深远的,在中国现代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清楚地显示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