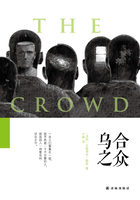在描写人物性格时,人物的衣着、陈设的描写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巴尔扎克说:“走进人家的屋子,你第一眼就可以知道它的基调是什么,是爱情还是绝望。”。人总是通过多方面的条件肯定和显示着自己的个性。在《红楼梦》中,潇湘馆的鹦哥,在食水不接时,都会发出黛玉的那种吁嗟长叹的音韵;窗下的千竿斑竹,也因为主人公经常是“彩线难收面上珠”,而加重了点点斑痕,衬托着黛玉的多愁善感的性格色调。在果戈理的《死魂灵》中,梭巴开维支外貌像熊,为人吝啬、贪食,身体肥胖,头脑迟钝,脸通红,走路常好踩了别人的脚。因而他家的桌子、椅子、写字台,都全像他本人,笨重,坚牢,带着不安的性质,又仿佛在说:“我也是一个梭巴开维支!”或者说:“我也像梭巴开维支!”作家写了这些陈设,正是“因枝以振叶”的笔法,在这里透出了人物的性格面貌。狄更斯在《董贝父子》中写了一个开托儿所的老寡妇皮普青太太,为人性格乖戾,冷酷可怕,而她的衣着也极能透露她的性格情状,40年一直穿着“黑色的羽纱,色调那么暗,那么深,那么阴沉,那么昏黑,甚至天黑了用煤气灯照也照不见她,她一出现,再多的蜡烛也会被她衬得黯然无光。”所以她管理孩子,也难怪她,凡是孩子不喜欢的她偏给,凡是喜欢的她却偏不给,以致竟用这个来“培养”孩子们的“温柔”了。
我们谈到这些通过思维肯定自己和使人物自身本质对象化的塑造性格的形式,自然要服从典型创造的需要,符合典型的社会本质,失去了这个,必然会流于形式主义,这是应该明确的一点。
五、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的性格,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显得更为意义直接。因为语言是人们的思想的直接现实,人物发自内心深处的语言,总是在表明其为人的性格特点。黑格尔说:“一切表现手段,从表现意蕴的能力来看,都比不上语言。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而动作,由于起源于心灵,也只有在心灵性的表现即语言中才获得最大限度的清晰和明确。”黑格尔的强调并不过分。鲁迅的《看书琐记》里认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与邻家隔着薄板壁,虽未见过面,但从说话里“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哪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所以作家刻意经营的典型人物的语言,就更可能具有个性化的特色了。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应以人物性格的定性为核心。狄德罗说:“人物一经确定,让他们说话的方式就只有一个。”成功的典型人物的语言都有这样的特色。
比如《红楼梦》里的袭人与晴雯,这是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人物,袭人是一个驯顺的大丫环,由于她的忠实奴性,深得上房人物的重视,甚至连宝玉也得受她的软法制约,她自己也以宝玉的聪明的保护人自居。而晴雯,却是一个浑身都是棱角的人物,“性情爽利,口角锋芒”,向来不屈服于人。在第三十一回书里因为晴雯跌折了扇子骨,宝玉骂了晴雯,晴雯不服气,与宝玉吵了起来,这时袭人以保护人的资格出头排难解纷,结果倒还把矛盾弄得愈加严重,晴雯与她发生了冲突,在三次对话里,两个人的性格已经跃然纸上了。袭人听见宝玉与晴雯口角相斗,过来和宝玉说:“好好儿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呀,省了我们惹的生气。自古以来,就只是你一个人会伏侍,我们原不会伏侍。因为你伏侍的好,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我们不会伏侍的,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这锋利得像刀子一样的语言,袭人受不住了,但她不是进攻性的人物,想忍性求全,所以只想了事,没有仔细忖度用词的重量,说了一句:“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儿,原是我们的不是。”一个“我们”,使得晴雯又鄙视又嫉妒,旋即冷笑进逼:“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瞒不过我去!不是我说正经,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这入木三分的语言,连带旁敲侧击,宝玉也有点手足无所措了,只好以退为攻地说了一句:“你们气不忿,我明日偏抬举她!”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袭人,为了平息宝玉的怒气,又不知轻重地说晴雯是“一个糊涂人”,不叫他与她分证,晴雯又是分毫不让,意在言外地说:“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我不过奴才罢咧!”这场斗争的结果,只有袭人服输才算完结。这样的对话,把人物的性格的特性显示得多么清晰!
在现代文学中像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的语言,简直鲜明得使人惊异。就以阿Q在静修庵中偷萝卜被老尼姑看见之后的一段为例,也就足可说明了:
“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啊呀,罪过啊,阿弥陀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园里来偷萝卜?”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这里阿Q只讲了两句话,共计二十八个字,但每一个字里都饱含阿Q精神,都像是一个阿Q,从这里我们又进一步地领悟到,性格的丰富性与人物所说的每句话都有那么大的关系!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还应与人物的出身、教养、心绪、意向等等条件结合起来。“三句话不离本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都有一定道理。在孔乙己把茴香豆给了围着他的孩子们每人一颗之后,看一看剩下的已经不多了的时候,只有他这个落魄、可怜,但却不失善良的腐儒才能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在《水浒》中,武松去东京之前在哥哥家告别,以双关语言点化潘金莲之后,潘金莲恼羞成怒,指着武大郎骂道:“你这个腌脏混沌,有甚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也要着地。”就听这一番话,也知潘金莲是一个辣婆娘,绝不是温柔淑女,而加上见识广博,又善于应对的特点,就使懦弱的武大,在她跟前必然难讨公道了。
我们看语言的个性化,也不能苛求作家,要他的每一个人物的每一句话,都得表现性格,这难以实现,只要在基本关节之处,人物语言都是表现性格的,那也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了。以一个人物来说,在他的性格发展的关键之处,当他的精神进入波澜起伏之时,他说的话里就更能显露他的性格特色。这就是一个重要关节,类似这样的关节,就应充分利用。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剧中的玛格丽特,当她被逼得过分忍痛地离开了阿芒之后,她的心已经碎了,旧病又缠住了她,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阿芒虽然来了,但能使她兴奋,却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她预感到一场生离死别行将在即的时候,她把一颗善良、优美的心,透过不多的话语,全部向阿芒坦露出来了:
“你去开开那一个抽屉,那里头有一个小油画像……是我样子还好看的时候画的,是专为了给你画的,你去拿去藏着,将来做个纪念吧。但是,要是有一天,有一位年青貌美的女子爱上了你,而你也娶了她——这是应有的事,而且也是我要你做的事——这个小像被她发现了,你就不妨向她说:这是一个女友的像,她现在,要是上帝答应她在天上最幽暗的一个角落里占一个位置的话,她正在那里天天地替你们夫妻祝福哪。要是她嫉妒已往——这也是我们女人常有的事——要你把这个小像牺牲了,那么,你只管为她把这个像毁了,不必恐慌,不必懊丧,因为这也是应当的。我现在预先原谅你——多情的女人,感觉着对方不爱自己的时候,是太苦痛了,我的阿芒呵,你听见了吗?你都听懂了吗?”
这段刻骨铭心的遗嘱,几乎是这个悲剧女主角的全部性格的体现,如果不是把人物放在这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条件下,也很难以叫她说出这样深沉倾注般的个性化的自白。由此看来,个性化的语言,应该在人物语言中全面渗透,但亦应利用有效时机,让他把话说在刀刃上。
人物的语言既然是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无论如何也应注意艺术的美。所以尽管我们上面说到人物的出身、教养、心绪、意向等等与语言的密切联系,但我们也不赞成把行业语言大量地让人物说出来,更不同意自然主义地把人物的日常语言照搬到艺术中来。我们主张的是人物语言在表现性格的条件下,力求真与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