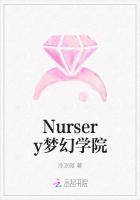杨蕴芳见无法隐瞒,只好从实“招供”:自己有身孕已经四个月了。但是,对自己的事她不想“扩大战果”,便仍然以一个队长的身分与威严对身边的几个妹妹说:
“这事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可不许往医院里捅,记下了吗?”
“这可不中,你这个决定俺们不能执行。这5000多米的地方严重缺氧,你不要命了,也得替未出世的孩子想想。反正你是一天也不能在山上呆了!”
是的,严重缺氧导致流产、胎儿发育不良,当医生谁还不懂得这些?
热心而有主见的魏丽芳再也不顾队长的反对了,她要不受任何阻挠地按照自己设计的方案行事:一方面让下山的人给自己的爱人捎信,快托人带些保胎药上山来;另一方面毫不迟疑地把此事报告给了医院领导,让组织上调杨蕴芳快快下山。
然而,她白忙了。就在她紧三火四地做工作要保住杨队长可爱的第二代的时候,杨蕴芳已经流产了……唐古拉山,你有罪孽,一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在你的怀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你吞噬的生命不少了。但是你无论如何应该饶过这个小生灵。他(她)是我们的明天啊!扼杀明天,不管是谁,都是罪该万死!
山上的风雪在放肆地吼叫着,它似乎不仅要把山抬起来,好像还想把地球掀翻。那不是母亲在哭泣婴儿——母亲是个坚强的军人,她不会流泪,也不是婴儿在呼唤母亲——婴儿已经夭折,他(她)没见过母亲是什么模样。
暴风雨呀,难道你要吞噬掉人间一切生机吗?
杨蕴芳,你34岁,结婚15年了,你还没有做母亲。这已经是第三次流产了……1970年,她怀孕两个多月时,为一位难产的孕妇做剖腹产手术,产妇度过了险关,她自己却流产在手术台旁。
1973年4月的一天傍晚,她不顾大家劝阻,硬是到戈壁滩去抬粪种菜,使一个发育才三个月的小生命“流”在荒郊山野……
杨蕴芳,你何时才可以享受到母亲的幸福?
地下输油管道这一年年底通油到拉萨。中国人用智慧和汗水在世界屋脊上修起了被西方人称为“中国苏伊士运河”的地下输油管道。
然而有谁知道,这条运河中流淌着一位女军人的血,她以三个亲骨肉的生命换取了这本不仅仅属于她的高原风景线。
5.缺氧与长寿者之间
面对这位生活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的百岁寿星,我的心中涌满惶惑之感,不知如何解释我所遇到的他以外的那些人和事。难道他的存在,要把青藏线人艰辛而痛苦地在缺氧区挣扎,有的甚至献上了生命的现象否定掉?当然包括我创作的这部系列报告文学。
冰块在春的河流里缓滞地流动。
我的记忆的大书里夹着一页页发黄的昆仑书签,虽然发黄,但是它比秋天的太阳还火辣;现在又夹进了一页像岩石一样的坚硬的书签,虽然像岩石,但是它像夏夜的月亮一样金黄。
寿星叫次桑,藏族牧民,家住西藏那曲地区当雄乡扎珠二村。我第一次听到一位战友说起他是在1988年,他已经106岁了。老人的刚强、豪放全都集中在那张脸上,他的脸结实得放射着一种黑里泛红的浑光。是唐古拉山的一块岩石,是埋在沙漠里数十年硬而不朽的柽柳根!他坚强并不冷漠、宽厚并不失态的脸上每时每刻都浮现着仿佛用手可以掬起来的笑容。他讲话思路敏捷,口齿清晰,只听声不见人,完全不会想到会是106岁老人的声音。
听,好洪亮、凝重的嗓音,分明是从钢板上敲出来的:
“我们这个地方有人叫它‘无人区’,笑话,我们不是人?没有到这里来过的人总是把它和荒凉、恐怖连在一起。也难怪,历史上曾经有好多进来探险的人,但是他们很少有人生还。所以,直到现在有的人提起我们这块地方还胆颤心惊。如果有谁问我,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西藏。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生活得很滋润,我对这块地方爱还爱不够呢!我家乡的美丽你们可能在银幕或照片上已经领略过了。你看,整片整片的草场都是绿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梅朵(藏语:花),虽然我有许多叫不上名字,但红艳艳地开在我的心里。小溪潺潺地穿过草原,白云一年四季都像棉花一样堆在蓝天上,周围的山随季节变幻着色彩。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闲暇无事的时候总爱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觉得自己和这山山水水融到一块儿了……”这是一个生活在海拔4000多米地区的人的感受吗?我听得入迷了,仿佛置身于人间的一个小天堂里。
老人给人们叙述完他的感受,便跪倒在草地,面对没有寺庙的冰峰,开始了他的祷告……
世界屋脊上到处都视氧如金。人们为了活命而在挣扎,在拼搏!然而,硬是有人爱这个“缺氧”,爱这个“高寒”,爱这个“禁区”。
我又想起了一位女性。
她在昆仑山下格尔木的军营罩服役15载,后来又调到拉萨一个军事单位工作了几年。奇怪,拉萨的气候、环境按说要比格尔木好得多,她却是很不适应,吃不好睡不好,无奈她只好又调回格尔木。好啦,一切都回归正常,饭也香,觉也甜。
她说,我是哪里艰苦哪里能安家。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话。
前年,我们在北京街头邂逅相遇,我简直不敢认她了。她的脸有点浮肿不消说,令我吃惊的是怎么显得那么苍老?眼角呈放射状有一束皱纹,虽然浅浅的,但显得很古板。还有,鬓角的几缕白发给她增添了几分忧愁。
她刚40岁出头啊!
她把体温留在了雪山,把英姿献给了高原,把青春染在了戈壁。
我握着她那粗皮暴起的手,心里颤栗着。她告诉我,她已经从高原调回来了,在内地某城市一家医院工作。我为她高兴,她付出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吃了那么多的苦,应该回到内地来。
谁知,她摇了摇头。
我们推心置腹地交谈起来。就在长安街上的一个酒家。我们都不会喝酒。
“我不应该回内地,青藏高原是我永久性的岗位。”她说得直截了当,也很认真。
“为什么?”我大为不解。
她说,调回内地已经快一年了,没想到,身体就是不适应内地的气候,头晕,呕吐,高烧,气短,吃不下饭……就像当初她从内地乍到高原那样不适应。她跑遍了城里城外的医院,哪儿也治不好,都说她这病太怪,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不,眼下专门跑到北京来求医。
“怎么样,有结果了吗?”我有点急不可待。
她摇摇头,接着说,首都的医生就是医术高明,他们找到治好我的病的办法了,也是唯一的办法,这就是:把我再送回到高原去。
“有这样的医生吗?”我掉进了五里雾中。
她说,我在高原缺氧地区已经生活习惯了,20年啊,是娇小姐也被昆仑山的风吹成藏家牧女了。
“我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怪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她倒蛮想得开的,“有人把这种奇特现象称为‘醉氧’。醉氧,明白吗?氧气缺了是好事,氧气多了反而招来祸。我就知道高原上不少同志患这种病,前几年上级照顾一位在高原工作了近30年的老同志到内地的部队工作,不想,醉氧症折磨得他无法坚持正常上班,几乎成了一个活着的死人。后来他退休回到高原去休息,啥事也没有了,身体很好。你可能在西宁兵站干休所看到了吧,那儿住着许多老高原,按说他们退下来后完全可以回到内地去度晚年,可就是适应不了内地舒坦的环境,只好在高原上熬着。”
我沉思着,心情异常压抑。我有好多话要说,但半句也说不出来了。醉氧?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对青藏线上的人却成了累赘、祸害。谁会相信有这种事吗?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她也在沉思。
我俩好久无话。
我替她的命运担忧,问她:“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她喝了一口酒,我也喝了一口。我俩都不会喝酒。
话匣子打开了。酒是“催话剂”,是媒介。
我俩在小酒家谈了好久,好久。悲悲切切,喜喜忧忧;苦中含乐,美中有怨。总之,希望没有失落,大路还在山中。
从酒家出来,已是满天星斗。我们都有个心愿:应该再回到青藏高原去,潇潇洒洒地生活几年。
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段最金贵的岁月留在那里的雪山崇岭间。
我不由得想起了百岁寿星次桑。望着她逐渐消失在月色里的背影,我想:此刻,次桑呢,他还是那么平展展地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吗?我遥遥问他:次桑老人,你知道什么是醉氧的滋味吗?你最好离开这缺氧区来一次京城,或内地别的什么地方……
我听见次桑老人在遥遥回答:不,我哪里都不去,我的天地就在青藏高原,缺氧就是我长寿的奥秘!
我爱昆仑山。我爱唐古拉山。我爱喜马拉雅山。
因为我不仅从地图上看过这一块块赭红色岩石似的颜色,还因为我的双脚曾经踏过这山的热烘烘的胸脯和硬朗的肩膀。这里有苍松翠柏构成的密厚的围墙,也有云朵一样的灵芝、雪莲;有剽悍的背权子枪的猎人,如大山具有高踞太空的宇宙之力,还有女性柔软的双脚在冰冷的山脊上描出来的美丽得像梅花瓣一样的图案。
山的这个世界太大,丰富的哲理蕴含在山里面。一座雪山,一个风格,千里昆仑,锦绣群雕。火山虽然变不成雪山,但雪山的腹部肯定包容着发烫的岩浆。
我走上昆仑之巅。山低了,人高了……
第二节爱情失衡以后
我要你整坛酒,不管它甜醇还是苦涩。
——题记
6.现实与历史镜头的重叠
昆仑军营里的男子汉思念女人的情形带有野性的狂癫。
假如女人是小岛,这些狂热的男人便是围着小岛的沼泽地。
从男人的视角看女人,注定更真实,更富有色彩。
我在这里要写高原男军人的爱。对女友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女兵的爱。不管谁的内心,都会珍藏着的爱情的魔盒,这秘密的核心也许只有两个字:女人。
正是青春的驼铃摇响了求爱信号的年龄,他们告别了花红柳绿的内地,来到孤寂、荒漠的高原,面对着一片爱情饥渴的沙漠……
夕阳,是一颗泪滴,溅起了夜的相思。此刻,高原上的风也在寻找着爱的请柬。
那天夜里,在西宁招待所我和一位大校同志闲聊,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话题触及跳舞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这里从来不组织舞会。”他说。“为什么?”我问。“过了日月山,母猪赛貂婵。”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瞬间,他忘了自己肩上那块金丝编织的黄牌的分量。一位堂堂的大校军官,怎能口出此言?如果是站在他的部属面前,这种话是要污染军心的!
他知道我明天要翻过蕴含着文成公主传说的日月山上青藏线了,便以此“物”赠我。开玩笑!这句酸溜溜的话我在二十年前就听说过,今天重新灌耳不仅仍觉苦涩,还有一种凄惨之感。昨天、今天以至明天,这个现实恐怕是谁也抹不掉的:女人不去的地方,男人是要发疯的!
没错,在日月山以西女人实为罕见,就像要在北京、上海难得见个骆驼一样稀贵。
果然,我一到格尔木这话就得以验证。
接待我的是另一位大校,我俩都是60年代初就一起在青藏线上当兵的老战友,当时我开着“大依发”牌汽车跑拉萨,他在偏僻的五道梁兵站当加油员,整天攥着油腻腻的油枪吱吱吱地给我们的汽车灌着动力。一次,我的车拉了几个进藏演出的女文工团员,那小子看得迷神了,油箱里的油都溢出来了他还在灌,慌乱之中拔出油枪,却忘了关住闸把,弄得柴油四处飞溅,喷了女文工团员们一身一脸……这是往事了,小小丑事一桩。现在,当年的秃小子出脱成了大校军官,当上了兵站部的领导。我们交情蛮深,彼此说话从来不设防,十分随便。我问他:
“伙计,还留恋五道梁那段生活吗?”
“球,不值一提。娃娃们的事了,现在老啦,没那份心劲了!”
他显然明白我的所指,不在意地说着。
“今晚是周末,你也别写了,我也不钻了(指打扑克钻桌子),咱们找个地方风流风流。在北京可玩的地方很多,舞厅、酒家挑着去。咱这儿不行,享受不到你们那些高雅的待遇。青藏线人一入夜日子就难熬了,过去是白天兵看兵,夜晚看星星,怪凄惶人的。现在呢,略有改观,晚上可以看看‘景致’了,这还仅局限于在格尔木。”
看景致?
大校指了指旁边一家驻军医院内一处灯光耀眼的广场:
“呶,那不是吗?看看去!”
我寻思,所谓“看景致”无非是句玩笑话罢了,便没在意,跟着大校往前走去。
他显得很活跃,话也稠密,像是一只老羊在黑房里关了好久,现在冲出来到了广阔自由的草滩上,快活极了。他说:
“周末,在咱格尔木两件事最兴盛,也引人,一是看景致,二是钻桌子。对我,还有一桩美事,这就是周末的晚餐——煮土豆,那才叫好菜呢!”
说毕,他放声大笑。
我知道,他是甘肃临夏人,大家都叫他“甘肃土豆”,离开土豆是活不了命的。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点沉重,遥远的青藏高原上,人们在紧张的一周工作以后,是怎样的在夹缝里度过这个渴盼已久的周末?
格尔木城慢慢地被夜色所笼罩。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仍然很繁忙,那扇形的灯柱不时地在小城夜的腹部闪烁。我们不时遇到从昆仑山方向驶来的汽车,嘎吱一声刹在我们的面前。
车刚一停就从大厢里跳下来几个穿戴整齐、利落潇洒的小伙子。他们和我们走在一起,很客气地打个招呼,便夺路而走。
小伙子们小跑着拥向医院,身后留下了一缕淡淡的美容霜的气息。
大校说,你看他们全是穿便衣的不是?其实都是军人。
军人?我有点诧异。
是的。而且都是战士。大校说话的语气十分肯定。
我吃惊了,高原上的战士真帅!我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