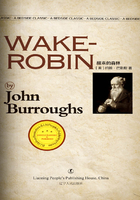那是夏天最热的日子,医院里的芦伟兴政委对3个军医所在科室的主任说:“格尔木眼下到处都是西瓜,我们天天都可以吃上,但是别忘了医疗站的同志,她们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工作,别说吃西瓜了,连喝水都很困难。”于是儿科主任李显全托人给3个女军医捎去了3个西瓜。她们从接到西瓜那刻起,就感得自己这间小屋里有了一种湿润润的甜蜜气氛,第一个西瓜切开后,3个人敝开胸怀吃了饱,真是既解渴又解馋,她们浑身的每个毛细孔都透着甜甜的凉气。接下来,她们谁也舍不得放开吃剩下的西瓜了,每次每人只切下一小块,放在嘴里像糖块一样含着,不让它轻易咽下。这3个西瓜整整伴随了她们20天,最后剩下的一小块还是送红一位病号吃了。
徐春玲告诉我,她从医疗站回到医院不到两个月就生下了儿子。当她看着刚出世的带着她鲜血的儿子时,心里涌动着的不仅是一种初为人母的幸福,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言的滋味。我问她是什么滋味?她想了想,说:我的儿子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跟着我尝过了“无人区”的酸甜苦辣。
我听了,心里酸酸的,对她说:高原军人的奉献精神许多人不仪看不见而且也难以想象得到。
俞祥海院长说:王老师,我们医院住在少数民族地区,在我们每年接收就诊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藏、蒙、回、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他们多数来自边远贫困地方,要拿出更多的钱治病,确实有一定困难。遇到这样的病人,我们从来不敷衍他们,总是满腔热情的、竭尽全力抢救,使他们感受到人间的真情真爱,感受到解放军的医生就是他们至亲至善的自家人。
一次,一个叫马国东的回民外出做小生意途中,因车祸腹部受到挤压,他感到稍有点疼痛,便到22医院门诊部去检查、治疗。医生先是询问了病情,做了一般检查,未发现什么异常。他第二次来到门诊部就医,说腹部的疼痛加重。医生给他做穿刺检查,认为脏器有损伤,让他住院治疗。他问住院的时间要多长,医疗费需要多少。医生告诉他,这些问题都不是现在就能回答清楚的,眼下你最当紧的事是赶紧住院治病。马国东当时一脸的愁云,但是他并没有说不住院的事,没精打采地走了。医务人员以为他准备住院的事去了,就没在意。
接诊医生等了两天,也不见马国东来办住院手续,就有些怀疑他是因为掏不起钱可能不治病了,因为他离开门诊部时提起钱就满脸的无奈。医生想,他的内脏已经损伤,不抓紧治疗延误了时机后果会很严重的。得设法找到病人,给他讲清治疗与不治疗的利害关系。可是,上哪儿去找病人?医生隐约记得病人说他住在一个旅舍。好,就到旅舌去打听病人的下落。
这时,院长余忠江已经得知马国东因交不起住院费拖着病体离开了医院的事。他对医务处的同志讲,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病人,先给他治病,救人第一,医疗费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还可以减免。
医务处主任俞祥海组织了5个医务人员分头去找病人。茫茫人海,马国东在何处?他们只是在那住宿费便宜的小旅店查寻,因为病人生活困难是迈不进高档宾馆的门坎的。最后,他们在一家叫昆仑旅馆的地下室找到了马国东。
“你怎么不去办注院手续?”
“你们知道我有多困难吗?我做倒卖洗衣粉的小生意,情况好时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元,遇上生意的淡季,连糊口的钱都捞不到。”
“生活困难总可以设法克服,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有了病不治那是会要命的。你应该明白,你的病拖不得了。”
“我比谁都明白救自己的命是最重要的事,可我实在没有能力支付这笔住院费用。”
医务人员未能把马国东“请”回医院,他们很同情这个流浪在外的生意人。他们返回医院给余院长长汇报了这个情况,院长很果断地决定,先让病人住进医院,暂时不谈住院费的事情。
俞祥海和几个医务人员去旅馆把马国东接到医院。经过再次仔细检查,他的肠部有撕裂伤,立即做了手术,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关于他的医疗费用问题,后来由地方政府和医院一起做了妥善处理。
还有这样一个堪称奇怪的病人,找到22医院给他治病。其实他本人倒不善言谈,是他的家人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和医院打交道。
这个病人叫杜甲多,藏族,男,17岁,青海省治多县曲蔗莱乡人。他脑子里长了个脓肿,视神经受到压迫,视力极弱。他几乎转遍了高原上的医院,人家都说无法治疗。他来到22医院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生命垂危。医生给他实施了手术,挽救了生命。但是视力只有稍微的改善,看东西仍然不大清楚。医院只能治疗到达个程度。杜甲多住院时间长达50天,医院认为他可以出院时,结算的医疗费共11000元。
杜甲多的亲属拒绝让他出院,理由是,杜的眼睛未治好。医生给他们解释,医院摘除了杜甲多脑子里的脓肿,挽救了他的生命,这对医院来说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是比较理想的疗效。家属根本听不进去,一口咬不把杜甲多的眼睛治疗得像好人的眼睛一样,一分钱的住院费也不交,而且要医院把杜甲多养起来。之后,陪同住院的几个亲属就把杜甲多扔在医院,他们回家了。
谁心里也明白,他们提出的是无理要求,问题的实质是家庭生活困难,无法交医疗费、也不想交医疗费。
医院的同志的想法是:医疗费的问题如何处理这完全可以商量。但是,必须明确地告诉病人及亲属患者的眼疾未完全治愈,这不是医院应承担的责任。医生不可能包治天下所有的疾病。
他不出院,医院就得养着他。当然也要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懂得由于外界的干扰他却不懂或不完全懂得的道理。他毕竟很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
医生找他谈心,起初,他就是不开门,只是摇摇头,意思是他听不懂。当医生有意把话题涉及医疗费时,他听懂了,马上说话了:
阿爸不让给你们交钱。医生明白了,孩子无罪。
医生再也不提医疗费的事了。但是,要教他学会诚实,让他懂得是解放军医院的金珠玛米救了他的命。
“甲多,你的眼睛现在能看见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能看清,是一只茶杯。”
“你再看看,我又拿了个什么东西?”
“是钢笔。”
“你继续看,我这回又换了个什么东西?”
“看不清,看不清……”
杜甲多的视力有限,医生拿上了一根火柴他便看不清了。
医生接着又跟他对话。
“甲多,你觉得你的眼睛看东西比住院前好些了还是不如以前了?”
“当然好多了!那时候你站在我面前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瞅见个影子,现在我把你的眉毛、嘴都看得很清楚。”
“那你的阿爸为什么要说我们根本没有治好你的眼睛呢?”
“医生叔叔,你们千万别怪我的阿爸了,他太苦了,大半辈子放牧攒的那点钱连养活一家人都很紧巴。他真的不是坏人,你们不要让他交那么多的住院费。让我给你们医院打工还这笔住院费吧!”
“你的阿爸和家里人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我们早就说过了,医院是救人第一,至于医疗费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商量嘛!你看他们,不容我们商量就扔下你走了!”
“医生叔叔,你们别生阿爸的气,我回家去把他叫回来。你们要相信我,我会回来的!”
杜甲多并没有回家去找阿爸,因为医院不会放心地让他跑那么远的路去叫阿爸;他所在的治多县的副县长、副乡长带着他的阿爸,拿着一面锦旗来到了医院——他们已经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特地来向医院致谢。副县长是一位藏族,他说:金珠玛米倾注了那么大的心血把我们一个同胞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代表全县人民感谢你们。藏家人会永远记着你们的恩惠。
杜甲多的住院费减去了一部分后,该交的钱由县里代付。县里还妥善地安排了生活困难户杜多甲一家的生活。
俞祥海对我说:像马国东和杜甲多这样的病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少见,我们医院从50年代中期建院到现在,哪一年都要遇到几个。对于他们,我们医院从来都是先抢救病人的生命,绝不因为他们无法支付医疗费而将其推出医院的大门。我们的原则是:
抢救少数民族病人的生命要做到不余遗力,不讲条件。我们把这一行动看作是给少数民族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这样,带来以下的结果就是必然的:医院每年都要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病人垫钱30?40万元,现在累计欠我们的医疗费400多万元。我在这里绝没有蓄意抬高我们的意思,但事实确实如此:在我们抢救的这些病人中,绝大多数是别的医院推出门的被认为难以救活的危重患者。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能把他们抢救过来,也有把命丢在我们医院的。但是我们是尽了力尽了心的。张永刚就是这样一个病人。
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年夏天,好多人都看见在格尔木街头有位30岁左右的流浪汉,他面黄肌瘦,身体孱弱,有时出现在一个工地上,搬搬扛扛地干些零活,有时又出现在菜市场的某个角落摆个小摊卖些小玩艺儿,更多的时候他在市区拣些破烂……准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但是,好多人都知道他是个病人,因为他多次到路边的小诊所买过药,他也向一些居民们讨要过止痛片,他说他浑身都发疼。他不告诉别人他得的是什么病,可大家都能猜想得到他得的是一种瞎瞎病(即不治之症),你瞧那瘦里巴儿的样儿,刮一阵风都会吹倒。
这个年轻人叫张永刚,河南省太康县板桥乡人,1993年入伍到了西藏林芝某驻军,3年后退伍回乡。他未找到工作,只好在家种地,有时捎带做点小买卖。妻子张红梅,农妇。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大孩3岁,小孩还不足一岁。永刚回乡后的最初日子,虽然生活有点苦涩,却也能糊口。不幸的事出现在他退伍后的第二年,他早先就得过的肝炎复发了,而且来势很猛,没出半年就把他撂倒了。医院确诊为肝硬化。他已经把家里多年来积攒的500多元,全部买了药,也未能控制住病势的恶化。永刚消瘦得成了皮包骨头,他不能干活了,所有的农活和家务事都靠妻子红梅去做。而妻子管着两个还在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的拖累太重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张永刚的心头的希望之光并没泯灭。因为他想到了他曾经服役的部队,那是他的家呀,他眼下有了困难,他相信部队的亲人会帮他一把的。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借了300多元,到西藏去找他的部队。
张永刚绝对没有想到去西藏的路是那样的艰难。当年他当兵去西藏吃、住、行等一切事情都有人安排得妥妥切切,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处。现在只身闯西藏,动一动脚都要花钱,要自己掏腰包,10元钱一转眼就用完了,他这才体会到出门远行真不容易!
他抠抠索索、省吃俭用地花着钱,总算到了格尔木。这时身上的钱已经花得一文不剩了。
一位好心的老丈爷帮了张永刚,让他住在了自己一间破旧的四面透风的小房里,好在是夏天,挨不着冻。有了栖身之地,可以站住脚了,他便开始了在格尔木谋求挣钱的门路。如上所述,他在大街上做“流浪生意”……
按张永刚最初的想法,他在格尔木挣够去林芝的路费,就上路了。说实在的,即使拣破烂他也能拣来一笔去林芝的路费,大不了日子过得艰难一些,受些罪罢了。问题是他在格尔木跑来颠去忙着挣钱的时候,他的病情加重了,而且一天比天加重,最后恶化了。他终于倒在小房里行动都很困难了。老大爷和一些好心人也不时给他送来点吃的喝的,但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最要命的是他的病情的加剧恶化使他日夜都在小房里呻吟,有时疼得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打滚。一次,几个热心的陌生人凑了百八十元还陪他上医院看了一次病,当然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只能买了一些常用的药带回小房里。那些热心人还询问了让他住院治疗的事情,人家说,先交一万元的压金,才能进医院的门。天啦!
别说一万元,就是一千元对张永刚也是个天文数字啊!
张永刚在部队培育成的那种刚强劲,在现实生活面前渐渐碰得支离破碎。他无路可走了,不能光靠好心人的恩赐度日月,更何况任何人的恩赐总是有限的。每天在天气最暖和的上午,他不得不拖着病痕累累的身体,手拄拐杖,到街上去找活路。向别人讨点糊口的食物自然是他的主要任务,有时他也去有关部门上访,像他这样没有任何“冤情”的上访者,任何单位也不会接纳他,尽多给他点忠告性的安慰。遇上那些态度不好的工作人员,斥责他几句甚至威胁要把他抓起来也是有的。他苦苦向路人哀求:大家行行好吧,救救我,我曾经是个军人,我为保卫你们每个人的安宁站过岗。
可以想象得出,有几个人会相信他的这番话,穿着槛楼的衣衫,面黄似姜,骨瘦如柴,哪儿能和解放军挨上边?当然也会有人相信他的话,作为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又怎么去帮他的忙呢?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填饱胃囊的食品,他的当务之急是有人救他的命!这又是一般的人包括作为个体的医生在内,也是难以解决的。
张永刚在肝部疼的时候,有时就躺倒在大街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喊爹叫娘地呻吟着。每逢这时总会有人前来围观,但是人们看到他那痛苦万分的样子,就赶紧走开了。有的软心肠的人便扶起他,问清他住的地方,或送他回到小房里,或送他到附近的某个医院及小诊所。可是,他身无分文,又无人给他担保,谁肯给他治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