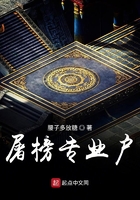1.夫妻之间(一)
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窗前去年才栽的小杨树,贪婪地吸收着这甘甜的春雨,努力向上伸展着。
我坐在桌前,抚摸着一本出版社刚寄来的新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雅致的图案设计配上醒目的标题是那么和谐,淡淡的油墨香与窗外春天的气息融在一起那么好闻,又那么容易引起人们的回忆。我知道,这本不满三百页的小书记载着爱人辛冰几年来的心血,也记载着我谢舜铭的辛勤劳动和滴滴汗水。它,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爱情”这是一个使多少年轻人向往的优美的字眼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爱情有不同的方式。不少人新婚蜜月曾漫步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也曾进出于南京路繁华热闹的百货商店。而我和辛冰的蜜月,却是在实验室、在紧张而忙碌中不知不觉地度过的。
打倒“******”的第二年春天,我们结了婚,那时我俩都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还记得,不习惯应酬客人的他,在新婚第二天一早就躲进了实验室,直到太阳偏西还不见他露面。我煮了满满一饭盒鸡蛋挂面,顺着平时一起走熟了的路来实验室。推门一看,果然,他又埋在书堆里了。消瘦的脸庞在书页的映衬下显得更加苍白,眉尖紧锁着,旁边的一杯开水早没了热气。我心里一阵发紧,走过去轻轻地说:“吃吧!趁热。”“嗯。来,帮帮忙,帮我把这几个数据对一下。”就这样,我们几乎干了整整一个通宵……时光过得真快,革命形势也在向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周围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包括我们这个小家庭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怀里抱上了咿呀学语的小女儿,辛冰的脸上有了红润,有了笑容。他比以前开朗多了,偶尔还笨拙地跟女儿开个玩笑。他工作更忙了,觉睡得更少了。从家里到研究所不过五、六里路,却常常一两天也不回来,有时两个凉烧饼一碗白开水就是一顿饭。我知道,他又被那些“链式电路”“链式反应”什么的迷住了。
家,每人都有自己的家。我们的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书库更恰当些。床上、床下、桌子上、椅子上,到处都是书。屋里除了简单的日常生活必用品以外还堆了大大小小近十个纸箱子,里面装的还是书。这些都是辛冰的宝贝。周围的邻居们,家家都做了大立柜,有的已经转入第二阶段——开始打沙发装电视了,我们家还是用着两口老式的木头箱子。商店里五斗橱、床头柜敞开供应,而我们的手头却往往很拮据,除了必要的开支外,大部分钱都买了书。这些,我做妻子的都能理解,然而要说真正的理解却还是由前不久的一场风波才开始的。
元旦前夕,辛冰要去北京出差,临走前我一再叮咛他:“给我买条围巾再给女儿买些礼物回来,如今你是当爸爸的人了……”怕他忘了,我替他记在小本子上。半月后,我兴冲冲地把他由车站接了回来,打开那些沉甸甸的旅行包一看:书,全是书!围巾且不说,给女儿除了一本《看图学说话》以外,连一块糖也没买,真让人哭笑不得!
大概再贤惠的妻子遇到这种情况也要发火了吧,我实在忍不住了:“怎么搞的?你心里有没有我们娘儿俩?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你看看,周围哪家不比咱们强!你搞科研,我支持你;你买来书,我替你包书皮,分类,编号;你需要资料,我替你查;孩子全由我一人带,家由我一人撑。你,你要当陈景润吗?人家是单身,无牵无挂。你呢,你有家!”听着我这连珠炮似的一串话,辛冰似乎感到了事态发展的“严重”,他抬起吃惊的大眼在我脸上盯了足有一分钟,就像看一个从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样。我一扭脸,避开了那不能让人忍受的目光。
“舜铭,这不像你说的话,不,不应该是你说的。你常看外文资料,比别人更应该知道我们的科学技术差了多远。想想看,咱们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畅快过?咱们要一天顶两天过,一人顶两人干,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得实实在在地干,这是党给我们的权力。如今不比前几年了,你难道亡了……”
啊,前几年,怎么能忘呢?一想起它我的心就要滴血啊!它与屈辱、悲愤、痛苦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2.夫妻之间(二)
文化革命初期,我这个刚刚迈出学校大门的女孩子,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主动要求来到祖国的西北,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身”。那时我是那样的纯朴,无忧无虑。但天空,并不像北京的秋天那样永远碧蓝澄清;生活,也并不像家乡的北海那样风平浪静。出乎意料的事情来了,我收到了北京街道居委会的来信:家被抄了,我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反动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啊!没几天,在西安工作的惟一的哥哥也给揪出来了。我成了一个在同志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的“黑帮子女”。
70年,我和辛冰认识了。刚见过一面,我就因为写黑板报时不慎抄丟了一个字而成了“新生的现行反革命”。几经批斗之后被送到农场和“走资派”们一起去接受劳动改造。临走那天,没有一个同伴敢给我送行,我背着自己那简单的小行李卷爬上了卡车,汽车在一片灰尘中驶出了西安城。
农场,简陋而荒凉,九个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女的。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压不倒我,我谢舜铭不是那种女人似的女人。然而精神上苦闷,失去同志的孤单却常常让我难以忍受。我真想对着荒滩大喊几声,但又喊不出来。
一天上午正在挖井,有人喊我回去,说是西安有人来看我。是谁呢?我一边走一边猜,爸爸上个月去世了,哥哥还关在牛棚里,同志们谁敢来“招惹”我?不,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多半是叫错人了。一踏上大堤,远远我就看见一个削瘦的身影,顶着渭河滩上惯有的风沙,吃力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啊——是他!
自此,每月十号我照例收到由西安寄来的一份邮件,除了科技书以外还有一份手写的外语讲义,这是因为买不到书,辛冰自己编的。
一年以后,当我和辛冰又在人群熙攘的钟楼新华书店见面时,我第一句话便是用熟练的外语说:“我没有消极下去……”当时,他的表情是那么高兴,激动。
“******”垮台了,父亲、哥哥都得到了昭雪平反,我们也成了家。
去年秋天,就是刚刚栽上这棵小杨树的时候,我接到了组织给我平反的通知。欢喜、滚烫的泪像决了堤的洪水一下涌了出来。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把脸紧紧地贴在女儿那胖胖的小脸上,让泪水尽情地流着。孩子开始困惑不解地望着我,然后摇着小手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唱一样地叫着:“妈,妈妈!”是啊,是妈妈,亲爱的党,你没有忘记自己的女儿!
正因为有过阴霾难忘的前几年,才更让人珍惜这阳光灿烂的今天。经辛冰的提醒。我心里更亮堂了,明白了应该如何生活才能无愧于这伟大的时代。我好像又年轻了十几岁,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为了工作方便;把不满周岁的女儿送回了老家。所有的家务我全部承担起来,只要辛冰不能回来,无论刮风下雨,热菜热饭按顿送到实验室。从他的动作、神情,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端上一杯热茶,什么时候该跟他聊聊天,让他松弛一下脑筋。我深深地懂得,这是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妻子所应该想到的和做到的。在紧张的八小时工作之余,我帮助他抄写、翻译了大量文献,到图书馆去查阅、收集了一批又一批资料,我也深深地懂得,这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助手所应想到的、做到的。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他为有我这样的妻子感到自豪。两年来,我们仍像度新婚蜜月一样,在实验室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傍晚和休假。深沉的爱,渗透在共同的事业中,也渗透在祖国的春天里……
《陕西日报》1980年8月23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