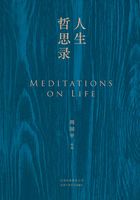第三,世界文学不能缺少中国。两千年的中国文学诞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一批文学巨人,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精华,已然成为了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瑰宝。而中华文化对东方的覆盖性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世界也将是一个跛子。而且按照新儒学的观点,儒教文明还将为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提供一剂拯救的良药。此说自然有待实践检验,但中国文学和文化已越来越为世界所重视却是有目共睹的。虽然由于西方某些人士的偏见以及汉“美文不可译”(张承志语)等诸多原因,西方世界不少人对中国文学文化还处于少知甚至无知的状态,这一点最近被季羡林先生的“失语新说”一语中的:“专就西方文学而论,西方文论家是有‘话语’的,没有‘失语’;但一谈到中国文学,我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但毕竟不乏有识之士开始了荜路蓝缕的工作。前文提及的范尼诺萨是一例,晚近又有美国青年学者金介甫专程来华深入调查考证,撰写了洋洋三十五万字的第一部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沈从文传》,而且对沈推崇备至,认为“沈的杰作可以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边城》“像《追忆似水年华》那样扎实”。并且预言,历史“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此外,拉美文学大师纷纷看好中国,几年前,马尔克斯和略萨都相继自费来华考察访问,目的无非是想亲自感受领略一下中国文化的神秘魅力。而至于博尔赫斯,简直就算得上一个中国文化通了,他对周易和老庄都有相当精湛的研究。谁能说,在他们的“文学爆炸”当中就没有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滋养与影响呢?
第四,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前述两点极言中华文化之精深之伟大,决非鼓励夜郎自大,提倡一成不变,实在是出于一种补偏救弊之用心。我们强调立足本土,回到传统的同时,也强调传统需要出新,需要创化,需要开放;向世界开放,向时代开放,向现实生活开放。摹仿洋人没有出路,摹仿古人也没有出息。因为毕竟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在变小。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中都在不断滋生出新的变性与活性,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异质文化进行愈来愈广泛的交流与融合,从而催发出新质和新机。我们应该拿出泱泱文化古国的气度,大胆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坚信“吃了羊肉决不会变成羊”,而只会变得更加强健有力。“五四”时期茅盾说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形式,而鲁迅则说自己的创作也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钱锺书的《围城》则是他在英法文学中长期徜徉之后直接汇入20世纪世界小说大潮中所溅起的浪花,它是中国传统开放的结果,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但归根到底,它还是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众生相的、飘逸着中国风神的杰出的中国小说,它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继续站在人类文化的最新高度,广迎八面来风,博采四方精华,更新观念,创化传统,以富于民族特色的新文学参与国际性的现代文化建设进程。
事实上,近年来的中国文学界也在实践中逐渐地从借鉴、摹仿乃至照搬域外文学的浓重阴影中挣脱出来了。从韩少功的“寻根”,重视“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到张承志坚定地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深深感到,中文的美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中文的美是否能让世界感受,只要我们有能力继续创造用中文写作的美文,厚重的中国文明就永远可能不被消灭。”从王蒙、李国文、刘心武诸君对《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兴趣与日俱增以及对其美学价值的重新认识与评估,到一批中青年理论批评家对新潮热的反省以及对国内创作实践的认真扎实的爬梳与清理,等等,都是中国文学界日渐成熟的表征,是他们运用从本土从自身生长出来的智慧和从传统中创造性转化出来的话语系统走向世界大文化建设的开始。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作家寻求与世界接轨的“艺术定位”展开了背景,提供了前提,暗示了方向。这就是希望之所在。
最后,归纳我的结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长点,就在于“提升作家素质”、“拥抱现实生活”、“立足传统文化”的三足鼎立。只要跨世纪的中国文学大树,往下能深植于现实生活的厚壤,往上能接通五千年文明的血脉,往外能承受住八方风雨的洗礼,就必将茁壮生长,郁郁葱葱,巍然自立于未来百年的世界文学之林。
2.我为什么反对“下海”——关于当前文人、文学的答问
我反对——当然是反对那些不该或不宜“下海”的真正具有文人品格的文人们“下海”,而对于另外一些原本就以从文作为“敲门砖”或“终南捷径”的本质上是商人的人来说,倒不存在这个问题——关于他们“下海”,其实可以换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做“商人归队”;只不过他们是在商品经济的今天,为自己的彻底“脱队”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恰如其时的机会罢了——他们自然不在我的讨论之列,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是也。至于我为什么反对“下海”,年来或撰文或讲课或发言,我都有过侧重点不同的阐释,因此,这里仅就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再分别简单地谈一下我的相关思考。
一工商时代文人何为?
20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这个历史的巨大杠杆出现在中国也许有点姗姗来迟,但它一经撬动就无疑给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个加速度。然而,正因为它启动太快,造成中国从“政治/农业”社会到“经济/工商”社会的突转,才使当代中国社会像急拐弯中的列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重和倾斜——比如道德失范,比如价值系统的紊乱。与此联袂而至或者遥相呼应的还有,由于形而上学传统的薄弱,由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极端匮乏,一旦高蹈的意识形态防线有所松溃,各种短视目光、功利心态、浮躁情绪和实用主义思潮便如春洪决堤汗漫而出,公然打起种种堂皇的旗号招摇过市。一时间,大有天下攘攘皆为利者、商海滔滔言必称钱之势。金钱似乎成了此一阶段衡量一切的惟一价值尺度。在此情势之下,刚刚从政治重轭下解脱出来的中国文人即刻又被经济大潮打得晕头转向摇摇晃晃,种种关于“文化流失”、“精神贬值”的惊呼、哀叹或诅咒依然被淹没在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狂潮之中,连水花都溅不起一个。一夜之间,被甩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中国文人们仿佛变得更加无所依附,找不到立锥之地了。于是乎,“注重经济效益”、“与市场接轨”、“化知识为金钱”等口号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挡不住的诱惑”,“下海”也便成了当前文人的“自救之路”——有的声称要“先商后文,以经济的自由来保障心灵的自由”;有的则干脆表示要“弃文经商”,直奔金钱而去,公然慷慨“下海”;至于羞羞答答的“隐形下海”者就更不计其数了。毫不夸张地说,突如其来的滚滚商潮在催动社会行进的同时,也给中国文人从行为方式到心理结构造成了巨大的震荡。
问题就这样被尖锐地提出来了——
工商时代文人何为?或者进一步说,在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前工商时代(或曰初级阶段),中国文人(狭义地说指作家,广义而言包括整个人文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他们到底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失落的价值?如何给自己定位?是“下海”经商、发财致富吗?是仅仅在金钱的拥有量上和那些摊主、小商贩、餐馆老板乃至公司总裁、董事长们扯平拉齐吗?如果真有这一天,那究竟是中国文人的升值呢,还是贬值?
在我看来,真正具有文人品格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就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时代的大脑和社会的良知在当前商海横流而人们又往往以某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表象(比如资本原始积累)为根据去批判传统道德同时否定道德本身,从而使一种非道德化倾向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潜伏病灶之际,决小应该去“赶海”蹚浑水,推波助澜乃至混水摸鱼。文人的“定位”恰恰是与这个“海”拉开距离,保持距离。坚定定批判的眼光和权利,以自己清醒的头脑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创造与品格发出正义和弹性的呼喊,既为这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负责,提供一种精神的价值尺度和终极关怀,也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负责,提供一种道德的前提条件和人文阐释——这才是工商时代中人文知识分子独特的责任和无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从宏观来讲,自清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百年的磨难、曲折、激荡和演进,现在已经到了亟待上轨定型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展开的社会现实,使得这种对新的人文精神的文化和理论的呼唤更为急切,也就是说,几十年来在当代中国大陆所形成的“传统中国文化、狭义的两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分文化”(许明语)已经无法对当前中国社会做出合规律的阐释与说明,今日中国大陆推进的既非传统意义的经典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而与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更是相去甚远。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混合型社会阶段,既有滞后的农业文化,也有先进的工业文明,还有超前的后现代思潮;历史还没有提供过相似的范例,以便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做出选择,另一方面,这种万花筒般的五光十色急速旋转着推进的社会实践运动本身又无时无刻不在调侃着和消解着既有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长此以往,这个社会势必行为失范,走向无序和混乱;这个民族也势必精神落魄,走向涣散与颓败……
“天降大任于斯人”,当此之际,历史的期待和现实的要求都把日光共同指向了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尽快地建构起一种富于当代意识和新的人文色彩的精神架构与文化体系,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导引。从逻辑上说,这种要求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因为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与之相应的理论说明。但是,从实践来看,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众所周知,七十年来的中国并没有进行过一场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运动——“五四”时期凌厉浮躁并过早地转向于政治,80年代外(政治)强内(学术)虚又过早地走人疲软——两次小高潮都未能在文化建设上取得更大更多的实质性成果。内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客观环境,比如****(包括战争的与歧治的)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学人培养和学术研究条件氛围的破坏;也有内在的主观因素,比如现代学人过于深重与膨胀的政治情结造成一种“政治/学术”的双分情势,引导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政治第一,学问第二(“出则为长,退则为家”),侵扰了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平常心与恒定力;还有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理想的偏颇:“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短处即实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重实际而轻精神,乃至可以出不少“世界之富商”,而缺乏“世界之思想家和艺术家”(陈寅恪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上对终极关怀和精神追问的传统性淡漠,最终导致了近代哲学——文化之魂的萎缩……凡此种种。都从或深远或切近的不同角度制约了现代中国人文学界的创造激情与活力,使得近百年的文化转型期中几次最关键的历史机遇对新生文化精神的期待一次又一次落空。以此观之,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真是任重道远而又困难重重。
再换一种观察角度来看,也许能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看得更清楚一些。就现代文化学术建设而言,“五四”运动虽未达到原本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毕竟产生了胡适、梁漱溟、顾颉刚、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及其创造成果。相形之下,往后几十年的创造活动反倒只见得热情有余而内涵不足。原因如前文所述,救国图强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和冲动一方面使学人难以冷静地给自己“定位”,总想介入主流意识形态,每每将学术主动地让位于或服从于政治——抗战初期有一句名言,说“偌大一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借此极而言之整个中国大陆又有几张纯粹的书桌?像钱锤书这样几十年“无为而治”(学)的特例真可算得是硕果仅存了;另一方面更为致命的是,训练和培育学人的土壤屡屡“地震”,造成当代学界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以目前的中青年学者为例,他们基本上是“****”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造反”或“上山下乡”中度过的,可谓先天不足,虽然后学有成,但也是亡羊补牢,比起真正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那批现代大师来确难望其项背。我们对当前西学的难以深入和对传统国学的无法衔接就使得我们的学术活动始终无法定位——既找不准明晰的文化背景,也树不起坚实的理论支点。粗粗一看,所谓的学术著作也算是荦荦大端,汗牛充栋,但是扪心而问:往后看,又有多少是谈得上对前人有所超越的呢?往前看,又有多少是可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淘汰的呢?以此观之,又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真是任重道远而又身单力薄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