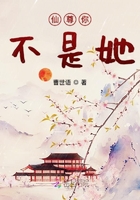第一节:《毛雪》
我曾经从开拓与延展军旅文学创作题材的角度指出过《毛雪》的意义:它在刘震云的《新兵连》贡献的“新兵现象”基础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推出了一种“前军人”的形象。而“前军人”形象出现的意义又不仅仅标示着一种创作题材面的拓展,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军人的新的视角,一个当代中国农民“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的第一个中间环节。作品中的主人公:“我”、那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竞争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心动魄的,同时也是带有相当的普泛性质的。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农家军歌》中有更明了的表述:“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当然,识见不同,希冀也有不同——“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大多是那些家里不太稀荒的人家,不愁肚子饥饱,盼望着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但无论出于哪一种动机,在庄户人眼中看来,当兵效命国家都应该是一种天职,所以:“说到流血打仗的事物,父母们也不私心,说是流血打仗乃当兵人的本分,皇粮养着身子,性命归了国家,丢了也是该着的事情,只当是在自己身上剜了一疙瘩肉去。”《农家军歌》中的这段引文,正好可以用来作为《毛雪》主人公“我”以及围绕“我”参军所展开的全部人们的行为的注释,并帮助我们理解成千上万的类似“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是带着何等样的精神、情感、文化和心理的历史重负与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的。从“我”的身上,我们窥见了农家军人的昨天与前天,因而也就不难想见他们的明天。也许,在他们通往现代化的军旅人生长途上,争抢着体检参军的较量与淘汰,确实仅仅是一场“毛雪”,“正经的大雪”还没开始。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什么样的“大雪”呢?
第二节:《在北纬41°线》、《荒原》、《蓝色黄羊》和《无岸的海》。
对于陈怀国笔下的农家军人来说,这场“大雪”可以是旷辽的戈壁、粗砺的风沙、寂寞的岁月和繁重的劳作对他们生理的和心理的承受极限的一种检测;也可以是包括价值准则、行为方式、道德标尺等等在内的军营文化对他们因袭与承传的农民文化的一种击打与渗透;更可以是对一个遥远而又切近、飘缈而又实在、美好而又残酷的梦想的追寻与失落。无论是那位在“北纬41°线”的茫茫沙海中终年跑车的“红鼻子老兵”;还是那个在“荒原”深处守着一个山洞“一眼眨了十三年”的“老万”;抑或是“守一眼井,堵一条路,在试验场最北边的这方世界一杆枪背了十四年”最终企图和一只“蓝色黄羊”亲近而不得的“老丁”;以及在那“无岸的海”一般的“罗布泊西部边缘阿什干以南”的戈壁滩中的一个窑场里无休无止地做砖的“何黑子”、“老维”、“宝福”、“朱全”们——他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对簇新的人文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许都从或一侧面与层面展现了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勤劳、朴实、坚韧、顽强等等。烧砖也罢,开车也罢,守洞看井也罢,不管是一年半载中紧张剧烈的体力牺牲,还是十三四年里默默无闻的青春奉献,都无怨无艾,恪守职守,始终如一,让你无可挑剔。然而,即便如此,在他们军旅生涯的尽头也终于投能升起理想的彩虹(没有一个人“穿上了四个兜兜”,如愿地“逃离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一个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即看一眼自己竭尽全力为之服务的核试验的“蘑菇云”的愿望也不能满足。“老丁”退伍前夕在去参观的途中半途折回;“老万”只在离队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雷声从远方滚过来,脚下有一阵震动。”随即,“向遥远的莫合尔山好一阵张望……”最遗憾的是“红鼻子老兵”到了现场也错过良机,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新兵的来信”。至于《无岸的海》中那个一百多号人集体撤离窑场时望着烟囱被炸而感叹“妈的,那团火,还真有点像蘑菇云”的结局,就不仅仅让人觉得失望与怅惘而是很有些悲怆的意味了。陈怀国如此无情地逐个击破这些农家军人们的希望,也许是出于一种潜意识的“农家情结”作祟,但在我,却从这不约而同的收尾中读出了一个深刻的寓意。
殊堪玩味的是,这群农家子弟都属于同一兵种:国防科工委亦即火箭原子弹研制兵种。虽然这是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军旅生涯对陈怀国的特殊馈赠,但它无形中却包蕴了一种独特的意味。这个意味就是刚刚从土地和历史深处走来的人群与他们所从事的最先进最尖端的科研事业形成了一种同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尖锐对比与巨大反差。事实上,这种遥远如天上的星辰的反差已经决定了这群人难以进入这种事业的“腹地”,而只能在非常遥远的边缘干着一些诸如看场守井烧砖最好也不过是开车之类的工作。这样,他们暗淡的军旅生涯的结局就已经是先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了。看不见蘑菇云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罢了。
《无岸的海》同样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多层次象征体。一是它象征了戈壁大漠的茫无际涯;二是它象征了农家子弟难以达到理想终点的军旅人生;三是超越了题材本身因而具有更广阔的涵盖面及深刻性的象征,即象征了当代中国农民军人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跋涉与痛苦寻觅。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将难以找到他们的“锚地”与“彼岸”。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头是岸——重新回到土地。
他们重新回到土地又将如何呢?
第三节:《农家军歌》。
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视为陈怀国给他这首完整的“农家军歌”暂时划下的一个句号。
带着深重的希望和同样深重的失望,二哥和大哥相继退伍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土地。他们的收获是“都从部队带回些习惯。二哥爱把那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剃头也极讲究,每月两次,剃得极短,能看得见白晃晃的头发……大哥乡音土语少了一些,‘的’、‘地’、‘得’咬字清晰”。并“乘着还穿军装先拾掇了个女人”。此外,二哥用腿的伤残换得在砖瓦厂吃一份“皇粮”(妻儿仍然吃“泥巴饭”)。大哥则因了复员军人与党员的身份,由一个普通农民上升为一个特殊农民,当了生产队会计,后又在男女关系和经济方面搞得不清不楚,最终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
这样的结局委实有些让人沮丧,但更发人警醒。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身军装的替换,几年军旅的历练,不仅没能把他们的肉体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也没能将他们的灵魂从土地中超度多少。那些和他们的生命一起从土地深处滋生出来的诸如狭隘、自私、保守、目光短浅与斤斤计较等农民根性也始终与他们身上全部的美德与优质纠缠在一起,相伴而行,相反相成,随着环境的改变而相互搏击着,相互消长着。假设大哥们一旦在部队提了干掌了权,他们将会如何演出他们的人生活剧,我想对我们来说也只能是一个谜。
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并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沉落与升华,最终在这里又回到了土地,匐匍在土地。这就是陈怀国为他笔下的鄂西山区农家子弟兵勾勒出来的一段生命轨迹,亦可看做是当代中国大部分(至少是贫困落后的地域)农村兵员青春旅程的或一廓影(虽然其中有百分之几的提干比例,但毕竟是极少数)。据表层考察,这样一支“农家军歌”咏叹的是当今中国一代农村青年生存状况的拮窘和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发掘即不难看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直接给我军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一个急迫尖锐的课题,即******同志早就指出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我向来认为,中国军队的基本成分是农民,中国军人的心理不可能不笼罩上农民文化的折光,质言之,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就是农民心理,军营文化的深远背景就是农民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无以了解中国的军队,此其一。其二,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而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那种种弱弊不仅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自行消除,相反只会在现代化推进中愈加暴露。因此,我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对小农意识进行教育与改造,否则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正是从这两点意义出发,我重视这一首完整的“农家军歌”的客观效应,并把它看做是陈怀国相比较于“新生代”的深刻与超越处和他对当前军旅小说创作的一个贡献。
我之所以特别提到“农家军歌”的客观效应,是因为我感觉到陈怀国的主观意图并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并没能以我军和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与目标为参照,去审视与观照农家子弟兵整体素质上的巨大落差。更多的是带着“农家情结”站在这一群体的情感立场上,比较客观真实地去描摹他们的生存原态与心灵历程,并给以同情、怜悯、惋叹或歌赞。而明显缺乏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与深刻的自审意识。就比如“老丁”、“老万”这样的人物,恪尽职守孤身置于大漠荒原中十几年,以致不得不向黄羊、蚂蚁、狗去寻求情感交流与心理对应,最大地表现出了人的生命个体对于长期寂寞与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承受极限,固然令人感佩。但是,我们在崇敬他们的克已坚韧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的同时,会不会对他们混沌麻木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地打发时光的生命方式感到惋惜与焦灼呢(他们难道不可以在这种无价奉献的漫长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进化与升华吗)?正是这样,在他们的故事中既表现了部队日常任务完成的艰辛与出色,也展示了我军整体现代化进程在某些局部(或个体)上的迟缓与停滞。因而,面对这样的英雄,我的心情就不仅仅止于颂扬,或者感叹。
无疑,要把“农家军歌”谱写得更加深沉浑厚和有力度一些,陈怀国还必须尽快从一己(或一群)的情感局限中超拔出来,以一种宏远的目光和深邃的哲思,去对农民——军人——现代化的三角关系或三维结构作出全新的多方位与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和探寻追问。因此,无论是他笔下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农家军歌”,都还远远投有唱完——“大哥”“二哥”不是都怪自己这个兵“当得窝气,没当明白”,最后促使五弟“我”又穿上了军装么?而且,“老万”的妻子生了一个白胖小子之后也“来信”告诉我们:“这小子像他爹,长大了是块当兵的好材料”……
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谈“农家军歌”的艺术特色了。
与陈怀国的文化承传和抒写对象相适应的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貌(从带有浓重自传色彩的《毛雪》中又可看到刘恒、李锐、刘震云诸君的新写实主义的余绪)。支撑这种风貌的首先是来自切实人生体验与生命历程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语言因此而朴素、平实、简约和洗练,语气亦因此而不浮夸张扬、咋咋呼呼,只是“低调”地含蓄婉转地娓娓道来,十分讲究感情的节约与内敛,情绪的控制与压抑,从而就有了一种凄恻的艺术情调蔓延着、弥散着,变得有几分隽永,有一些余味,耐得住半天咂摸。常常能把一种意绪提炼成一幅看似平淡实则有些“余味”的画面,或是浓缩成几句吞吞吐吐欲说还休音在弦外的话语。下面的句子是比较典型的——“皱皱巴巴的戈壁滩看上去并不坦荡,只有些空洞的感觉。已是早春天气了,罗布泊刚开过的季风收拾了头年秋未落下的那场大雪。还有些残雪膏药片子似地巴在皱起的阴处,使黄不溜秋的天地间多了些余味。”(《蓝色黄羊》)“十多年老狗陪着老万安稳度日,清闲自在,偶尔对了落日残月空叫几声,弄出点声音,倒也消了老万的寂寞,省得老万自己喊叫。想热闹的时候,老万就照准老狗的半截秃尾踹上一脚,狗就尽了所能,曲曲折折地叫出许多复杂的内容。”(《荒原》)“这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爹怕拿不准时间,老早就带我出门。妈说:‘去早了冷得慌。’爹横妈一眼:‘金贵!’然后抹一把鼻涕,就领着我早早地来到大队的场院上,等待目测。”
由此已然见出了陈怀国的白描很有了一些简洁传神的意思,人物对话也颇准确与性格化了。此外,他在捕捉与选用细节方面还很见功力(甚至还为这种功力所累)等等。这些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基本功,陈怀国也都有了一定的磨练,并且达到了相当的火候。那么,陈怀国还有什么毛病吗?
毛病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还不准备以“虽然……总之……瑕不掩瑜”一类的句式来结束这篇已经不算太短的文章。我认为那样做,是对一个文学新人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打算至少再写一千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