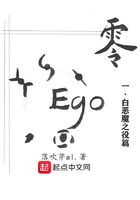钟希同白了一眼,心里疑惑了。两个人除了一起吃就是一起玩,哪有什么正事啊?平日都轮不到她过来,冷易寒自她睁开眼几乎整日陪着。什么时候这般疏远了?钟希同只道他因昨夜的事心情不好,一时也不计较。连请带求的,非要他教她骑马。冷易寒拗不过,只好依了。
八月的山野,正是风情水阔的时候。两人两骑,漫无目的的徐行在山水间,别有一番情调。钟希同瞧着田里耕作的农夫,挑着担子的小贩,驿道上飞驰的铁骑,越发觉得这个古代真实了。
“这马叫什么名字啊?”她指着自己的坐骑问。冷易寒道:“你那匹叫白术,我这匹叫苍术。”钟希同道:“苍术好听,白术不好听。”冷易寒策马靠的近些,问道:“依你,该叫什么呢?”
钟希同想了想,忽而大笑,问道:“******如何?”冷易寒不解,也不深究,只道:“你说叫什么就叫什么吧,这马儿又不会反对。”
钟希同好不容易听他说句玩笑话,一看他仍旧一脸正经的样子,笑道:“你自己说的笑话都不笑啊?”冷易寒愣了一下,由着她笑去。只是在这样清脆的笑声里,他的心也漾出了一层涟漪。
二人又行了一炷香的工夫,便在一个湖畔停下了。钟希同还未下马,便惊叫着:“好大的一个湖啊!”冷易寒扶她下来,脚一沾地就立刻冲到湖边去了。又是叫又是跳,足足扔了几十个石子才肯安静下来,好好说几句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这么美的湖呢!”
“不是,”冷意道:“我就是在这湖上遇到你的。”
钟希同愣了一下,慢慢在湖边坐下。低头拨弄着湖边的嫩草,全然没了刚才的兴致。自己突然消失了,姥爷怎么办呢?他怎样才能接受这个事实?想着想着,想的头都痛了。好像天地间只有一个自己,面对着几十个无法回答问题。
冷易寒静默的站在一旁,他想过去把她搂在怀里,想对她说很多很多话。但是,有一个顾及。所以,只能毫无声息的立在那里。在听到她吸鼻子的时候,递上一块手帕。钟希同接过去,狠狠的擤了擤鼻子,然后递回来。
冷易寒诧异着,没接。钟希同打开手帕看看,说道:“没有鼻涕的。”冷易寒接过去收回怀里。钟希同粲然一笑,问:“以为我哭了吗?”那人点点头。
她继续道:“古有‘孟姜女哭长城’,长城唉,多么不容易才建起来的,她竟然给哭倒了。所以,哭有什么好处呢?既不能解决问题又浪费水分。你呢,不笑,我呢,不哭。我们算最佳拍档吧?”发表完一番歪理邪说拍拍愣着的冷易寒,道:“回家,继续治你的病去!”
回庄后,钟希同拿了纸笔,描描画画,嘴里念个不停。冷易寒走过去一看,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几个词语。比如‘颜色’‘衣服’‘食物’‘位置’等等,让人不知所云。
钟希同解释道:“我在做图表,你想啊,前天明明睡着了,昨天却没有。说明一定有个因素改变了,所以影响了结果。可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她开始喃喃自语,“祷告吗?我昨天也祷告了啊!”
冷易寒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道:“其实,我前晚醒了一下。不过……一睁开眼就看见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又睡着了。”钟希同咬着笔杆,含糊道:“怎么会这么简单呢?会是这个原因吗?”
抬头看了看冷易寒毫无玩笑的样子,又道:“既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能性,不如试试吧。今晚,我还在床边守着你。”冷易寒担忧道:“其实,你完全不必冒这个险。如果你有任何意外,我会比现在更痛苦。”
钟希同笑了笑,道:“我现在可是掌握到秘诀了,只要你一不对,我就大叫自己的名字。不会让自己有事的,你相信我,你也不想一辈子这样吧?”冷易寒想了一会,坚持道:“那你去床上睡,我守着你,也是一样的。”钟希同无奈道:“好吧,反正我是真的困了。”
看着床上很快入睡的小人儿,冷易寒连呼吸都变得轻柔了。靠了靠身后的椅背,慢慢的合上了眼睛。
次日正午,钟希同睁开眼就看到冷易寒静坐在床边。见她醒了,忙递过一杯清茶,轻声道:“我只想告诉你,我昨晚睡的很好。”柔软的袖口拭了拭她额上的薄汗,出门去了。
丫头们一下子涌进来,钟希同刚刚清醒的大脑,没空理会那些或嫉妒、或欣喜、或感激的目光。反复回味冷易寒的那句话,昨夜一室安稳的气息,让她睡的很沉很沉,嘴角忍不住挂上笑意。
为保险起见,如此过了三日,方通告全庄上下。庄主心情好,个人均有赏赐,大摆了三天筵席。冷易寒终于放下心来,吩咐吴管家道:“好好准备吧,日子也就是中秋后了。最迟,不过月底。”听得冷易寒如此吩咐,吴管家喜笑颜开的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