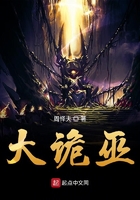一切依旧照着原有的轨迹前行。
他一如既往的对她好,骆尘鸢也清楚,只是当一切都不能尘埃落定,她依旧无法选择全无保留的相信。
宫明深知她心,却也不勉强,只是一直默默的守在她身边,不骄不躁,如同从前一样自若而淡然的为这一路计划。
在一路平安无事的将要抵达晨城时,宋如此和沫儿相互递了个眼色,放下手里的活儿,正着颜色看着骆尘鸢。
宋如此道,“风筝,你跟宫明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但是这一路上来,你这冷冷漠漠的态度,我看着总别扭。眼看就要到晨城了,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们还是趁早解决了好。这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的都耽搁了一个月了。”
“娘娘,王爷对您的宠爱,奴婢都瞧得见的。”沫儿也道。
“到了晨城后,还不知道要发生多少变故呢,当今之计,大家伙最好还是抱在一团做事。风筝,他若真想背叛你,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啊?”宋如此不给骆尘鸢否认的空隙,忙又接过话。
骆尘鸢叹了一口气,看着两人急切的眉目,“也许你们说的对,现在我们应该抱在一团。”只是,他完全有理由等到现在。
“宫明也真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宋如此微拧眉头,靠在锦被上,想了想,又肯定的点点头,“风筝,虽然这样,但是我觉得蔡太师这么一路上都很敞快的。他们都是一伙的人,我瞧蔡太师挺不错的。再说了,你担心他什么啊?你身后有那么神秘的隐卫支持,你也是他的人了。夫妻哪能还分个你我的?”
“分。”骆尘鸢忽而脸色凌然地开口。她已经不敢轻易相信了,说她一着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也好,说她多疑多虑也罢,她决定还是要等。
宋如此和沫儿不解的看着她,怅然一叹,各自无奈的忙活自己的事情去了。
“公主,今晚上先住这渔村。我连夜去黑山去同年老汇合,明早就来迎公主入城。”钟书策马探过身来,将他们讨论的结果告诉她们三个。
虽然早已料到此次来晨城恐怕不可能像上次那样平平安安的回来,但听钟书说出那个“迎”字时,骆尘鸢才如梦初醒一般,钟书的意思是……攻城……
“来得及吗?”骆尘鸢郑重的看着他,深瞳之中只有一刹那的波澜,很快又恢复平静。
钟书点了点头,同样意味深长地回道,“属下会尽力的,公主尽管放心。”
骆尘鸢沉默地安坐于车厢,内心却如绷紧的弦一般,勒得她有些窒息。
“还看哪,都走远了哦。”宋如此笑嘻嘻地拿手在沫儿眼前晃。
沫儿脸一红,嗔怪着否认道,“宋姑娘别乱说,我没看。”
“没看什么呀?”宋如此促狭地追问道,“小沫儿,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呢,我又没说你看钟书,你心里乱想什么呢。”
“宋大姑娘,你别乱说,让人家听到了,很不好。”沫儿脸红得都快要滴出血来。
宋如此嘿嘿直笑,自从月前钟书送了沫儿一次针线被宋如此知道后,就接连发现俩人之间涌动的莫名味道,这几日还被她逮着钟书给沫儿送了些点心,于是宋如此终于又忙了起来,一抓着机会,就把钟书和沫儿羞得脸红脖子粗,十分恶趣味的惹大家哄笑。
她们两个几乎是这群人马中最粗心和单纯的人,看着她们两个,骆尘鸢的心中,总是五味陈杂,浸满了难言跟心疼。
每个人都有自己执着的幸福,心底的疼痛,就像宋如此,这么大大咧咧,痛快而坚强的人,有谁知道她望墨炎那如黑夜一般的背影时,不是彷徨和眷爱?
“你能不装不?喜欢就直说嘛,有我在呢,你主子要是敢不同意,我就把她给卸了!”宋如此哈哈道。
沫儿气得要暴跳。却好马车已停下。
惦念着攻城的事情,骆尘鸢撩开马车帘,急着下了马车要去寻柳念。
沫儿忙追过来对骆尘鸢道,“娘娘,您可别听宋姑娘瞎说,奴婢才没那个心呢,奴婢一辈子都只愿意留在娘娘身边。”
骆尘鸢一怔,心里漫过一丝伤感,顿住脚步,转过身来对沫儿道,“有那个心也没关系,其实钟书也是一个不错的人。如果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了,跟了他,起码也能护你周全,我也能安心。”
“娘娘你怎么也这样说……”沫儿咬着唇,垂下头。
“傻丫头。”骆尘鸢抚着额头,无奈一笑,“好了,不说这件事情了。我心里有数。他今晚就要去回山寨了,你去替我帮钟书打点一下行礼物什去。我去找柳先生说说话。”
沫儿搓着衣角,羞涩地犹疑了一下,见骆尘鸢目光坚决,只能磨蹭着步子,向钟书那边走过去。
柳念独自一人悠闲的坐在渔村的长柳下,手里捧着一卷书,正摇头晃脑的看着,如果不是知道真相,任谁看过去,都会觉得他是那种久考功名,死不就的那种疯癫老学究。
“柳先生。”骆尘鸢不常跟他说话,估计是当初被他整怕了的缘故。
“姑娘请坐。”柳念笑吟吟地收了书卷,伸出衣袖替她弹去了石凳上的灰尘。绛雪山庄中,也只有他一如既往的穿着朴素简陋,行为习惯和在村子里时候没啥两样。
其实当初就算是骆尘鸢不出手相救,村子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恶霸冯迎给平了。
“先生,明日……”骆尘鸢心里焦急,坐下后,便忍不住开口问道。
可是没等她说完,柳念就摇着脑袋,笑呵呵道,“还记得老夫初见姑娘时说的话吗?”
呃,骆尘鸢一怔,不知何意,只能诚恳回道,“柳先生,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呵呵。年轻人,怎地比我这个老头子还容易忘事?”柳念玩笑着,续又道,“老夫说姑娘非凡类,机智心胸都很奇特,只要姑娘不退缩,不迟疑,这些困难,呵呵……”他摇了摇头。
“先生过奖了。我哪里有那么厉害。”骆尘鸢苦笑。
“姑娘志不在此。”柳念笑呵呵地道,“不过,若是脱掉这层枷锁,很难哪,除非……”
骆尘鸢抬起眸,微笑而平静的看着柳念,“我不要那除非。先生,明日恐怕会有恶战,小女恳请先生指导。”骆尘鸢失去了耐心,也更怕柳念的话会让自己那刚刚树立起来的信念动摇,所以只能横下心来,冷静地打断了柳念的话。
“不是明日。恐是今晚。”柳念干脆利落地回道。
“先生……”骆尘鸢一凛,墨眼瞪圆,“你是说……那钟书他。”
“钟勇士已经走了。”柳念神色淡然,从腰间掏出他那个陈旧的酒葫芦,给骆尘鸢面前的杯盏里添满。
浓郁而沉厚的酒香顿时绵延缠绕于鼻间,带着莫名的安定与诱惑。
“喝一口,先定定神。听老夫慢慢给姑娘说。”柳念笑着道。
美酒诱人,骆尘鸢也更想借酒安神,举杯饮尽,“先生,您说。”
“骆伯的身份,明小子可能已经给你说了。这一路上之所以不会动手,那是因为他想给我们最重的打击。到晨城,绝不是结束,而是正式的开始。姑娘不知道吧,呵呵……其实我们如今已经被包围了。钟勇士其实是在突围,而不是去接应……”
骆尘鸢的心在下沉,之前一直所坚持的一切,在柳念吐出那“突围”两个字时,已经轰然倒塌。她本以为这一路平安,本以为会如计划中的那样顺利入城,本以为……
清风拂动垂柳愈加葱茏的枝蔓,恬然而安静,浑然没有暴风雨的前奏。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甚至连一丝异样的空气都不曾被她察觉。
骆尘鸢觉得胸口漾起一丝令她眩晕的甜惺。没有丝毫犹疑,她站起身,毅然拂袖。
却在转身的那一刹那迎上那双带着淡淡温润眼色的深眸,眷恋一般的在她身上流转片刻,如云一般轻飘的落在了她身后,“柳先生,有劳了。”
柳念却没有理睬他,只是欠身对骆尘鸢盈盈一拜,“还望公主恕罪。”
叫的不是骆姑娘,而是公主,那一句,她听得分明真切。
蓦地,刚才那丝晕眩如墨迹般迅速在眼前溢开,浓重而迅速,很快他的目光变得一团模糊。
宛如洪水一般,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她的意识,身体软倒在一个柔软而温暖的怀抱。
她犹记得昏迷的那一刻,朦胧中听到柳念怅然的声音,“王爷纵是为公主着想,但此计未免会伤了她的心。”
带着丝淡淡的忧伤,“伤得太多了,多添一道又何妨?”
是呵,多添一道又何妨?残存的清醒意识在苟延残喘地切齿,纵有万般不甘,还是没有逃脱他的股掌。
看着晕倒在自己怀中的她,忍不住抽出一只手,轻抚她眉目间深深皱下的沟壑,英挺眉宇间潜藏着他怅然而复杂的情愫。
郑重的抬头,看着柳念,“柳先生,余下的就拜托给您了。”
柳念起身,眸中带着赞许与感激,扫了一眼马车中同样晕过去的令外两个人,对宫明长长一揖,“此计凶险,王爷可思量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