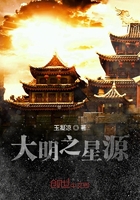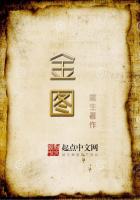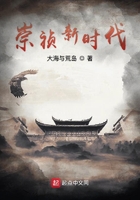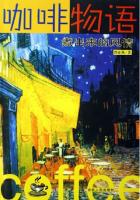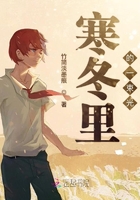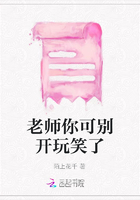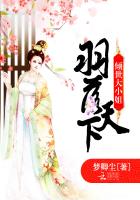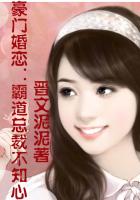与江南织造局的船队交错不过是南下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而以。船队依然依照着他们的速度继续的南下。
“赵大人,前面便是浯屿了。”秦禺指着远处的一个海岛大声的说道。
“哦。”赵传书将手中的书放了下来。然后走到了望亭的前面,站到了秦禺的身边。顺着秦禺的手看过去。只见在船队的右舷的远处,山海之间可以看到一个庞大的海岛正在海天之间慢慢的出现。赵传书知道,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到了。
浯屿,这个时代的金门岛。就是厦门湾的锁阴口。
十二月四日顺风顺水的船队便到达了福建的漳州月港的港口外面的。大明开海的第一个被开放的港口。而赵传书他们来到这里的季节正是这里最为繁荣的时节。
只见船队慢慢的向着前面进前的时候,一路之上都可以看到数量庞大的各种大船在后世的厦门湾里进进出出。并且在没有赵传书的时代里。几十年以后,一个晚明最庞大的海战便在这里爆发。
顺着厦门湾的水道,三只大船一路向上。月港在这个时候正值北方的商船最多的时候,各种北方的小型的货船将浙江与江苏出产的货物运到这里,然后装上闽商们的大船。再顺着季风,一路向南到达马尼拉或是其他的南洋国家。换来香料、银子与及各地的土产。这就是大明这个时代的南洋航线。
所以港口内四处可见北方体形比较小的浙江的货船和江苏的货船。福建的大货船倒是比较少见。
“秦禺。为何这里的大船极为少见。”
“哦,大人有所不知。这些闽商的船全系停伯在周边的私人码头边的。既方便于自己的上下货物,又可以防备有倭寇的攻击。”
“原来如此。”赵传书这才明白。原来明代没有城管,荒郊野外的地方是可以随意搭建的。而月港本身面积有限。使得当地许多人为了大船进出方便,所以都在周边选了新的地方搭建自己的码头。所以整个月港周边小型码头林立,四处可见。而月港本身只是浙船到了这里与闽商们沟通的一个桥梁而以。大船很快进入了海澄县周边停泊。
大船刚一停下,马上便有大量的闽商过来与他们谈价钱。都将三只船当成了过来卖货的浙江商船了。
还没等到赵传书向管斌请示是不是要由他来应付这些人的时候,就看到管斌的座船上放下了舢板。然后管大人就这样前往海澄去“巡视慰问”去了。至于这慰问是不是慰问这海澄的妇女工作就不得不得而知了。
但是从高杰那里赵传书知道自己至少是得应付一下这里的商人们。当然这个工作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赵传书就大至知道了他们这两船货从舟山到这里以后价钱便上涨了六成还要多。可想到时候再到澳门那些地方会是个什么价钱。
晚上,应付了一天的商人之后赵传书才一脸疲惫的回到了致远号上。但是刚刚从水仙门上船赵传书就看到了管事魏清一脸喜色的地走了过来。
“大人。您让人去找的佛郎机人找到了。”
“是吗?”赵传书一听喜上脸色。马上跟着他便向着船尾楼走去。
进了黄屋,果然看到一个身着传教士的黑衣长衫的西方人等在这里。不是瓦利纳尼还是谁。
“赵,见到你太好了。”瓦利纳尼一看到赵传书进来就兴奋的过来给他来了个拥抱。
“我也一样啊。瓦利纳尼。”赵传书说道。然后拉着他坐了起来。
从瓦利纳尼的嘴里他知道在自己离开了平户一个星期以后瓦利纳尼便也离开了平户,坐着闽商的船来到了这里。好在这个时代大明人虽然不喜欢佛郎机人。但是在月港这里还是有天主堂的。所以瓦利纳尼便寄居在这里的天主堂。并等着澳门那边的消息。
一直到半个月前天主堂的消息才通过葡萄牙的一只商船被带了过来。澳门的教庭果然非常的高兴。已经写信给梵蒂冈的教会了。而瓦利纳尼也被调到了大明来工作。并且在写给梵蒂风的信里还对赵传书大书特书。什么东方的先哲、东方的大善人、东方的救世主、圣灵附体。凡是他们能够想到的赞美都不吝的加到了赵传书的脑袋上面。
所以相信到时候教庭回信的时候,赵传书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也十之八九都不会有问题。
“主教大人答应了您的所有要求。不过其中有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他需要请你过去与之商议。”
“没问题。”赵传书兴奋的说道。他没有想到后世的二鬼子在这个时代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请问这次我是随你的船队一起去妈港吗?”瓦利纳尼问道。但是他的话却引来了赵传书的反感,因为他提到了一个词——妈港。
后世但凡听过《七子之歌》的人都记得那由爱国诗人闻一多写的长诗。其中第一句里唱到:“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名姓。”
而MACAU翻成中文就是妈港。这是一个带有强列殖民色彩的一个地名名词。
“当然,当然。你可以乘坐我的致远号一起回到香山澳。”赵传书于是有意的提醒葡萄牙人关于澳门的名称。只是他不知道这个时代半岛的真实名称。所以只好将一个香山澳这个更大的地理名称说了出来。
“哦。”瓦利那尼一听点了点头有些奇怪的说道。
“当然,我以此为荣。”赵传书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笑容。
致远号还有船队在月港停留了三天。赵传书此行除去想要见瓦利纳尼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要见见。
=============================
“赵某在倭国见过贵馆的陈馆主。”赵传书站在一间庞大的屋子的则门对着一个接拜贴的老门夫说道。
“陈馆主?”这个老门夫看着赵传书一身的青衣长衫。如同一个上门找工作的师爷一般:“敢请问是陈元寿馆主?”
“正是,正是陈馆主。我手里还有他的信。”赵传书将他手中的信交给了老门夫。
“你等等。”
没一会儿便见一个小厮将则门打开:“赵大人。陈馆主有请。”
“哦。”赵传书一听,应了一声,便跟着他走了进去。一边走赵传书一边客气的问:“陈馆主从倭国回来了?”
“您说的是陈元寿馆主吧。”小厮一听一脸讪笑的说道。
“这里还有几个陈馆主不成?”赵传书有些奇怪。
“在倭国乃是陈元寿馆主主持。但是在这月港那却是他的哥哥。我们的陈元青馆主管理。”
“原来还有两位陈馆主,小生唐突了。”赵传书没有想到这一个大的会馆的馆主居然是两兄弟。
偏厅里坐了没一会儿,一个比之前在倭国的时候见过的陈元寿年纪大一点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赵大人。”来人虽然年纪比赵传书大。也有着一股久于上位者的贵气。但是为人却非常的和善。让赵传书的好感度大为上升。
“陈馆主。”
“令弟写信回来,极力赞扬赵大人年轻有为啊。看来令弟果然没有说错。”
“这,是大人缪赞了。”赵传书一听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两人于是坐定。下人上过茶以后又客气的几句。陈元青便开口问道:“不知道这次赵大人过来所为何事?”
“哦,传书有一匹货物,当中有一些棉布,数一很少、价格便宜。想拿到闽地给这里试卖。不知道大人可愿意代劳。”棉布,这个将来七海居最重要的拳头货物赵传书是非常的重视。不但将来这个是用来摧毁国外手工业的武器,也是用来整合自己国内制造业的工具。
所以赵传书想试试国内的市场。虽然他的棉布厂还没有出现。但是对于他来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他们。不断的试探市场就是他将来必需不断做的事情。因为明代人其实不太喜欢穿棉布。
“哦,未想到大人也织棉。”陈元青有些惊讶。他原本只认为赵传书是一个有着商人意识的军户而以。没有想到他还发展手工业。
“当然,岛上军户们平日里生活困苦。传书为其找些事情也是帮他们制富。”
“赵大人还……还真是胸怀宽广啊。”陈元青一听突然对赵传书高看了起来。做为闽地最大的商会的管理人员,他如何能够不明白一个封建时代的商人最重要的品质——团结。在这个时代只有能够团结到更多资源的商人才更容易的能够成功,这就是为个什么在这个时代里商帮会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