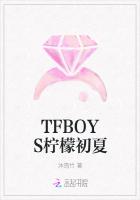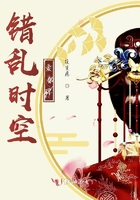《冬天的红棉袄》
有一天,黑渠口土塬上大雪纷飞,
一个穿红棉袄的少妇,
朴素的乡村少妇,踽踽独行,
穿过茫茫的雪地,
多么难得!有一天大雪纷飞,
瞬息淹没荒芜的西部大野,
寂静!寂静的世界几乎空白——
大雪却不能熄灭一件烫心的红棉袄,
一件红棉袄在慢慢移动,慢慢地,
——进入我的幻想。像一团滚动的火焰
她并不带着什么神话,
多年后,我却不能彻底忘怀。
《一个人吼着秦腔从山上下来》
远远地,一个人吼着秦腔从山上下来,
声音沙哑、沉闷,
像是有人故意向他的嗓子里,
扬了一把沙子,
经过一片杂乱的坟地时,
他停了下来,肯定和某个未曾见面的长辈,
打招呼。或者怕吵醒那些沉睡的人,
大约一袋烟的工夫,他又吼起来,
吊在谷穗上荡秋千的麻雀,
忽地一下惊飞,落到了更远的田埂上,
荒草丛中竖起耳朵的野兔,
机警地注意着他提在手里的镰刀和麻绳,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些,只顾吼秦腔,
他的声音将身体里堆积起来的疲乏,
一点一点卸在了路上——
而一只隐藏在树荫间的蝉,
突然加入,使他的声音更加沙哑粗糙,
像两张相互较劲的沙纸,擦伤了,
这个格外寂静的正午。
《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
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我把山说成是穷山,
把水说成是瘦水。我写下的路,
窄小,摇摇晃晃。我写下的阳光太毒,月光太凉,太忧伤,我把蓝天写得太蓝了,把白云写得太白了,把青草和小野花写得太纯朴,太羞怯,像闪到路边的小姑娘,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我把春天,写得缓慢、迟钝,像性情温顺的婆婆,把夏天写得急躁,风风火火,像一个坏脾气的倔老汉。
我把八月的苞谷,看成是腆着大肚子的、怀孕的村妇,把九月的高粱,看成是醉酒的汉子,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我把羊群,写得散漫,从秋天的大洼,慢慢游移进冬天的谷底。把公鸡写在黎明的墙头上,把牛写在黄昏的田埂上。我把驮水的毛驴,写成了民歌手。把鸽子写得像公主,把乌鸦写得似巫婆,我总是描绘不好故乡。我把钻天杨,写得太英俊,一直插进了云霄。把枣树写上断崖,像绷紧的弓。我把柳树的脖子写歪了,把杏树的腰写弯了。我把瓦屋写得低矮、破旧、松动,像蹲在时光里咀嚼往事的老人,我把父老乡亲写成了忙忙碌碌的黑蚂蚁,四处奔波,……我总是描述不好故乡,这让我一直背负着作为一个诗人的羞愧。
《再一次看见柠》
我曾在春天爱上了这些叫“柠”的矮小灌木,
爱上了它有乡村女子一样,
好听的名字。爱上了它细碎的刺,
哆哆嗦嗦的小黄花,
可现在,我在深秋。我目睹它快速地衰败,
一丛一丛,瑟缩在洼地上,
黑黢黢的乱枝,
在冷风中抖动、倾折、喧响。
我目睹,突如其来的早雪,
压低那些细小叶子的叹息。并且耐心地涂改,
一堆一堆岁月的枯黄,
但又很快地融化、消失。从发灰的枝叶间,
滑落。滴答滴答,
我见过的那个穿黑棉袄扎腰带的牧人呢,
散漫的羊群呢,
飞来飞去的鸟雀呢,
是啊!谁也阻止不了它在一场早雪中的衰败,
和萎缩。但我知道,
这一年,它的根须向苦涩的盐碱地,
又深扎了一寸。
《对一座废弃宅院的简单叙述》
窑洞老了,老到局部塌陷和昏黑,
门框老了,老到抱不住门扇,
门扇老了,老到转不过身,
围墙老了,老到豁口、晃动和扑通一声跪下,
墙头上摇晃的狗尾草老了,老到白了头,
墙根斜倚的芦苇老了,老到折了腰,
恩爱夫妻老了,老到一张白纸和一块石碑的背面,牛老了,老到皮革厂的一张好皮子,羊老了,老到牧羊人身上的一件皮夹袄,狗老了,老到一条褥子,杏树老了,老到一个屠夫尖刀下的案板,井老了,老成一根空空荡荡的肠子,木桶老了,老到肋骨松动、瘫痪,石磨老了,老到秃了牙齿,嚼不动一粒粮食,碌碡老了,老到瘦腰、圆滑,拔不出,土里的半截身子。哦!老了。
静静默守的几寸光阴也老了,
老成这荒凉院落里一片片肆意蔓延的苍苔。
《一盏马灯摇晃着穿过漆黑的夜》
漆黑、黏稠的夏夜,一盏灯摇晃——
我猜想,那是一盏祖传的铜马灯,
擦得干净、锃亮,
指甲花一样大小的光芒,摇摇晃晃,
静寂的夜,也被弄得摇摇晃晃——
是在寻找一只跑丢了的馋羊?一个挨了耳光赌气出门的孩子?
一对抗婚,趁着黑暗夜色私奔了的乡村恋人?
是在护送临产的孕妇赶往镇子上的卫生院?还是接一个在外打工的亡灵回家?哦,一盏马灯——一盏开着指甲花那么大一点光芒的马灯温暖的、坚强的马灯让乡村一寸一寸冰凉下来的夜,摇摇晃晃——
《坡地》
坡地是父亲心上一块陡峭的伤,
坡地上种庄稼,下种五斗,收获四斗,
逢个好年景,
下种五斗,收获六斗,
不好不坏的年景,
下种五斗,收获五斗
坡地欠父亲的数担麦子,数年劳力,
坡地上滚土豆,滚背篓,
滚过十岁的我,
滚过一头牛,
坡地欠一头老牛的命,
后来坡地撂荒了。荒了的坡地像是要偿还什么,荒了的坡地上,青草丛生,野花竞开,一堆一堆疯长的野苜蓿,就要漫过羊背。
《和一场沙尘暴同时经过黑渠口小镇》
骤起的沙尘暴,把黑渠口正午的天空刮破了,
把春天的绿头巾刮破了,
把铁匠铺的炉火和叮叮当当的声响,
刮灭了。把羊肉馆的门扇刮得甩来甩去,
把两只铁皮桶,刮得,
哐啷哐啷地滚。把一个瘦老汉和他灰暗的羊群,刮得飞起来,像一团废塑料纸,过了空荡荡的河湾,贴在一面斜坡上,这先于春天的沙尘暴太猛烈,来不及躲闪的黑渠口小镇,习惯性地缩着脖子,弯下了腰,瓦屋弯下了腰,树木弯下了腰,而我,还没来得及揉亮飞沙击痛的眼睛,就和另外一个男人,另外一个包着红头巾的女人。以及一辆摇摇晃晃吐着黑烟的手扶拖拉机,沙子一样,被刮进了心慌的崾岘。
《春天开始》
一只啄木鸟在树干上敲,
风沙刚刚又擦了一遍的土塬,一只啄木鸟的敲击声,多么脆亮。明天,明天之后春天开始。细雨微凉,像针尖,会扎疼大地的胸膛,这些柳树、杨树、槐树、榆钱树,就要爆出细嫩的叶子,这些杏树、梨树、桃树、苹果树,就要打开白色的、红色的、粉色的花朵明天,母亲会再擦洗一遍陶器,父亲要打磨农具,孩子们会背着新书包走进莺歌燕舞的学堂,明天,明天之后春天开始,溪水涌动,爱情发生,春天会带着花朵、青草和露水姑娘姗姗而来。你听——一只啄木鸟在树干上不停地敲。
《飞起来的红屋顶》
一个人爬到最高的山顶,向下眺望,
看他打了一辈子的江山,
高处的风,把他瘦小的身子吹成了一片枯叶,
低处的村庄宁静,矮于层层秋色,
小路依然麻绳一样勒紧山腰,
花开始凋零,草开始枯萎,
一个人,他终于看见了那一小片暗淡的红屋顶,看见了红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在那里,他的女人此刻正扭动着腰身,穿行于琐碎家务之中。儿女们已长大成人,儿女们的儿女咿呀着爬过门槛,开始练习飞翔。这让他心里暖和,留恋。
让他内心的大海顷刻间波浪翻涌,
握旱烟锅的手止不住地哆嗦,
整个早晨,一个人一直蹲在山顶上,
像一只苍黑的老鹰,
俯瞰自己云烟沉浮的江山,
天亦苍苍,野亦茫茫,
那一小片红屋顶越来越亮,越来越亮,
慢慢地飞起来——
《牛车缓慢》
后河湾最后一个赶牛车的人,
死了——
死在了他破旧、松动,吱嘎吱嘎作响的牛车上,说是那一天下午没有一丝风,夕阳红的凄惨,血染了大半边天空,说是那一天下午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辕杆上唱《下河东》,唱着唱着就累了,就枕着车上的一捆嫩苜蓿,安静地睡了——说是那一天下午,后河湾一带的刺槐树花,一下子全开了,粉白粉白,说是那一天下午,他破旧的牛车缓慢,缓慢……刚好适合他的睡眠,适合那条延伸在夕阳里的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
《四月四日访南岔小学》
请让开窄细的山路,让这一队羞怯的孩子,
和他们羞怯的歌声顺利通过,
请推开放学后虚掩的校门,
轻轻敲打房檐下这截发号施令的废铁,
——上课。下课。活动。全体集合,
让静静的校园再沸腾一次。
请扶一把这些刻上“早”字、“勤”字,画上分界线,拐腿的老课桌凳。请关好糊上牛皮纸,钉上塑料布的窗户,为墙皮脱落的旧教室致敬,请为驮回两桶混浊窖水的老麻驴刷刷毛,拍拍它汗湿的脊背。请为戴超厚近视眼镜的校长,穿蓝中山装的教导主任,炒洋芋片的王老师,和批改作业的民办教师小李鞠上一躬,为伸进土墙头的一枝杏花鞠上一躬,为小小春天的探访鞠上一躬。请为飘摇在校园上空的,五星红旗鞠上一躬,深深地鞠上一躬。
《四月》
——四月亮了
油菜花照耀的黑渠口土塬亮了,
那个从油菜花地里慢慢慢慢飞出来的人,
沾满了金黄色的花粉,
她比原来稍微胖了一些。她的素蓝花花衬衣上,弥漫着淡淡的香气,——四月亮了。
蹲在风口子上的堡子屯也亮了,
细细的南风吹,
细细的南风,把细细的绿草,
和油菜花的蜜,
从旷远的河谷一直推送到母亲的篱笆小院。
《柠》
其实叫:柠条子,
但我喜欢叫柠。像低唤一个朴素的乡村女子,
我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去爱
我爱生在这路边的一丛一丛的柠,
我爱它低矮的、暗淡的枝桠和细密的叶子,
以及深深扎进盐碱地里的根,
我爱一枝一枝开不败的小黄花,
在微冷的风里一个劲儿地哆嗦,
我爱叽叽喳喳的山雀子,
从这一丛飞到那一丛。我爱缓慢的羊群,
经过它,爱抚地啃它——
我爱落在这路边的小小的春天。
《狗尾草摇晃的下午》
这是一个掉进秋天与冬天的缝隙里,
——喘息着的下午
灰暗的天空低垂着。感觉有什么要塌下来,
收割后的土塬裸露出无边的荒凉,
狗尾草摇晃着。孤寂的狗尾草,
白了头——
狗尾草白了头的下午,
空空地摇晃着,
大坳里的一个人一锹一锹翻地,
一锹一锹给土地松绑,
他卑微的身子摇晃着。像一株白了头的狗尾草,笨拙,向着风吹去的方向倒下去——这是一个人戛然而止的下午,一袖山风,两手空空,从知冷知热的黄土里来,往知热知冷的黄土里去。
《荒凉的黄家梁》
秋天过后,
那个低头劳作的人扛起农具走了,
黄家梁,
高出几堆黑乎乎的干草垛,
高出荒凉的黄,
有两只老鹰盘旋着,黑石头一样掉下去,
不见了——
有两只乌鸦诅咒着,撞向硬邦邦的北风,
不见了——
有一个饥渴的男人,和一个包着红头巾,
同样饥渴的女人闪了一下
不见了——
秋天过后。荒凉的黄家梁,
高出几堆热乎乎的干草垛,
高出几堆——
在岁月的缝隙里喘息的干草垛。
《傍晚》
初秋的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