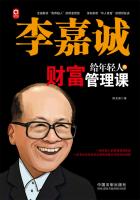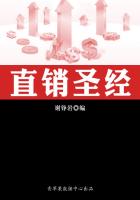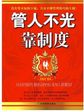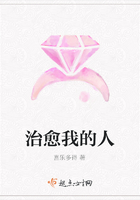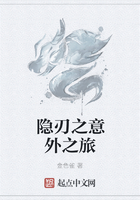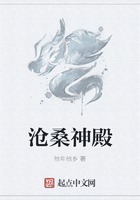在一座著名寺院的大门上有一幅对联,其中的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什么算作难容之事?公正对待异己,在掌握权力的时候,不对曾经与自己有矛盾的人挟私报复,应该可以称为容下了难容之事。
唐朝的名相李泌与宋朝名相文彦博都是不计私情以大局为重的代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随肃宗至彭原(今甘肃镇原东),规划平叛大计。肃宗与李泌谈及李林甫,想命令诸将,克长安后,掘其冢墓,焚骨扬灰。李林甫是唐玄宗后期宠信的奸相,口蜜腹剑,害人无数。他曾谗害李泌,几致死地,按照常理,对肃宗这一想法,他自然会十分赞同。但李泌考虑的却不是个人私愤,他认为若是肃宗为首的新朝廷这样对待以往的怨仇,恐怕会波及安史叛军中的新仇人,使他们断了改过自新、归附朝廷的念头。因此,他提出:“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雠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雠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肃宗听后,十分不悦,反问道:“此贼昔日百万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后在李泌的反复劝导下,肃宗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说:“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文彦博也是一位颇有气度的宰臣。文彦博,字宽夫,宋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仁宗时为相。仁宗宠幸张贵妃,对其从父张尧佐也厚加封拜,当时,谏官包拯、唐介等人激烈抗辞,反对此事。尤其是唐介,反对尤烈,而且还连及文彦博,他指斥文彦博向张贵妃进奉蜀锦,是因贵妃之故方登位宰辅,并要与文彦博当面对质。仁宗一怒之下,将唐介贬为英州别驾,而文彦博也被罢相。
文彦博复相后,谏官吴中复请召还唐介,文彦博不计前嫌,也向仁宗进言道:“介顷为御史,言臣事系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但仁宗不许,仅命迁官。至神宗时代,文彦博已是元老重臣,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之子唐义问为其属下转运判官,颇有才干,惧文彦博报复,欲另寻仕途。文彦博当即召义问解释道:“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所言之事,正当某罪。再入相时,尝荐其父,晚同为执政,相得甚欢。”唐义问闻知后,十分感动,自此,与文彦博成忘年之交,常出入其门下。后文彦博荐唐义问为集贤殿修撰、荆南刺史。
李泌、文彦博都曾位至极品,而能够容纳异己是他们的共伺特点,正是这种容人的肚量使他们做事事成,开创了不寻常的人生大局面。
[智慧方圆]为官做领导的总会与人有一些摩擦,如果把这些琐事当是非的话,你就会有生不完的气。可能有时候别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被你当成了挑刺、找碴,结果一头栽入了是非的泥潭中。还有的时候,确实是他人有心伤害你,但你的反击却产生了“越描越黑”的效果,事情没澄清,却惹来一肚子气。其实在一些非原则性的是是非非面前,我们无须去计较什么,心胸开阔一点,时间自然会替我们证明。谁人背后没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别人说你两句,就让他说吧,只要无伤筋骨。非要和别人较劲,不是给自己找难受吗?做人是这样,做事情做领导也是这样。不过分吹毛求疵、凡事皆留有回旋的余地,对微末枝节的小事不妨姑且放过,这乃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处事为人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