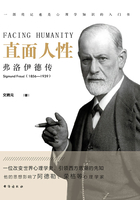三十日,左马介光春来到龟山会合。光是他所率领的坂本军队就已经人数众多了,明智麾下的将士又从各自的领地召集来与其身份相应的人数和家中的孩子,城下挤满了兵马,辎重的车马拥挤在各个十字路口,交通几乎被阻断了。太阳毒辣辣地照射着,那些运货的马夫聚集在商店里,举止粗鲁地大吃大喝,高声叫唤,让人以为是盛夏呢。这会儿步卒们又隔着运送兵粮的牛车斗嘴呢。女孩子围成圈看热闹,脚下的牛粪马粪上苍蝇嗡嗡地叫着飞来飞去。光春在马上看着这一切,觉得景观已经不同寻常。跨入城门一步后更是如此。
光春首先去拜见了光秀:“那之后您身体健康吧?”“你看啊,好得很!”光秀莞尔一笑。比起在坂本的时候,显得和蔼多了,气色也很好。“出发的日程定了吗?”
“稍微延后一点,决定月初出征。我想万事万物开始的日子也就是朔日是最好的。”
“六月一日吗?那么是否已经禀告安土那边了?”“已经派人将这一计划报过去了,可是估计右大臣已经入京了吧。”“听说二十九日傍晚平安进入京都了。信忠公住在妙觉寺,右大臣下榻在本能寺。”
“听说是啊……”光秀声音低沉,话音渐渐消失,不再作声。光春立即起身说:“很久没见内城的夫人和孩子们了,我去看看她们。”
“你先解下行装,好好休息一下吧。”光秀慰劳道。他不知厌倦地目送着堂弟离去的背影,心中的闷气无处倾吐,只好宣泄在脸上。
隔着一间房,在另一个房间里,一看满头白发就知道那人是齐藤利三,他正与诸位将士促膝而谈,地上展开着军事档案和一些文件,他们似乎在热烈地商谈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独自来到光秀跟前问道:“您吩咐的大小行李都在三十日先行发往山阴方面吗?”
“行李?那件事啊。不需要全部发出,一部分就够了。”这时,今天与光春一同到达的叔父长闲斋突然出现,真的十分突然地窥视了一下光秀的房间,东张西望着说:“啊?不在啊。坂本的将军去哪里了呢,到底去哪里了?”这位老人一直那么开朗,他那乐天的表情几乎让人来气。不管是临近出征也好,主公及家臣多么担心也好,明智长闲斋总是改不了爱开玩笑的脾气。主城的诸将把他看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老人。但是一旦他掉转头来到内城的绣房之中,就会拥有绝对的人气,那些女官以及少爷小姐还有他们的玩伴全都聚集过来,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他的周围从不缺少嬉笑声。
“玩笑大人驾到!”“玩笑大人,您啥时候来的?”“玩笑大人,今晚住下吧?”“玩笑大人,请用茶。”“玩笑大人,抱抱我。”“给我唱首歌听听吧。”
“我想跳个舞给你看。”有的坐到他腿上,有的缠着他嬉笑,还有女童看了看他的耳孔说:“玩笑大人的耳朵里长毛了。”“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一边打着拍子唱,一边给他拔耳毛,这时又有男孩子骑到他背上,按着他白发苍苍的脑袋说:“当马吧,学马叫!”“咴儿,咴儿,咴儿!”长闲斋心甘情愿地在地上爬行。他打了个喷嚏,背上的孩子落下“马”来。侍女和保姆都捧腹大笑起来。
光秀的夫人和左马介光春正在里面一个房间谈论着什么,非常肃静,他们回头望了望这边,也跟着笑起来。到了夜晚,这里的嬉笑喧闹依然没有停止。光秀所在的主城和这里大不相同,一边是冰天雪地,一边却是春意盎然。光春离开内城的时候说:“叔父大人年事已高,与其上战场,还不如留在这里照看少爷小姐们,免去将军的后顾之忧。我会跟大将军说明此事的。”
长闲斋回过头苦笑着说:“可能我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这些事了。你看看,他们也不肯放我走。”他把绣房中的人都召集在一起,虽是晚上,也有人央求他讲他熟悉的故事,于是他开始风趣而滑稽地讲述《盛衰记》中的一节。离出征只剩一天了。光春想当晚应该会召开全体会议,结果主城非常寂静,他只好来到外城睡觉。第二天是当月的最后一天,他一整天都在暗暗期盼着,依然没有任何音讯。到了晚上主城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派家臣前去打探,说是光秀已经进入寝殿睡了。“怎么回事呢?”光春感到很可疑,不过也只能睡下了。
翠纱帐中
左马介光春突然睁开眼睛,因为隔着两间房,值夜房间那边传来一阵说话声,将他吵醒了。他感觉睡了很久,估计已经是丑时三刻了吧。过了一会儿,脚步渐渐近了,拉门被轻轻地拉开了。还没等对方开口,光春就问:“什么事?”值夜的武士一直以为他在睡觉,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他慌慌张张地跪拜在地,回答说:“大将军光秀大人在主城等您,说是有要事相商,所以才突然来迎接您。”
“是吗?”光春立即毫不犹豫地起床了。洗脸、漱口之后又梳了梳头。然后一边换衣服一边问:“现在是什么时刻?”
“子时一刻。”“原来是三更啊。”他走出房间,看到漆黑的走廊尽头的杉板门那里蹲着一位白发老人,越发感觉这次意外迎接非同小可。前来迎接的人并非光秀身边的侍童,而是老臣齐藤利三。
“是您老人家啊!”“……哦,不敢当!”
“深更半夜,有劳你了。”齐藤利三拿着火把走在前面。绕来绕去的长廊中没碰到一个人。主城也是夜深人静。只有最里面的一角充满着非同寻常的气氛。有两三个房间似乎有人没睡。
“将军现在在哪里?”“在寝殿。”齐藤利三来到寝殿的走廊口,将火把熄灭了。他将沉重的门打开,用眼神催促光春进去。
光春一走进去,身后的门就被关上了。到寝室之前还有三个房间,只有最里面透出浅绿色的烛光。光秀就在那里,身边没有近臣和侍童。他独自坐在那里,身穿白色便服,旁边放着一把刀。烛影看上去透着绿色,因为光秀的周围挂着翠纱蚊帐。睡觉的时候,翠纱蚊帐的四面都会垂下来,现在只有前面被打开了,像幕布一样挂在撑蚊帐的竹竿上。
“左马介,靠近点儿。”“是。”光春靠上去问道,“什么事啊?”
“这事很重要……你肯为我卖命吗?”光春没有回答,仿佛忘记了自己有一张会说话的嘴,一直都没有回答。隔着烛光,他的眼睛与光秀闪着异样光芒的眼睛依然在相互凝视。
两人都不作声。你肯为我卖命吗?光秀的话简单明了。自光秀到达坂本城以来,光春梦寐之间也在暗暗担心,他预感有一天光秀会败给他自己,说出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光秀终于对自己说出了这句话。光春并没有被这句唐突的话吓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感觉自己周身的血液像冰一样凝结住了。真是个可怕的人,他事到如今才这样看待这个人。
从十二三岁开始,就与他同吃同住,后来又在战场上同生共死,今天才重新认识到这一点,似乎显得过于愚钝了,可是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明智日向守光秀这样的人竟然会想到这样的事。
“……光春,你不愿意?”不一会儿,极为沉痛略带沙哑的声音再次传到光春耳内。光春依然没有回答,光秀也继续沉默。他的脸多么苍白啊!这并不是因为翠纱蚊帐的映衬,也不是烛光摇曳的结果,而是光秀内心的颜色。
如果光春说不愿意,光秀就必须立即执行事先的决定。光春不需要深思熟虑,就直接感觉到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虽然隔着蚊帐,在九尺大床旁边,有个小隔扇,里面藏着武士。藏在里面的刺客的呼吸和杀气,使隔扇上的金粉闪着令人可怖的光辉。另外,右侧的大隔扇外面也悄无声息,感觉刚刚带自己到这里来的齐藤利三正屏住呼吸竖起耳朵偷听。除了齐藤利三之外,好像还有几名提枪握刀的武士同样僵直着身子在听。
光春很显然早已识破了这些。光秀将自己拉到这样的环境下,只问一句肯为他卖命吗,光春窥度他纠结挣扎的内心深处,无法憎恨他的无情和阴险行为。他首先会感到可怜,那么聪明的人,那么富于理性的人,就这样纠结挣扎吗?他现在只觉得所注视的只是那个人的形骸,自己从小就认识的明智十兵卫到底消失到哪里去了呢?
“光春,你的回答呢?”光秀有些忘我地靠过来。光春感觉到他的呼吸有些像重病发烧之人。他这才回答道:“您问我是否肯为您卖命,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很难理解。”他并非想巧妙地避开光秀想要的承诺,也并不是明明看透了光秀的内心却故意装糊涂。他还有一丝不舍,无法舍弃最后的希望,希望能有办法将这个人从那种暴动与不忠的想法中拉回来。然而听了他的话,光秀的眼角几乎要和太阳穴突起的青筋连在了一起。“……这话你要问我吗?”声音也有些不同寻常,他哑着嗓子问,“从离开安土到现在,我心中的郁闷无法挥散,一直怏怏不乐,左马介,你没察觉到吗?”
“基本上察觉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需要多说,只要回答是否愿意就行,先让我听听你的答复。”“将军!”光秀不作声。“将军!”光秀还是不作声。
“您为什么不说话?您在这里说一句话,不仅关系到明智一族的浮沉,还会牵扯到全天下。您才需要清楚回答呢,将军!”
“回答什么?”“您怎么了?像您这样的一个人……”光春眼泪簌簌而下,他刚要将手放在榻榻米上,却突然靠近光秀说,“我从没像今晚这样不理解人类。我们都还年少的时候,在父亲家里同窗共读,读过什么书,学到了什么道理?我国的先贤留下的遗书中,有一字半句可以弑君的内容吗?”
“光春,小声点儿。”“有什么好泄露的。小隔扇后面,大隔扇外面,都是刺客的刀刃,就等您一声令下了。将军,聪明的将军,我从未怀疑过您的睿智。可是,自从在坂本城见到您,感觉您完全变了一个人。您不应该是那种自制力弱的人啊!”
“已经晚了,左马介,要是想劝谏的话还是算了吧。”“我还是要说!”
“没用。”“就算是没用,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很遗憾,太可惜了!”光春趴在自己的双手上,颤抖着呜咽起来。此时,藏着武士的小隔扇咔嚓一声响了。也许是因为潜藏在里面的刺客发觉事情难办,正在摩拳擦掌吧。可是光秀还没有做出任何暗示。他将脸转过去凝望着一边,似乎努力不去看在自己面前哭泣的光春。“您比别人读的书要多一倍,又比任何人都具有理性的思维,您也过了不通晓事理的年龄,又不是个糊涂人,正因为如此……恕我愚钝,想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是就连我这样的人,至少读了忠孝二字也会铭记于心,贯穿于血脉之中。哪怕您胸中有万卷诗书,如果看不见这一点还有什么用呢?”光秀没有回答。
“将军,您可以听我一言吗?我们都是继承了名门望族土岐源氏血脉的人,我是相信一脉相通才跟您说这些的。一旦有辱家门名声,无论是对列祖列宗的灵位,还是对生身父母,都是极大的不孝啊!可是,您现在是多少孩子的父亲啊?”光秀还是不回答。“嫁出去的千金,成为别人家养子的公子,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您一念之间就会让他们以及子子孙孙千秋万代蒙受屈辱,必须这样做吗?”
“要是说下去的话就没完没了了。左马介,我的心意已决,超越了一切。什么事我都考虑清楚了。而且我绝不会放弃。我是忍了再忍,思虑再三才下的决定。算了吧,别再说没用的谏言。你所说的顾虑,也是我每日每夜反复思考过的。唉!我只想说一句话,回顾五十五年来的人生道路,要是我没有生在武门,也不会如此烦恼,更不会想出这样的事。”
“对啊,正是因为生在武门,即便是多么难于忍耐,也决不能对主公那样。”
“就算是信长,也曾驱逐过足利义昭。火烧叡山等诸多恶行也是人尽皆知。你看,他的宿老林佐渡、佐久间右卫门父子、荒木村重等人的下场,我感同身受啊!”
“天哪,将军,您领了丹波六十万石的俸禄,又被赐封惟任这个姓,您也想想如此浩荡的恩典,一门之中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此前光秀如同井水一样,听了这话突然成为奔腾的河流,“这点俸禄算什么?要是我没有才能也不会得到这些。而且,等我完成了使命以后,在他眼里我只是安土养的一条狗,只会觉得我是无用的赘物。他下令让我跟在秀吉麾下攻打山阴,这不是预告了不久的将来明智家的命运吗?我生在武门,作为男人继承了土岐源氏的血脉,岂能屈身受信长驱使,结束自己的一生呢?光春,难道你看不透信长的黑心肠吗?”
光春失望地闭上了嘴,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您的心意都对身边的哪些人说了?”
“除了你之外,对光忠、光秋,还有……”说到这里,光秀松了口气接着说道,“心腹之人有妻木主计、藤田传五、四方田政孝、并河扫部……村上和泉守、奥田左卫门、三宅藤兵卫、今峰赖母……另外还对沟尾庄兵卫、进士作左卫门、齐藤利三等人讲过。”
“只有这十三人吗?”“我有没有提到天野源右卫门?还没有啊?我想应该告诉他了。四方田右兵卫虽然是年轻人,但是我曾吩咐他执行特殊的任务,某种程度上他应该觉察到了我的心思。”
“唉!”左马介光春一听完这话就抬头看着屋顶长叹了一声,接着又说,“事到如今我还能说什么,既然您已经向这么多人透露了。”
光秀一下子靠过来,动作非常突然,他立即用左手抓住光春的衣领,右手握着短剑的剑柄,用令人可怖的力量勒紧光春,问道:“愿意还是不愿意?”光春没有回答。
每次被推一下,光春就像没有骨头一样,仰面朝天,脖子左右摇晃,脸上珠泪纷飞。“要是您还没向其他人透露的话也就罢了,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
“那么,你是答应了?要和我一起起义吗?”“我和您虽是两个人,却跟一个人没什么两样。要是没有您,我也不想活下去。无论是以主从的名义,还是从血缘上说,既然我们是同根所生,共同走到今天,我本来也是打算今后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与您共同承担。可是,话虽如此……”
“不要担心,光春。虽说是孤注一掷、听天由命,既然我决心起义,又跟众人讲了,还是胜算在胸的。事成之后我也不会让你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坂本城,至少我答应让你做几个国家的太守,享受仅次于我的荣华富贵。”
“啊?不,不是这个问题啊!”光春挣开抓着自己衣领的手,猛然将光秀推倒在榻榻米上,“我,我……我想哭!将军,让我哭吧!”
“有什么好悲伤的,傻瓜!”“唉!愚蠢!”
“傻瓜!”
“愚蠢!”“你是傻瓜!”
“你愚蠢!”两个人互相对骂着紧紧拥抱在一起哭了,就那样放声大哭起来。藏着武士的小隔扇后面和大隔扇外面的阴影里都传出了抽泣声。
老坡
无论从气象还是气温看,都已经完全进入夏天了。尤其六月一日出现了近几年罕见的炎热天气。从早上开始就艳阳高照、万里无云,过了中午北方天空被云峰遮住了,然而直到天黑夕阳的光和热还在炙烤着丹波的山河。
龟山城从这一天开始变得空荡荡的,因为数量众多的兵马辎重一股脑儿开出了城外。提着长枪、挎着步枪的队伍,满载着子弹火药以及其他军用品的运输部队,士兵们一个个汗流满面,头上戴着晒得发烫的黑铁头盔,举着旗,背着行李,脚上穿着武士草鞋。一看他们今日就要离开故土,城镇中的人和乡村的老幼都聚集在道路两旁。
“哎?拐角处府上的次郎丸大人也过去了,水池前那家的老爷也骑着马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