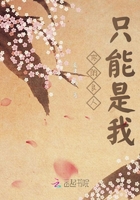如此一来,游民在获得劳动技能、经济上取得独立、成为新的个体的同时,通往社会中心体的道路也向他们打开。1956年,上海市一年之内就有17000多个经过改造的游民走上了工作岗位。其中大部分是回乡生产,并有6000千多人到上海各工厂、企业等单位工作,还有一些志愿去安徽、甘肃、西藏等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自立作新人,上海今年一万七千多游民走上工作岗位》,〔北京〕《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通过对游民进行劳动能力的训练,具备劳动意识和能力的游民被重新赋予公民身份得以再次进入社会,此时,他们所具有的职业身份和阶级身份自动做出调整,游民群体伴随着游民身份的消除而消减。
(三)游民的去阶层化:文化的整改
游民阶层在漫长的形成发育过程中,拥有了本阶层的文化,游民文化不仅根深蒂固,而且维系着并壮大着游民这一群体,因此,游民文化的整改是消解游民阶层的根本。
游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不仅如此,游民文化还对主流文化产生了冲击。王学泰先生认为,游民文化是与孔孟文化相对立的文化,“自宋代以来由于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游民的思想意识也通过通俗文艺作品散播到一般民众中去,因此,才使得许多不是游民的中国人的灵魂中也活跃着游民意识,它与儒家意识和道家意识构成了中国的思想传统,应该说这是极其可悲的。”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6页。,王先生所指的由游民文化滋生出来的各种游民意识,主要是“逞英雄”、“打不平”、“讲义气”、“有办法”以及“威风”之类《怎样认识流氓的丑恶本质?》,〔上海〕《文汇报》1955年2月8日。。就这些意识本身而言,虽然是愚昧和目无法纪的集中表现,但这种意识不仅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甚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行为逻辑。一些会道门组织正是以标榜这种意识为幌子,吸引了众多徒众,而当它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存在时,其暗含的破坏力也是巨大的。
游民文化的一种典型载体是地方戏,其流传的过程,也是上海游民文化不断酝酿和形成的过程。由于游民文化是维系游民群体的精神力量,故游民的改造也就落实到旨在消解游民文化的戏改上。“人民戏曲是以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我国戏曲遗产极为丰富,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继承这种遗产,加以发扬光大,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遗产中许多部分曾被封建统治者用作麻醉毒害人民的工具,因此必须分别好坏加以取舍,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才能符合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
上海游民人数众多,而戏曲界戏院剧种之繁多,艺人队伍之广大,亦是其他任何都市所不及的。据调查,上海共有京剧剧场10个,演员1200人;越剧30个剧场,演员1500余人;沪剧9个剧场,演员近千人;江淮戏11个剧场,演员800余人,维扬戏7个剧场,演员340余人;滑稽戏8个剧场,演员175人:评话弹词100人。此外还有通俗话剧、苏弹、故事、蹦蹦戏、常锡文戏、甬剧、绍兴大班、魔术、大鼓快书、相声,以及不经常演出的粤剧、川戏、潮州戏、崑曲等。这些剧种共拥有剧场100个左右,书场及饭店表演的约百家左右,演员总数8000余人。每天的观众达15万人(电台和郊区场子尚无统计),每天演唱的艺人约5000人,业余的还未算在内《上海市一年来戏曲改革工作的总结》,〔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7月30日。。如此庞大的传播规模与受众,再加上戏剧所特有的娱乐、消遣而非强制性的传输方式,使得游民文化几乎可以做到无孔不入。因此,整个戏改工作受到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全面重视。
1951年,政务院发出”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曲改革指示,首先改戏。5月5曰,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戏改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指示》明确了戏曲改造的方向:“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各地文教机关必须根据上述标准对上演剧目负责进行审查,不应放任自流,……对人民有重要毒害的戏曲必须禁演者,应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禁演。”《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
通过对演出剧目的审查,禁演“坏戏”和不健康的剧目,戏剧文艺工作的内容、性质由此发生巨变。从内容看,这一时期上演的大多数作品都以反映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时期新生活为主题,如昆剧《琼花》,京剧《红色风暴》、《赵一曼》、《智取威虎山》,沪剧《罗汉钱》、《星星之火》、《红灯记》,淮剧《海港的造成》,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诗词谱唱《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李太成主编,《上海文化艺术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文化艺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从出演形式看,曲艺表演走向有领导、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演出,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阵地。而旧社会的“戏子”也被冠以文艺工作者的身份,陆续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反运动、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正如文艺工作者自己所说的:“我们参加了每一项爱国运动,如劳军、庆祝开团纪念、劝购公债等、五一劳动节等大游行,并且也经常做救灾等义演、义播工作。”《感谢人民大救星,翻身艺人上书毛主席致敬》,〔上海〕《文汇报》1951年7月5日。通过戏改,戏剧开始以“为工农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并向大众化、革命化的方向发展,逐渐与游民阶层脱离,曲艺等文艺形式从此负载的不再是游民文化而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化,至此游民完全去阶层化。
综上可见,为了清除各种异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新政府制定了严格而有效的游民改造过程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之下,通过“思想改造”扼灭了游民的腐败性,通过“身份再造”精心塑造其社会主义人民性,最后通过“文化整改”实现了游民的去阶层化。通过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游民整个阶层退出了上海社会舞台。
本文原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探析王合群李国林城市化既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是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器。城市化过程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可以说,“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历程”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然而,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和集中,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激烈的地方,从而集中了人类社会的各种环境问题。
一、人口的城市化与城市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