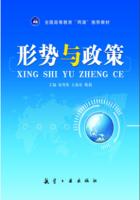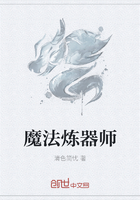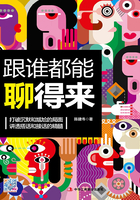江浙军阀战争与上海特别市的发端
任念文
李国林
一、辛亥革命后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开始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人口在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成为中国第一大,远东第二大城市,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上海作为特殊区域的特征已经显现。[1]而在行政隶属关系上,晚清上海只是淞江府属的一个县,清政府设江南提督于淞江。这种行政建制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符。
上海有全国最大的租界,其统治者可以通过租界加强与列强的联系,获取政治资本,求得仕途发达。辛亥革命后,各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上海的工业分布和行业规模均有长足的发展,经济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其发展之路却是畸形的。
北洋时期,上海除正常贸易之外,尤以鸦片进出口的收入为各系军阀所垂涎。自上海开埠以来,鸦片始终是进口洋货中最重要的货物,据海关报告,至1911年,鸦片输入还占上海进口物总值的11%。由于各界人士的反对和国际禁烟大会的压力,公开合法的鸦片进口逐年减少,至1917年3月3日,根据国际协定完全停止,但是非法的私下鸦片交易始终存在,且越做越大。“非法的鸦片贸易早在1916年就同合法的买卖势均力敌,现在它有了自己的地盘,当然规模就做得更大”。[2]除了进口鸦片之外,国内各地所出产的鸦片烟如红土、川土、云土、西土、湘土等也源源不断运来上海,基本由各地军阀用军舰贩运,交淞沪护军使派兵士看守,然后用军用卡车运到十六铺与法租界交界处,交给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人物转销,淞沪护军使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据当事者回忆,卢永祥、何丰林每年此项收入将近百万(钟士澄《齐卢战争的幕后活动》,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仅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税收就足够养三个师(马葆珩《齐卢之战纪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
上海还给驻扎上海的各路军阀带来巨额商业税收。单南市、闸北两市每年的税收就有100万元以上。孙传芳联军司令部月开支达201.46万元。孙仍要求“原来有市政的地方,旧税要积极整顿。旧税以外,还要筹办捐税。原来没有市政的地方,要照闸北、南市的办法,一律纳税”,故在过去经常收入的田赋、货物税、杂税等之外,又增加三种税:一是淞沪宅地税,二是货物增税,三是土布税(由半税增为全税),[3]又为孙传芳筹得了大笔款项。此外,还有上海的兵工厂和军火生产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这些有利因素势必导致上海成为那些视军队如生命的各方军阀的财政支柱,为争夺此地不惜兵戎相见。
二、各路军阀对上海的争夺及影响
辛亥革命后,上海的政权机构“府”制取消,设立沪军都督府,与江苏都督府并存。袁世凯上台后撤去沪军都督府,设上海镇守使和淞江镇守使,各派军阀便开始了争夺上海控制权的斗争。1915年,上海和淞江两个镇守使署合并,改称淞沪护军使,由杨善德任护军使,卢永祥为淞沪护军副使,镇守吴淞。袁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直、皖两派,双方产生争斗。1917年,北洋政府命杨善德任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升任淞沪护军使。杨、卢都亲近皖系,而江苏为直系冯国璋的势力范围,冯以副总统兼江苏督军。皖系极力向江苏渗透,直系决不答应。1917年,冯国璋入京就任大总统,段祺瑞有意让卢永祥以帮办身份坐升江苏督军。冯坚持以直系的江西督军李纯调任。1919年杨善德病死任上,卢永祥升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一职由卢的部下何丰林继任。直系则在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之后,即以齐燮元任“帮办江苏军务”,不久,齐即升任会办江苏军务,李纯死后齐又坐升江苏督军。这样,江苏为直系所控,浙江为皖系所控,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上海,由于护军使为卢永样嫡系,因而实际上便为皖系控制。上海的民政长官名义上归江苏任命,但事实上作为上海护军使的何丰林对于上海的一切无不加以干预,双方围绕对上海的控制权展开激烈的斗争。
由于江、浙分属直、皖等不同的军阀派系,江浙之间的形势不能不受到皖、直、奉等军阀之间既相倚又相争的影响和制约。(见表)虽然直系屡次想用武力夺回上海,却不敢轻举妄动。1924年,孙传芳控制福建,江西迅速投靠直系,形势发生转变。1924年8月齐卢之战爆发,上海因卢的战败落入直系手中,而东北奉系也时刻窥视着上海。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奉系把势力伸向上海,1924年12月11日,北京政府罢免齐燮元江苏督军职,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奉系张宗昌于1925年率军南下,打败齐燮元,上海被奉系控制。同年10月,孙传芳再次进军上海,奉军退出,一直到北伐军进驻上海,孙传芳逃离,北洋军阀对上海的争夺才告结束。
战争使上海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金融市场因人心浮动而发生恐慌,公债狂跌,洋厘暴涨,银根奇紧,钱庄倒闭。随后,棉花棉纱价格暴跌,布匹交易完全停止,物品交易所被迫关门。战火切断沪杭、沪宁铁路后,市面进一步恶化。商业呆滞,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江浙两省二十多万难民涌入租界。[5]据当时人估计,一系列战争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4亿元以上。[6]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同时,战争也完全打破了商界的发财计划,从而引起了各界的不满,他们认为,在上海设护军使驻兵、办兵工厂是招致军阀争夺上海、酿成兵祸的主要原因。因此,上海各界纷纷行动起来,用各种方式要求北京政府裁撤护军使,不驻军,军工厂改为民用工厂,并谋求上海的独立。
北京政府、浙江省、江苏省首脑更迭对上海的影响[4]北京政府任职时间江浙关系浙江上海江苏黎元洪1916.6~1917.7紧张吕公望杨善德(皖)冯国璋(直)冯国璋1917.7~1918.10紧张杨善德(皖)卢永祥(皖)李纯(直)淞江1918.10紧张杨善德卢永祥李纯徐世昌1919紧张卢永祥何丰林(皖)李纯徐世昌1920紧张卢永祥何丰林李纯徐世昌1921紧张卢永祥何丰林齐燮元(直)徐世昌1922紧张卢永祥何丰林齐燮元黎元洪1922.6~1923.6紧张卢永祥何丰林齐燮元曹锟1923.10~1924.11战争卢永祥何丰林齐燮元段祺瑞1924.11战争孙传芳(直)宫邦铎(直)卢永祥1925战争卢湘亭(直)宫邦铎杨宇霆(奉)1926和平陈仪(真)孙传芳孙传芳张作霖1927和平(北伐除外)陈仪孙传芳孙传芳三、江浙军阀混战与上海地区各股力量谋求独立发展的努力早在清末,地方自治的构想在上海就已露端倪。1900年,上海地方士绅革职在籍的李钟珏就已开始研究如何“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以图自强。1903年11月,上海城乡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由上海等县地方士绅自筹款项,施行修桥、筑路、疏浚浜河等公共事业(据《上海自治志·工程成绩表》统计),拥有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用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和地方税收权。总工程局设有议事、参事两会。议事会由议董32人组成,内举一人为议长,议长任期两年,议董任期四年,但每两年必须抽签改选50%。参事会由领袖总董、办事总董、各区区长及各科科长共13人组成。(见《上海市自治志,董事会职员表》,1909年7月,总工程局改为城市自治公所,有关上海地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的一切活动,都己由其负责办理,已初具城市自治的行政规模。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自治公所改组为市政厅,在国家政权更迭动荡的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城市自身的不断发展,上海的城市自治运动从未间断,各种社团组织在城市生活中作用巨大。
江浙战争一触即发,更促使上海各界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国家立法或北洋政府首肯,把上海建成独立建制的行政区划,摆脱战争的威胁。战前,上海的工商界及地方名流推举虞洽卿等人,奔走宁沪之间,呼吁双方勿动干戈,并发起苏浙和平协会。[7]一方面,以城市各经济、政治组织的名义请求军阀将上海划出战场之外;另一方面,向当局争回地方自治权。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县市乡地方各法团、沪北六路商联会先后致电段祺瑞,要求裁撤驻沪之护军使及镇守使两职,撤军上海;迁移兵工厂,以使沪上纯为商场,永杜拥兵害商之苦。1925年1月,上海各公团召开联席会议,电请北京政府饬双方军队离沪,派代表分别与张宗昌、孙传芳所部接洽,以弥兵祸。
英、美、法等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积极反对各路军阀在上海用兵。1923年8月,战火燃烧在即.上海的英美商人致电使馆,要求置沪杭宁于政事旋涡之外。8月,英、美、日、法四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警告,如果战争爆发,外人的生命财产不能得到保障,外交团将采取措施。1924年8月,驻京美、日瑛法四国公使约见顾维钧,要求划上海为中立区,附近30里以内双方不准作战:吴淞口为中外轮出入之地,亦应划出战线之外;各国军舰必要时得自由开至长江巡弋,保护侨民。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驻沪各国海军舰队司令官宣布:黄浦江流域以内为中立区,江浙两军不得在内交火,江浙两方海军不得在吴淞海道航线至高昌庙一带作战,由各国驻沪军舰,分段担任防务。
江浙战争也给宝山、淞江、川沙、嘉定、青浦等地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而纷纷要求划入淞沪特别市。1925年2月,淞江460人分电上海总商会、淞沪督办,请将淞江也划入特别区域;[8]上海浦东同仁会通电,要求将奉贤、南汇、川沙三县划入淞沪特别市。[9]齐鲁之战结束后,诸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上海的自治运动又有所增强,沪南、沪北工巡局先后改为上海市自治公所和沪北市政局;徐湘波等发起组织市政促进会,拟定宣言大纲,商定章程,征求全市市民一致加入,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发起组织“上海特别市市政研究会”,另有人组织“淞沪市民协进会”,共同推动特别市市政之建设,要求上海实施“特别行政区划”的声势日盛。
四、上海特别市主张的初步尝试及命运
江浙战争后,来自上海各界和西方在华势力的巨大压力,北京段祺瑞执政府被迫于1925年1月就淞沪问题颁布三道命令:沪制造局(即兵工厂)改为普通工厂,未改前,移交上海总商会保管;裁撇淞沪护军使;上海附近永远不得驻军及设任何军事机关。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等出于重新调整、控制上海的有利形势,通电全国响应。[10]接着,江苏省长韩国钧宣布上海为特别市,直属中央。2月1日,上海迅速成立特别市筹备会,决定以上海、宝山两县及相关22乡为区域,定名“淞沪特别市”,筹备会致电段祺瑞:“第一,淞沪既为不驻兵区域,其治安之职,商民自行担负;第二,淞沪市之根本法,由筹备处拟定后,经各市乡同意施行”[9:224],具有明显的城市自治的特征。对上海建立特别市的要求,在北京政府内分成两派意见:交通总长叶恭绰等表示赞同,[9]而段祺瑞出于军阀对地方政治控制的目的,不完全赞同,只想把上海变成一个特殊的商业区。
上海各界则不肯就此停止建市的步伐,从1925年1月到6月,实现建立特别市,实行地方自治的飞跃。(一)通过法律程序,建立健全筹建特别市的机构设置,确立建市纲领。2月,新成立的筹备会拟就姍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和《淞沪公约起草委员会章程>.并呈报江苏省长韩国钧批示遵行。该《章程》将特别市“区域”扩展,在原上海宝山县有关系之22市乡外,又加入18市乡,共为44市乡,确定行政区划范围。《公约》规定:“特别市为自治团体,按照公约(处理)本市一切事宜”。(二)扩充、完善建市的民主共议机构,以民主决议的形式确定未来城市的诸多事宜。在早已存在的上海各社团的基础上,成立淞沪市政协会,选举淞沪市政协会委员,并致电段祺瑞,请其收回设立“商埠督办”及“会办”成命,以准地方自治:筹备会还召开会议,就拟订市议会筹备会程序,推举市公约起草委员会委员,推举淞沪特别市筹备主任,推举县议会正、副议长,提议各商会会长为本筹委会顾问等问题达成共识:2月21日,特别市所属各县,乡代表召开百人大会,讨论组织法、区划等问题。(三)确定现代城市自治的性质及行政职能范围,确保国家和特别市之间责权分明。2月28日,淞沪特别市委员会就淞沪特别市之性质及权限问题,致电段祺瑞及执政府内务、外交部长,指出:“淞沪本系商埠,惟特别市筹备之必要,而商埠涉及外交,须有华洋杂处之准备.特别市纯为内政,以永不驻兵及军队不得任意通过为要点。”;淞沪特别市临时市议会成立后草拟的《淞沪特别市公约》,明确规定特别市作为自治性质的政治实体.其主要职能是:“保卫地方治安;发达市乡交通:改良市乡自治:促进市民卫生:发达市民智识:举办模范市村”[9:232—233]:关于特别市之外交,主张“不妨官办,但条例内须明定有民意监督机关”,明确指出外交权力归国家,但必须有市民监督权,城市自治的理论己相当成熟。在上海各界紧锣密鼓地建(特别)市筹备热潮压力下,5月,北京政府公布《淞沪特别市自治条例》命令,允许设立市议会和区议会作为民意机关,淞沪特别市正式成立。然而,为限制其自治权力,坚持设立“区督办”为最高行政长官。由于五卅运动的爆发,6月,段祺瑞政府以此为借口,趁势任命孙宝琦为淞沪市区督办,虞洽卿、李平书为会办。上海特别市在与北洋政府的周旋中,虽获得自治,但离其所确立的自治宗旨相去甚远,仍未摆脱军阀政权对其命运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