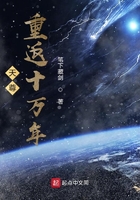这是我还处于十几岁时的年代。细算来,时光穿梭了近八十年。这时国家还不富裕,而这个山沟里掖着藏着的小村子,贫穷程度可以说落后了外界整整五十年。
没有电话,没有电灯,只有裸着身子在泉中洗澡的孩子们,吹着口哨,甩着树枝。
紫陌,却是这群孩子中最孤独却最突出的一个。
她是一个私生子,母亲生前是村里公认的美女,外公精挑细选女婿的时候,十五岁的她在一个晚上衣衫不整的跑回家去,蒙上被子嚎啕大哭,一夜之间精神崩溃,外公懵了,当初门前应婚者排成长队,如今却只剩下冷风瑟瑟。再后来,他的傻女儿肚子大了,却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紫陌出生时,她的母亲就死了。十四岁那年,抚养她的外公也去世了。村里那些憋着气儿的妇人们终是爆发了,明里背里七嘴八舌得说着她母亲是个狐狸精,不知道勾引了多少男人,生出的女儿一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啊,谁又能知道,她的存在是谁酿成的祸吗,说不定就是那些妇人中某一位的丈夫吧。
紫陌在咒骂声中长大,兴许是听“狐狸精”听多了,出落得愈发绰约。十四岁的小姑娘,一袭瀑布般的黑发,俏丽的鹅蛋脸,水汪汪的大眼,小巧的鼻子映着红润欲滴的嘴唇。同时也有着纤弱的腰,润白/丰软的酥/胸。
现在她一丝/不挂的摊倒在裸露的岩石堆上,雪白的肌肤上盈着未干的水珠。清晨的阳光一米一米伴着细微的呼吸在她的酮/体上雀跃,如同演奏欢欣的圆舞曲。
只是紫陌并不知晓,危险就在十步开外。突然,一个硕大的黑影扑面而至,粗糙的大掌猛的滑向下体,紫陌并不懂得这意味着什么,只是那厚重的汗臭味和脚臭味让紫陌一阵恶心,刚欲挣脱却感觉一排带着恶臭的牙齿直撕咬着紫陌胸前的敏感区,紫陌只能感觉到两腿被一双长满汗毛的大腿强行分开,一阵失落感猛烈地撞击着紫陌的心。
倏地,一道黑色的弧线划亮了紫陌的视野,男人猪嚎一般哇哇叫着滚到一边,一片黑色盛开在她们中间,恰巧遮住了她的私/密部位。
紫陌愣愣得望着眼前的黑布,她知道,那叫伞,是外公生前留给她的唯一遗物。
彼刻,紫陌回过头去,涌入眼帘的是一张俊朗的面容,棱角分明,一双深蓝色的眸子,皮肤比紫陌竟要白很多。
紫陌失了神得盯着他,直到一只有力的大手环住了她的身体,紫陌被横腰抱起,男子的指尖划过她的曲线,触到她的敏感点,紫陌一阵难以言喻的感觉,下体不自觉的潮湿。只是这些,她尚且不懂。
她被他环在怀里,问道:“你是谁?”
“Umbrella.”
“什么?”紫陌没能听懂,她想,或许是外地的方言,是叫“安穆泊”吧。
之后,紫陌的世界里走进了一个“安穆泊”,他不爱说话,一身黑色,左胸前一块方方正正的口袋上赘着一朵白色的花朵。紫陌想,八成是家里人不在了,守着丧呢。
“安穆泊”倒不是时时刻刻守在她身边。却在她周围盘旋了多年。
紫陌不知道他的出身,不知道他的居所,不知道他保护她的目的,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
只知道他,总是在雨天出现,在她身后缓缓撑起一把同那衣服一般漆黑的大伞;只知道他,总是在别人欺负她的时候出现,一手拎起那些满嘴脏话的妇人和臭小子们,半蹲在地抹去她的眼泪。
生活就这样持续了一年。春,秋,冬,夏,山中的景色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紫陌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平凡中数着青涩的果,望着澄明的天——生活依然很快乐。
只是紫陌知道,外公的遗产,快要消耗殆尽了。
摆在紫陌面前的只有三条路,嫁给村里的男人;饿死在外公的院子里;翻过前面那座山。
紫陌不知道什么清高,只是觉得,这个村里的男人,她都不想要。
除了——安,穆,泊。
然而命运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齿轮一旦开始运作,洪水就同猛兽一般破堤而入,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他也是在一个夏天出现的。那天没有大雨,没有欺负她的人,没有安穆泊。
紫陌是后来才发现他们的区别的,当半夜他从她吱吱呀呀的床上醒来时,紫陌就已经发现了。近乎一致的面孔,一致的身材,却是不同的人。
这个人像是从天而降的,当紫陌仰头凝视着粲然的夕阳,祈求明天下雨见到安穆泊的时候,一个被荆棘捆得像粽子一样的人从山坡上滚了下来,直滚到紫陌的脚底。
紫陌吓坏了,因为在看到那张脸的一瞬间,紫陌以为那是安穆泊。
紫陌将他拖回家中,脱去他破烂的白色衬衣,为他清理沾满泥沙的身体。而他只是昏迷着,紧闭着眼,紫陌害怕到了极致,因为她以为,安穆泊要和外公一样,离她远去了。
三天的观察后,紫陌渐渐发现了他们细微的区别,仿佛发现了双生子的差别一般。
紫陌想,或许那个人已经死了吧。于是,第三天,紫陌挖了个坟。晚上紫陌累到了极致,瘫在床上,沉沉睡去。
直到感觉身边的“死人”晃动了一下。紫陌以为做了噩梦,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夏日的夜漆黑而温凉,那个干涩的声音贯入紫陌的耳朵——
“这时,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