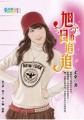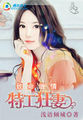著名作家宗璞翻译了一篇小说《信》,其中有一个自私的母亲教育孩子,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要再拆信,信里都是别人的痛苦,不要让别人的事伤你自己的心。这种看法太偏激,或者只是一己之见。
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机器已经影响和控制了人类的命运。电话,传真,手机,短信,网络,QQ和伊妹儿,人们的交流愈来愈讲究便捷、低廉和效率。信件变成了一件珍稀的物品,很多人已经彻底告别了纸质书写的交流。我也很少写信了,像个吝啬的土财主,舍不得自己的笔墨、时间和心情。
这种经典的书面来往,也是一种审美和猜测。单单是来信者的笔迹,或遒劲,典雅,娟秀;或方正,舒展,精致;或是普普通通,潦草涂抹,个性特异,天马行空……通过其中的遣词造句,语气,行文结构以及纸笺的选择,通过这些文化碎片与书写痕迹,我们触摸到了对方的汗渍和呼吸,仪态和气质,意志和味道,还透析出对方的素养和深层心理。像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便是这类典范。
所以,我怀念唐诗的“红叶题诗”、“棉袄藏书”和宋词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鱼传尺素”,悲苦之中的巧妙,惆怅之中的期望,全凭了这些特殊的载体。沧桑的历史和漫长的时光因为这些易逝的书信而留下了永久的惊艳。
读大学时,我喜欢写信。没钱了,修封家书回家,过几天就会准时收到父亲寄来的汇款单。大学三年只学到写信的功夫。我能把信封的张把纸写成一件“艺术品”,书法和文采都很优美,还不忘点上一句温馨的祝福。我可以在无聊的课堂上将心情写得很美丽,也能在喧嚣的人群里将信写得很宁静。常常,静谧的夜晚明净的灯光,在书桌前忙完了一天的事,还无睡意,信就不知不觉写开了,给东西南北的狐朋狗友。这太随便太放肆了,没有任何羁绊和束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喜就笑,有泪就哭。也许被现实的桎梏锁得死死的我们,只有这时才是自由的。或相互取娱,捎给朋友一片晴明的心境;或书生意气,一番鸿篇长论,激扬人生,指点江山;或愤懑寡欢时,从繁杂的心情里抠个洞,化作墨水泼出去,换得如释重负的舒畅与轻松。有道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就能得到两份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俟修好书信,室友的鼾声已和夜色一样深沉,我将信件连夜一起投入邮筒,还了一桩心愿似的,平澹的生活因此味道浓郁了。
信,生命与心灵在纸笺上的投影。海内存知己,添有信件往来,天涯遂成比邻,这不是一句空话。有信自远方来,我急猴似地撕开信封,打开纸张,快速地读完朋友的文字,然后再细细地品读,回味,想象,推测,如饮糖饴,甜在脸,甜在心,与孔子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样美妙。过几天,我又拿出信件温习曾经封存的温度。收获颇多,随时撷得情感的抚慰、真诚的启迪、独特的思想和深邃的哲理,胜于读书。时常几天无信,便有种失落感笼罩心头,剪不断,驱不去,收到盼望已久的信件,则有拨云见日的感觉。我们的交流和探讨就在你来我往中展开了。
以后恋爱了,信件就成了我们传递情感的使者和载体。一页一页的的纸张和一封一封的信件记载了我们的柔情蜜意、思念的苦痛和对未来的想象。有些话语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虽然爱情会凋谢,但信件替我们保存了一切。
我收藏了很多信件,朋友的,老师的,作家的,书法家的,领导的,他们的信件就是另外的一种作品。不妨,偶尔抛开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给远方的朋友写一封信,这是一个意外。有时候,在江湖上,信件也是一件很有杀伤力的武器。
技术时代的统治下,交流变得机械化和程式化了,工整的印刷体,统一的没有个性的冷漠,快餐式的匆匆而过,我们的性灵正在慢慢的丢失。我想,自今以后,当代文学馆关于作家的信件和手稿收藏将会越来越少,甚至灭绝,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