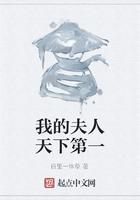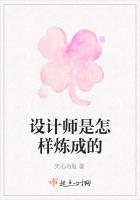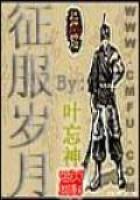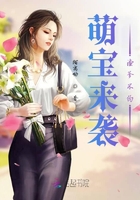乡下中学因其僻远,独得幽然宁静之妙,就像喧嚣之外的一座岛。
校园依山而筑,蹲于小山脚下。山像一把藤椅,校园稳踞其中。山是浅山,有了校园的点缀,风景的内容就厚实了,寂寞的倩影便灵动了。校园也因小山的扶仗,便不怕风凄雨苦,经岁月冲刷,也依旧是灵气活现。有山,便多树。树是青松,也有翠竹,最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两种植物,把偌大个校园烘托得智慧无比。校园内也多是粗而壮的梧桐树,躯干虬曲如龙,枝叶郁郁如盖。阳光被枝叶分割成一片片粉红色的暖意。啁啾的鸟声和琅琅的书声一起溢出山外。屋舍错落有致的是校园,视野平坦开阔的是田野,有收有缩,显得含蓄而有风度。我的书房就藏在这小山脚下、绿荫之中、田野之侧。我且享用这无边的清香和书香了。
书房极陋,仅一桌,一床,几百册藏书而已。桌上摊着的是书,床上躺着的是书,我心里惦记着的更是书。书,日子因你而有味,梦因你而绚丽,生活因你而充实,汗洒于斯,血流于斯,情汇于斯。一位作家曾说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喜欢读书,所以要将他置于死地,就干脆剥夺他读书的权力。我亦是,失去了书便失去了味道失去了绚丽失去了充实,也失去了生命。
书是我通往天堂的阶梯。
书房外的田野更是一本大书。透过书房的窗户,可举目远眺,俯赏田野。一俟春光,大片大片的紫云英像彩云一样,绕着书房,更有那花蝴蝶和小蜜蜂,姿态翩翩,嗡嗡嘤嘤,似在这阔大的舞台上,跳舞,唱歌,或吟诗。春耕的牛哞声常常飘进我的书房内,把我从唐诗宋词中唤回,而后我又会乘着屈辕犁深入到远古的岁月。农人们插秧最忙的时候,我却在吟诵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入夜,我便坐在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密密匝匝的蛙声之中,倾听着寂静之中的热闹。每每读书至凌晨,陪伴我的只有这天籁般的蛙声。夏天的窗外艳阳当空,一野翠绿,农人们“锄禾日当午”,我却躲在暑假的绿荫里,一杯凉开水,玩味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秋天的田野最具风致,金灿灿的稻谷低下了沉沉的头颅,等待着镰刀的亲吻,等待着机器宏大的声音。我却在秋风中收获思想的稻穗。
窗外,既有自然的写实性,又有文学的浪漫性。春的空濛,夏的绿浪,秋的金黄,冬的凋敝,各有三昧。无需音乐,每天都有蛙鸣盈耳;无需彩电,每天都有品不透的景致。我的窗户始终敞开着,淘气的雨滴会蹦进来,任性的月光会泻进来,可爱的雪花会飞进来,迷蒙的雾霭会漫进来,落寞的山风会飘进来,明媚的阳光也会蹭进来,无需出门,我就享受到了自然的恩赐;无需翻书,我便能撷取到生命的智慧。
这是一块清凉界!犹如面对泰戈尔老人,犹如打开《新旧约全书》。
瓦尔登湖一样拙朴的乡下中学,尽天利、地利、人利之便,占尽风韵,可“坐看云起”,“闲中立品”。我诗意地栖居在这样的天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