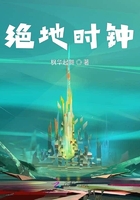“想不到这处种植园居然如此庞大。”封郁萍借口要商量避而不见,整日里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练万户这个吃货当然不在意,但张宸洮却闲极无聊随意的在庄园里四处走动,结果这么一走却发现封氏的种植园远比自己当初看到的更加广阔。
“恐怕少说有三个男爵爵领那么大。”护卫在张煌身边的一名总督府侍卫如是判断着,大华男爵授予一屯之地约计五千亩山林,三个男爵领也就是一万五千亩、四十平方里。“若是那封老儿不知趣,大人断他个逾制也不为过分。”
“逾制?”张宸洮一点也觉得这个笑话不好听。“地方官难道不知道吗?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再说了,强扭的瓜不甜呢。”说到这,张宸洮的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座建筑。“那是家庵?”大华早年就对僧道等有明规,州有下院、县有小庙、封爵或富庶功民或可设立家庵,但是大华对度牒的管理一向严格,封爵又担心朝廷的猜忌,因此家庵倒也并不常见,更何况此地的信仰是小乘佛教,难不成封家延请了一位异族的僧侣,对此张宸洮不禁有了一丝的好奇。“走,过去看看。”
走到庵前,张宸洮抬头仰望,门楣上并无庵名,使人敲敲门,却无人应答,张宸洮随即一推庵门,门扉应声而开,张宸洮迈步走了进去。小庵不大,也是普通的庭院结构,中间是一眼池塘,有几片绿萍漂浮,几尾小鱼在中穿梭。
从左侧的回廊走过去,最左边的屋子里布置有书架、牙床、琴几还有一张山人远行图,图上题字: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张宸洮深深的嗅了一口,檀香中一丝脂粉的味道,再看看这边柔婉的字体以及易安居士的《凤凰台上忆吹箫》的片段,张宸洮明了的点点头,这是封家女眷的读书地。
张宸洮退出西屋,关上房门,继续沿着回廊向前转折,眼前就是客堂,不过现在应该叫做佛堂才对,屋子的中间供桌,供桌上有一佛龛,龛中有一尊杨枝观音的木像,像前香炉里香灰半满,再联系四处干净的陈设,显然此地主人是经常要来的。不过供桌前只有一个蒲团,显然主人也是不愿意和他人分享这个私密场所的。
“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
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
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杨柳不计秋。
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度人舟。”
当年武王张煌不信神佛,但是并不意味着张氏子孙不崇佛礼道。尤其是张宸洮,一方面是海军出身,大海之上无边风浪,恍若苦海,即便不信佛也常年要跟着老水手们口念南海观音法号,祈求风平浪静;另一方面张宸洮此刻也有所求,自然希望神佛庇佑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因此看到观音像,张宸洮当然要礼拜,于是他先从供桌上取来三支檀香引燃,冲着菩萨再三顿首,随即跪倒蒲团上,默默的祈求了一会,随即拜倒在地。
礼拜过后张宸洮退出佛堂,转入右手的走廊,不过右厢房却是关着的,张宸洮自然不会做梁上君子强行入内,于是直接走出庵堂,看看天色,似乎又有一场西洋夏季常见的阵雨正在酝酿中。“走,回去吧。。。。。。”
“主上,那封老儿显然是不准备答应了。”张宸洮在封家有住了五日,一开始封郁萍说自己要好好权衡一二请张宸洮再稍等几日,接下来封郁萍又说家中突然出了急务要处理希望张宸洮再住几天,最后封家又说封郁萍有恙需要静养,这么一来即便是练万户也觉得对方是在施展拖字诀。“主上,封老儿不知好歹,咱们也用不着这么干耗着,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难道就吃带毛猪了?”
“也罢,”张宸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点头,人是不可能事事如意的,既然封郁萍不愿意,自己是没有必要在此地白白浪费时间。“老练你去和封家打一个招呼,咱们既然光明正大的来的,自然也不能偷鸡摸狗的走了。明日一早,咱们就走。”练万户抱拳领命而去,看着练万户的背影,张宸洮还是不令人察觉的叹了一口,他站了起来冲着几名侍卫吩咐着。“本爵走一走,你们不必跟的太紧。”
侍卫们知道张宸洮碰了个软钉子心里不好受,因此也不敢触霉头,因此只是远远吊着张宸洮的后面,张宸洮慢慢的走出居住的院子,漫无目的的走着,不知不觉走出去很远,然而天上的云彩变幻,乌云聚集,眼见的又要下雨了。
“啪嗒!啪嗒!”几粒雨滴落到了张宸洮的身上,张宸洮猛然一醒,抬头四下一望,只见附近最近的建筑远在半里之外,就这么一耽搁,雨就噼里啪啦的下了起来,张宸洮无奈,只好向刚才看见的建筑跑去,而远远吊在身后的侍卫也被铺天盖地的大雨阻断了视线,一时半会找不到了张宸洮的去向。
张宸洮跌跌撞撞的来到建筑物前,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来过的封家家庵,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再加上摔了几跤之后,身上泥水一片,狼狈不堪,于是他也不管不顾,随即推开门闯入院中,可一进去,就听到廊下有女声响了起来。“哎!你是什么人呢?”
张宸洮摸了一把从头顶上流入眼睛的雨水,定眼观看,只见一个高挑的女奴一手插着腰,一手指着自己责问道。张宸洮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狼狈,也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道。“我是此家的客人,正在散步,不巧遇到了大雨,记得前次曾经来过此地进香,所以冒昧前来,不知道大姐在此,冒昧了。”
“前次来此地进香?原来是你。”女奴顿时大叫起来。“好一个小贼,巧言令色,这是封家的家庵,是你一个外人可以来进香的嘛?害的上次我被责骂,终于抓到你了。”
张牙舞爪的女奴准备作势来抓张宸洮,还没等张宸洮反应过来,一个柔美的声音从左厢房里响了起来。“阿蛮,不要胡闹,这是爹爹的贵客,去,打一盘水来让这位先生在右厢房里洗漱一下,等雨停了,再请这位先生出庵。”
“多谢这位小姐。”张宸洮向声音的方向到了声谢,随即在撅着嘴阿蛮引领下来到上次没有进入的右厢房,进去才知道这是一间浴室,自然是不能让人轻易进入的,张宸洮也是在海上吃过三年苦的,只见他先是用热水洗了洗头脸,随后接下外衣用清水搓洗了一番,然后挤干水分,找个根绳晾了起来,至于贴身的小衣和亵裤什么的自然无法解开,不过张宸洮正值青壮年,底子又厚,一会就利用人体自然的热力蒸干了衣物上的湿气。然而雨却没有停,稀里哗啦的,一直下着,天色也越来越黑,隐隐约约对面的厢房里已经点燃了蜡烛。
给,送给你吃的。”不一会对面送来了一份清淡饭菜,从阿蛮不高兴的眼神中,张宸洮明白是对面那位小姐节省下来的。
张宸洮接过饭菜,放在地上,回头穿上还有些湿漉漉的衣服,在阿蛮怀疑的眼神中,走到左厢房的门口,隔着门扉冲内一稽首。“多谢这位小姐赠饭之恩,但不知小姐乃是封老爷的何人,在下该如何称呼?”
张宸洮跟潘庆安早就打探清楚封家的底细,封郁萍有三女二子,长女下嫁同州秦氏长子,生有二女,但六年前夫婿亡故,因与继承家业的小叔之妻不和,一怒之下携二女返回母家居住,长子获得功民资格后就留在家中操持家业,次子尚在军中服役,二女新嫁,三女年方十六尚待字闺中,所以张宸洮才有此问。
“我家小姐跟老主人怎么称呼关你什么事,少来凑近乎。”阿蛮明显不是华族,但是这话说得利落,显然不是家生子就是丽奴。“走开,回去吃你的吧。”
“阿蛮。”里面小姐斥责了阿蛮一声。“民女乃是丧夫不祥之人,先生还是不必多问了。”
“原来是封老大人的大小姐,在下失礼。”大华虽然对儒教并没有彻底打倒,但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却从武王时代就被定为伪学了,因此寡妇再嫁在大华也算平常,倒是一怒之下就携女儿破门还家在当时并不多见。“不过大小姐既然是信佛的,当知道生老病死乃是宿世因果,又何必念兹在兹呢,如此执念又如何可以超脱苦海。”
“先生倒是佛法精深。”对于张宸洮居然知道自己,封家大小姐却十分的意外,更意外的是张宸洮对佛学的研究,她是不知道各家各派为了在宫廷中获得一定的影响,无不派遣大德高僧或有道全真为王家服务,因此张宸洮了然佛法倒也不奇怪。“民女失礼,还没有请教先生尊姓大名啊?”
张宸洮正要回答,突然原本半合的庵门被人大力的推开,几个同样浑身泥泞的汉子闯了进来,还来不及抹去眼前的雨水便大声探问起来。“侯爷,侯爷可在里面!”
“噤声!”张宸洮立刻大声的回应了一句,冲着屋内之人歉意的点点头,扭头走到廊下。“封家大小姐在,尔等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是!”几个人将张宸洮的声音听得分明,一个个顿首应声。
“你是总督大人!”死死盯住张宸洮的阿蛮忽然明白过来,眼前这个人就是家中最近几天议论纷纷的新任侯爵总督,不由得捂着嘴大惊失色。
“还请阿蛮姑娘替我的几个伴当打水洗漱一下。”张宸洮默认着,却不知道走到纱窗前听得仔细的封家大小姐此刻也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