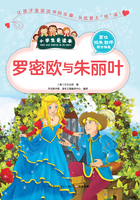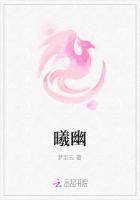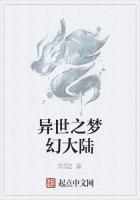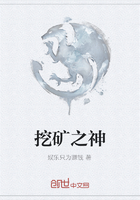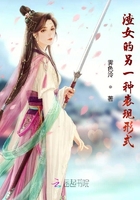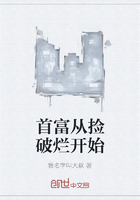1.主体力量的交换
《假面》(Persona,1965)通常被视为一部“难懂”的电影,同时也被视为伯格曼最杰出以及世界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电影之一,还有人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无论如何,不管是对导演伯格曼个人而言,还是对世界电影艺术的整体而言,《假面》都是一部非同寻常的电影。它的杰出不在于对情感或生活——艺术作品的恒常主题——的再一次率真的呈现或描绘,而在于将一种几乎完全是哲学的探讨用电影这种通常被认为是娱乐大众的媒介来加以呈现并最终使之成为一场手法高明的影像呈现。并且,《假面》作为艺术作品的杰出之处同时也是隐晦之处还在于,尽管自它问世以来就阐释不断,但它的意义却似乎永远没有穷尽的可能。这些意义也许连它的创作者自己也未能完全意识到,却令这部创作于四十多年前的电影迄今仍在遥远之处闪烁着令人难以抗拒的光芒。可以想见的是,这迷人的微光将会抗拒时间抗拒空间抗拒一切地闪烁下去。
就影片的故事核心而言,它呈现了一场关于言语与沉默的力量性对抗与交换。
伊丽莎白·佛格勒是一位决定保持沉默的舞台演员,而影片并未向观众提供一个她之所以要保持沉默的确定理由,我们既可对此进行各种经验性的猜测也可对此置之不理。由于住院对伊丽莎白的情况无效——在这里,伊丽莎白显然是一个患有某种心理障碍症的病人——她的精神病医生建议她和护士艾尔玛一同前往自己位于海滨的小别墅休养,影片就此展开。在那个空旷荒芜如月球表面的海滨,病人和护士之间发生了一场介于梦幻和现实之间的力量抗衡:面对伊丽莎白的沉默,艾尔玛不停地述说并最终在喋喋不休的述说中耗尽了自身。但这并不能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胜利或者失败,因为伊丽莎白的沉默也终将被证明为一种比语言更为虚弱的装饰,其虚弱正如同她的医生的告诫,一种角色而已。在力量的抗衡与最终形成的力量交换中,语言的地位显得尤其可疑。
在言语与沉默的对抗、交换中,不仅意义仿佛丢失了,而且时间也处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时间被分割为表面上的流动(实际发生的电影放映时间)和实质上的凝滞(叙述时间),观众不是被时间领进了某种线性运动或序列运动中,而是被领进了某种被呈现的状态之内。不过这并非电影就时间所进行的一种错位叙述——伯格曼的早期电影《野草莓》便是对这种简单然而有效的时间错位叙述的出色运用。在错位叙述内运动的时间往往显得更为立体、多维,而在《假面》所呈现的那种状态之内包含着的时间则是不连续的,成为了一种散点元素。
正是在时间与意义的离散之中,构成一个故事的大量背景信息被忽略并被去除,例如,关于《假面》的两位女主人公,决意保持沉默的舞台演员伊丽莎白·佛格勒和护士艾尔玛的故事性背景不再成为某种必要,我们知之不多。她们也因此很快就溢出了伊丽莎白和艾尔玛自身,成为了两个被言语的聚光灯紧紧追踪并展示着言语或沉默的女人——她们成为了两个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在挣扎中抗衡的言语个体。
伊丽莎白的沉默首先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叙述背景,其他的一切都在此背景之内展开。她的沉默诞生于一次演出之中:在演出中途,她站在舞台上突然停止了说话,她沉默了一分钟,惊讶地看着四周,好像想笑,演出结束后她便进入了沉默的状态。正如同泡沫诞生自大海的深处,伊丽莎白的沉默正诞生自言语行为的大海——舞台演出之中,因而,由她的沉默所体现出来的对语言的否定意味也就来得尤其强烈。
在文本中,为了完成一场叙述,必须形成某种强度的叙述能量,而此片中叙述能量的形成显然无法完全回避对伊丽莎白的沉默的解释。因此在影片的开始,她的精神病医生即以一种相当自信的口吻向观众交出了一份听上去颇为权威的解释:
生存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望的梦……每一个音调都是一个谎言,每一个手势都是一次伪装,每一个微笑都是一次掩饰,然而,自杀么?不会……但是你可以拒绝行动并保持沉默,至少你将不再撒谎……不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我明白你为何沉默,为何不再行动,你的了无生气成为了一个荒谬的角色……我想你会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直到它不再有趣,然后你就可以抛弃它就像你抛弃其他的角色一样。
这是一个精神分析医生对伊丽莎白的沉默的理解,她的话代表了从心理学展开的居高临下的诠释。而在心理学之外,这个解释显然也还代表着20世纪法国的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对存在之本质的理解。因此在接下来的海滨生活的开始,艾尔玛对伊丽莎白半懂不懂地读了一段显然是从哲学书中摘录的话,这段话与医生所言则恰成前后印证:
我们的焦虑、破碎的梦想、无以名之的残忍、对死亡的恐惧、对自身的现世处境的痛苦觉察撕碎了我们对神圣救赎的渴望,而我们对信仰的哭泣、对黑暗的怀疑和沉默便成为了我们的孤独和恐惧的可怕证明。
这段话把对沉默的意义的解释从心理学推进到了哲学,伯格曼就此再次预先强化了对沉默的背景性解释,这些解释在文本当中形成了一个足够强度的叙述能量来推动叙述的进行。然而,随着这叙述能量的推进,影片却同时构成并隐含了一种张力与抗衡。
随着影片的呈现式的展开,在那预先强化并强行赋予的外在解释力量的框定中,伊丽莎白的沉默却逐渐获取了对自身进行表白的力量——即便这力量仅仅是个体那脆弱的勇气,即便这力量唯一能表白的便是自身的虚弱;她的沉默的力量曲折地但却坚韧地展开,这展开并非逐步增强而是逐步虚弱;她的“沉默”与“解释”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她的沉默不断地抗衡并最终突破了外在解释对她的无情框定,而那叙述能量则因此被迫消散。不管定义为何,最终是她定义了自己。“意义”的生成并不是在现成的框架中,而是在它自身的运动中,在它的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中,在它奔赴自身命运终点的饥渴的趋向中。沉默的意义也同样如此。沉默并非静止,沉默的意义必须在动态之中才能确定并得到呈现。
艾尔玛的开始言说是一种职业性的需要,一种模糊的治疗的需要。她仿佛试图用自己喋喋不休的言说来形成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去“诱使”伊丽莎白开口,因此在一开始,在护士与病人、言说与沉默之间便隐约形成了张力和对比,然而在持续的言说和沉默中,双方的身份区别却开始变得模糊,言说与沉默之间的力量对比则变得突出而醒目。
正如伯格曼在自己的构想中对伊丽莎白的沉默的理解那样,“她强加给自己的沉默绝不是神经病,那是一个强者的抗议方式”。从一开始,艾尔玛便对沉默产生了敬畏,她对医生说:“如果佛格勒太太的沉默是她的决定,那可真是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我可能对付不了。”沉默的力量的最初来源是它的不为人知——人总是对自己不知道、无法知道或不敢知道的事情保持着一定的畏惧或敬畏直到自以为了解才得以解除,人也总是在对事物的所谓本源的无尽追索中徒然消耗着自己。这就像一个魔咒。伊丽莎白的沉默构成了一个仿佛可以不停地、无止境地进行吸收和容纳的虚空并因为此种虚空而显出了人所畏惧的力量,所以艾尔玛会认为那是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而言说,作为语音和声调的一种物质构成,相对于这种具有非物质性、仿佛不存在界限的虚空而言更像是一种边缘确定的凸出物。因而言说与沉默的关系正如同容纳与被容纳、进入与吸收一样,既充满了张力,也充满了脆弱的平衡或者说脆弱的不平衡。
在言语和沉默所形成的默然对立中,一些平常司空见惯的事物的“言语性”则在一种不平衡中得到了奇异的凸显:从收音机里传出的无聊的广播剧(引得躺在床上默然不语的伊丽莎白发出嘲讽的微笑),从收音机里传出的抚慰人心的音乐(伊丽莎白陷入痛苦的思索中并流下了泪水),电视里关于越南暴乱的新闻播放(伊丽莎白退缩在墙角,惊恐不安地捂着嘴),伊丽莎白的丈夫寄来的一封信(艾尔玛读给伊丽莎白听,但未等听完伊丽莎白便将之夺过并撕成两半)。在这些经过了挑选因而不那么“公平”的凸显中,在沉默的对照中,声音和语言仿佛极其缺乏抵抗力,极容易与无聊、暴力、死亡、痛苦、隔膜等令人不安的元素发生交叉污染从而污染了人,或者反过来说,人仿佛极容易被声音和语言所污染。因此,当人言语时,在无聊、暴力、死亡、痛苦与隔膜中人不仅容易伤害他人而且也容易伤及自身,就此而言,沉默似乎可以被视为一种比言说更可靠、更能避免伤害与被伤害的生存方式。
面对病人的沉默,护士艾尔玛开始习惯于独白。当对象虽然真实存在却沉默不语,当对象虽然不能形成言语上的反馈却具有无比强大的容纳能力时,个体面对沉默的述说便会成为一种被完全容纳的独白。因为获得了一个具备沉默的力量同时又具备极聪慧的理解力的倾听者,艾尔玛变得毫无戒心,她的独白也因此逐渐演变成了滔滔不绝的倾诉。这倾诉显然是坦诚而温情的,艾尔玛因为自己的被倾听而感到安全、温暖和美好。在倾诉声中,言语与沉默、护士与病人的关系逐渐淡化,并逐渐演变成言说与倾听、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的关系,而其中的帮助者与求助者也由此互换了位置。
艾尔玛显然是被这种痛快的、毫无保留的倾诉行为迷住了,她诉说着自己与情人和未婚夫的关系,倾倒着自己那隐秘恋情的难堪、对沙滩上放荡的性狂欢的忏悔和随之而来的流产的痛苦。她不分昼夜地沉浸在倾诉里,我们甚至不用去区分这些关于倾诉的场景是断续的还是连续的,是同时的还是异时的。在这场倾诉的滂沱大雨中,艾尔玛终于倾空了自己——通过不可遏制的言语,她将自己完全倾入了伊丽莎白的沉默之中。因为这倾空也因为人对事物本源那无法遏制的渴求,这场漫长的倾诉最终演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一场徒劳的追寻,演变成了对生存的痛苦质问和由此引发的歇斯底里般的痛哭。
然而,正是在倾诉和倾听中,这两个女人已经使言语和沉默从隔膜式的对立形成了“进入”与“包容”的和谐并结成了一个暂时、隐秘而温情的同盟,影片将此种同盟关系表现为两个女人头颈相靠的亲密偎依。当然,我们还可以将言语和沉默之间的这种同盟关系理解成其他更为大胆而隐晦的隐喻,例如同性与异性之间的敌对与同盟。言语与沉默的这种同盟性同时包含着伯格曼对语言、欲望、利比多、性和性别之间那乱麻一般纠缠不清的关系的隐晦探询。
但是,这同盟关系却被一封所谓“泄露真相”的信迅速打破。艾尔玛偷看了伊丽莎白写给医生的信,伊丽莎白在信中认为艾尔玛可能已经不自觉地爱上了自己,并且说“对她的研究很有趣”,“她声称自己的感知和行为并不一致”。这封信在艾尔玛心中掀起的轩然大波使她们之间力量的对比顿时发生转折。
虽然伊丽莎白的信中所言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错误——倾诉者确实可能已经爱上了倾听者,就像凸起物热爱可容纳自己的虚空。但是,艾尔玛的震怒所源并不是当中可能的错误,而在于被“出卖”与被“背叛”的感觉。在此需要进行仔细探讨的是:艾尔玛是被什么所出卖,又是被什么所背叛?
在表层意义上,艾尔玛是被“言语”所出卖:信——言语——伊丽莎白的言语——艾尔玛的隐私被伊丽莎白的言语出卖给他人。但是,这种所谓隐私的被出卖确实只是一种表层因素。
比被“言语”的出卖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被“情感”所出卖:言语——倾诉与倾听——亲密情感的形成——情感被“言语”撕破——情感的出卖。倘若自以为处于一种亲密的、几乎结为一体的关系之中而实质上只是被对方当成显微镜下的细菌来观察,这确实可称为一种可怕的、令人震怒的情感的背叛和出卖。
然而,还有一层比“情感”的背叛与出卖更深刻的原因:艾尔玛是被“沉默”所出卖。艾尔玛已经预先赋予了沉默一个高级的位置并对之毫无保留地用言语倾空了自己,但沉默却并不是她当初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可信赖、可敬畏的不变体,却是一个与言说的无赖本性相同的可变体——艾尔玛终于被自己信赖的沉默所出卖。因为被沉默出卖而不仅仅是被情感和言语所出卖,艾尔玛的倾空顿时变得毫无意义,被沉默出卖使艾尔玛的生存本质突然显得那么岌岌可危。
因此,被这封信泄露的唯一有价值的“真相”便是伊丽莎白的沉默的言语性:原来沉默不过是言语的一种把戏,而那令人敬畏的虚空也不过是空虚的一个变体。魔咒得以解除,敬畏由此消失,艾尔玛变得无所顾忌,而她从无所顾忌的愤怒之中获得了比伊丽莎白的沉默更为强大的对抗力量——当言语与沉默都同样显得形迹可疑时,凸出而尖锐的言语显然比空虚的沉默更具有攻击性。针对伊丽莎白的继续沉默,艾尔玛的言辞从挑衅与嘲讽渐变为不满、恐吓、乞求与威胁,而艾尔玛的愤怒也逐渐变成对沉默进行揭发和颠覆的执拗与某种狂暴的歇斯底里。
当文本的叙述行至此时,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倾诉所形成的言语与沉默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表象,它们原本就一直处于同一个战壕,它们之间原本就具有一种天然的、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联系。但是,言语与沉默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如此。
实际上,伊丽莎白的沉默的本质也已相应地被言语所出卖,在文字的言语而非口头的言语之中,她的沉默被出卖、被证实为只是言语的一种变体。这使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出现了:沉默是不被信任的言语的虚伪性的一种表现。这个证明最终是由艾尔玛来完成的。
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中,艾尔玛将同一段话说了两遍,或者说,伯格曼将艾尔玛的同一段叙述拍摄了两遍。但是,这样说是不太准确的,因为这两遍叙述虽然听上去一字不差、完全相同,这两遍叙述所采用的叙述语气和镜头所指却具有明显的区别:在第一遍叙述中,镜头一直对着倾听者伊丽莎白,在第二遍叙述中,镜头则一直对着叙述者艾尔玛。在这前后两段相同的叙述中,叙述者与倾听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身份交错、意识互达的精彩的融合:
让我来说吧。那是一个晚会,是吧……有人对你说,“伊丽莎白,作为一个女人和艺术家你已拥有了一切,但是你缺乏的是母亲的身份”。你笑起来因为你觉得这话很荒唐,但是你禁不住去回想这些话。你变得焦虑因此你让你丈夫使你怀了孕。
……当你知道一切都已成为定局时你却感到害怕,害怕责任,害怕被束缚,害怕必须离开剧院,你怕疼,怕死,怕自己变得臃肿……你几次试图流产但都失败了。当你知道这一切都不可避免时你开始恨这个孩子并且希望他是个死胎……分娩的过程漫长而痛苦……孩子被人用钳子夹出来,看着这个哭闹不止的孩子你感到恶心……孩子日夜啼哭不止,你痛恨这一切……你感到自己有罪……
这个孩子就像一个无底洞般无止境地向他的母亲索求着爱。你绝望地抗拒因为你认为自己对此无以回报……你冷漠、无情,而他看着你,他爱你,他是这么柔软而你却想揍他因为他不让你自己一个人呆着。你认为他是令人厌恶的,包括他那厚厚的嘴唇、丑陋的身体和他那总是因为祈求而显得潮湿的眼睛……你害怕这一切。
这是艾尔玛对伊丽莎白作为母亲的揭示。这一揭示的核心并不是个体作为母亲的惧与私,却关涉伯格曼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伦理性主题——“无能的爱”的主题的核心。
在艾尔玛的第一遍叙述中,伊丽莎白注视着艾尔玛,她先是摇头否认,继而痛苦地将头扭开似乎要逃避这种声音与言词的指控,她疑惑地注视着,惊惧、痛苦、自责与悔恨交替出现。与此同时,摄影机的镜头毫不留情地步步进逼,直至她被迫注视着镜头,直至她那极度痛苦的面庞充斥了整个屏幕。
在第二遍叙述中,摄影机的镜头也以同样的节奏行进着:艾尔玛注视着伊丽莎白,显得沉着、冷酷,充满嘲讽,但是当镜头以充满了压迫的节奏(与第一遍叙述相同的节奏)步步逼近时,她也被迫直视着镜头,而她的语气却逐渐变得空茫,指控变成了述说,就仿佛她在述说着自己——在她的空茫的述说声中,她们两人的左右半脸在屏幕上合为了一张扭曲、古怪、令人惊骇的面庞。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摄影机镜头的运动及其视角转换,这个叙述场景是以其充满压迫性力量的节奏达成了镜头上的重合感:
镜头1:人物艾尔玛(A)与伊丽莎白(B)同时出现在镜头的前后景之中(A的背面前景与B的正面后景)并互相直视(被摄影机镜头C注视着的A与B之间的交流);
镜头2:A的背面在镜头内消失但其叙述的声音并未消失,其声音代表了A的在场,此时的B注视着镜头外的A,在这个镜头的末尾,B垂下了眼睛(A缺席,C仍是客观镜头);
镜头3:在A的声音中镜头向前推进,B抬起眼睛,正面直视着镜头(A与C与观众视角的重合,主观镜头形成)。镜头再次向前推进,直至B的面庞充斥了整个屏幕。在推进中,镜头不再外在于B,它具有一种似乎要“穿越”或者“进入”面庞的尖锐的镜头感——在镜头不断向前推进的节奏中,这种“穿越”和“进入”使人物A、B和镜头C三者之间隐隐地完成了一次重合。
接着,伯格曼将人物A与B的位置调换,并在细节上做了一些不同的安排,将此场景“重复”拍摄了一遍。在这个“重复”中,不仅镜头、观众与人物的重合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调,而且人物内部的意识重合也得到了最强有力的突出。
这种重合一方面是由摄影机镜头的运动所提供——从客观镜头到主观镜头直至穿越镜头,视角的逐步变换提示出镜头、观众与人物“重合”的节奏与可能。但是另一方面,镜头的运动只是提供了外在的节奏以及镜头上的重合感的可能,这种重合——艾尔玛与伊丽莎白最终的意识重合,或者戏谑地说“意识通灵”——最终却是在艾尔玛的声音里也即在艾尔玛重复叙述的言词里形成。不是通过镜头而是通过艾尔玛那重复的言词,那已然在镜头内消失的和那尚未消失的才仍旧结合在一起。“重复”促成了“重合”,但是在这里,重合并不是融合无间,而是一种“进入”:艾尔玛的言词进入了伊丽莎白的沉默,或者说,伊丽莎白的沉默被艾尔玛的言词所进入。
然而,言说的艾尔玛则必须为此付出自我消失的代价,所以她惊惧地叫了起来:“不,我不能感受你的感觉,我是艾尔玛,我不是伊丽莎白·佛格勒,你是伊丽莎白·佛格勒!”——“进入”成为言词在沉默内的消融。作为言语者,艾尔玛的言语被迫消融在伊丽莎白的沉默之中,与此同时,作为言语主体的艾尔玛也被迫消融在了作为沉默主体的伊丽莎白之中。艾尔玛的惊惧正在于对自我主体的消失的惊惧。
言词被消融,沉默被进入。艾尔玛终于以言词完成了对沉默的本源及其虚伪性的指证并将之彻底颠覆,她完成了对上面那个命题的证明:沉默原本就重合着言语,沉默原来只是并且仅仅是虚伪的缄口不言。沉默终究还是一种角色,不管它是言语的角色还是身份的角色。沉默被言说拉下了马。虽然艾尔玛对此必须付出主体消失的代价,言说和沉默却因此结为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同谋。
在言语与沉默这种紧张的同谋而非亲密的同盟里,两个女人之间逐渐发展成为受虐和施虐的关系:厮打,流血,艾尔玛发疯一般地捶击桌面,敲打自己的脑袋,抓破自己的皮肤,撕扯伊丽莎白的头发,伊丽莎白则俯身吸吮艾尔玛的鲜血。这是逐步沦陷于虚无之中的两个同谋之间的趋于疯狂:沉默者的力量已然消散,言说者的自我陷入迷茫,言说和沉默都溶解在空虚之中。在艾尔玛不知所云、仅仅是语音堆砌的“言说”中,伊丽莎白对着镜头,面无表情地蠕动着嘴唇,跟随着艾尔玛的语音开始了自己无声的、沉默的“言说”。
在伯格曼的构想里,“艾尔玛在这个梦幻情境里插足之深使她不再能使用语言。她……丧失了表达自己的能力。她像一架已经解体却仍在疯转的机器,她的没有任何顺序关联的语言只是随口倾泻而出”。在这里,对发生在现代哲学里的那所谓的“语言学的转向”,艾尔玛的言语自我的丧失恰好成为了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注解:在语言的表述与意义的生成具有密切关联的同时,它也同无意义勾结得过于密切并终令言语主体丧失于“无”。
影片最后回到了医院的场景。随着艾尔玛劝诱的声音——“说,跟我说,无”,佛格勒太太重复着那个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字:
Ingenting-Nothing-无。
在这个主体力量的转换中,是“无”最终包容了沉默的痛楚,也包容了言语的痛楚。
是“无”最终包容了人的孤单存在的所有难言的痛楚。
2.电影的言说
在《假面》中,在言语与沉默进行力量交换的过程中,真实与幻觉的难以辨别成为了一个极其醒目也难以被观众忽略的镜像事实。正如同思维的异常性跳跃,那些有意不连续的、突然停顿或突然运动的、性质常常显得似乎单一的时间和场景使观众难以对之进行基于观影经验之上的区分。这也提醒了我们,对于电影这个就其物理本质而言本是虚构的事物,所谓真实与幻觉的区别本就如同语言一般存在着虚构与被虚构的多重关系。因此,试图对《假面》中场景的真实与幻觉硬性地加以明确区分无疑会成为徒劳。那些经验不多的观众,当他们执拗地要做一个求真的侦探时,他们很快就会在其中失去“真实”的线索并陷入茫然之中从而只能将此片视为一场含义难明的幻觉游戏;而那些稍有经验的观众,即便因为他们对“伯格曼”这个名字的肃然起敬使他们不致轻易失去对影片的敬重但也仅能将自己限定在矜持的敬重之内。
有一点相当容易就可以做出判断,那就是影片的基调是客观而凝重的,这自然也是伯格曼的一贯基调。然而在这凝重的基调之上,影片中却有相当多的场景似乎是不真实的,但是,似乎也不是虚幻的。
比如,在亲密同盟已经形成之后,我们看到艾尔玛躺在北欧白夜的黯淡光线里,伊丽莎白走进她的房间,艾尔玛梦游一般地起身站立,两个女人头颈相偎,朝着镜头露出神秘的微笑。然而第二天,当艾尔玛问伊丽莎白是否晚上来过自己房间时,却遭到了伊丽莎白大惑不解的否定。影片中有诸多令人迷惑的此类场景,对之似乎都难以进行“真实”或“虚幻”的区分,再者如伊丽莎白丈夫的来访:他在门外叫着伊丽莎白的名字,艾尔玛走到他身边;尽管艾尔玛对他说“我不是你妻子”,出于一种未加解释的理由,他却固执地将眼前的艾尔玛当作伊丽莎白并开始倾诉与亲吻(显然,对他的视觉和听觉的考虑是在问题之外的);伊丽莎白来到这两人身边,注视着他们,艾尔玛一边报复性地看着她,一边假装自己便是她;在接下来的镜头的后景里,艾尔玛与那位丈夫亲昵地躺在了床上,继而她开始忏悔地、歇斯底里地哭泣,此时镜头的前景则是伊丽莎白那面对观众的痛苦而麻木的面庞。
就观众对电影的观赏心理或就电影表现手法的“惯例”而言,对真实与幻觉(如晕眩或梦境)的区分,影片常常需要对此给出可以辨认的恰当提醒,比如镜头运动方式的突然改变、灯光或色彩效果的变化甚或布景的一点改动等等。但这部影片却仿佛并没有提供什么明确的线索或暗示来说明这是真实还是幻觉。
一个看似稳妥的办法是将所有这些场景都看作是情境性的超现实。对那些运用于电影当中的超现实手法我们早已不再陌生,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甚至已可被视为陈规旧习。然而即便如此,疑点也不能去除:当我们认为这些场景是超现实的时候,这些超现实也得建立在某种来源之上,这个来源是幻想,是臆造,还是胡言乱语?是谁的幻想,谁的臆造?艾尔玛的?伊丽莎白的?导演伯格曼的?——于是我们又会再次落入漫无目的的处境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暂时将这个问题放在一旁而从影片的开头重新仔细察看。
影片的序幕和结尾明显游离于两个女人的故事之外,在分镜头的检查之下,它们呈现为这样的序列:
电影开始于一片黑暗。一个具有质感的光点渐显,接着又一个光点,它们逐渐获得亮度直到可以被辨认出是两个灯头;两个灯头碰触,发出火花;电影放映机的转盘开始转动,速度加快;电影胶片从片盒中被抽进放映机;放映机的弧光灯开始照射;胶片上的划痕、片号以及数字在闪烁;在黑屏与画面的快速切换中,一根勃起的阳物;纸张快速掀动;银幕逼近,被掀动的纸上的图形获得运动感;经过对速度的调整,动画人物的运动具有了逼真感;孩子游戏的双手。
接着是白屏。白屏与画面开始切换,其切换速度逐渐放慢——一组仿默片的死神闹剧;一只巨大的蠕动的蜘蛛;一只在人手中挣扎的被宰羔羊;死去的羊仍旧睁着的眼睛,一只手戳入羊眼;羊被肢解,人手握着羊的内脏;巨大的钉子被钉进一只向上摊开的手掌,鲜血从掌心中涌出。
一些静态的风景。树林、雪地、栅栏、雪堆;一张衰老的脸;衰老的静止的身体;一个在被单下躺着的或许已经死去了的孩子;静态的手的剪影和一些静态的人。
铃声突然响起。静态的人睁开眼睛;孩子也不满地醒来,他坐起身,取出眼镜戴上,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孩子仿佛听到一些奇特的声响;他伸手向前触摸;一张巨大的女人的脸,模糊的,变幻的。
序幕结束,片名出现,然后便是白屏中片头字幕与画面的快速切换。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以上这些画面在影片的实际放映中大都以极快的速度一掠而过几乎来不及辨认,这似乎是在说,这些画面即便具有某种意义也是可以忽略的。但是在我们的检查中,它们逐次显现出了不能被忽略的明确含义。
序幕的开始显然是在模拟和解释电影的运作过程:放映机内弧光灯的碳柱头的运动,胶片进入放映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性欲”——这带着明显的弗洛伊德的痕迹),电影形成运动感的视觉原理,并以“电影是孩子的游戏”的隐喻作为结束。
在接着的白屏与画面的切换中,我们可以将白屏视为一个屏幕,从那些嵌在白屏中的画面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这是电影的一系列主题:死亡(躲在柜子里的死神,从伯格曼早期电影中剪辑而来),上帝与信仰(在伯格曼的影片中上帝常被描述为一只可怕的蜘蛛),献祭(被宰的羔羊),虚伪的献祭与渎神(手戳进羊眼,对羊的肢解),基督受难(钉子钉入掌中),风景,人物等等。
铃声就像一道召唤。这召唤使原本处于静止或死亡状态的人开始动作,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化也许意味着电影的某种召唤和电影叙述的进入,或生命与死亡的界限,而孩子与老人同时又代表着生命的开始与结束。孩子阅读着悖谬的人性与人生之书(莱蒙托夫的《时代英雄》),他开始触摸,隔着某种透明物质——这个物质虽然透明但却成为了阻隔双方的中介——他抚摸着一个平面而巨大的女人的脸。在影片的开始,我们当然无法得知这张介于模糊和清晰之间的脸庞究竟属于谁,但当我们进入片中之后便会反过来得知它正缓慢地交替显现为伊丽莎白和艾尔玛的脸。
片头字幕结束,护士艾尔玛推开门进入镜头,这是一家医院。医院的具体情境使刚才那些静态的风景被暗示为医院附近的风景——镜头一步步地从较远的树林到较近的医院栅栏再及院内的雪堆,那些静态的人物也随即被暗示为医院里的病人或躺在太平间里的尸体。因为某个具体情境的进入,刚才那似乎分散的一系列画面便都成为构成一个具体的电影叙述文本的相关元素。
在一种必须被解读的序列中,这些表面上似乎不成系统的画面逐次形成了一条明确的线索:电影放映机如何运作——电影的原动力——电影的视觉原理——电影主题如何形成并得以呈现(这些主题显然带着伯格曼强烈的个人印记)——电影如何充当了“看”与“被看”之间的叙述媒介并如何从单镜头的静止画面进入复杂的文本叙述。这条线索的完成依赖于对这些画面所呈现的大量的隐喻和象征的解读,而这些强烈的隐喻和象征,由于它们的互文性以及多重结构又常使其含义显得过于分散。例如,已有论者就序幕中那个孩子的身份进行长篇推论,在这些推论中他既是伊丽莎白的未出现的儿子也是艾尔玛流产掉的孩子甚或是伯格曼的童年的化身,而孩子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则被认为象征着基督的复活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隐喻和象征常常会令其解读者轻松而愉悦地掉入索隐的汪洋大海之中。
无论如何,伯格曼还是将这条明显的线索置于画面的快速切换之中,从而使其不致过于引人注目,但也不会不引人注目。
在影片之中,伯格曼还数次插入了对电影放映机制的模拟。例如,在偷阅了那封信之后,艾尔玛愤怒地凝视着窗外被玻璃划破了脚的伊丽莎白,此时电影画面突然从中破裂并被无名之火所烧毁,影片再次进入白屏与画面的切换,默片闹剧以及钉子钉在掌心的镜头再次出现,然后是一只巨大的眼睛(摄影机的镜头/看与被看的关系)。
影片的尾声是一种呼应:孩子仍旧在“触摸”女人的面庞,电影放映机再次出现,速度变慢,停止了转动;弧光灯的两个碳柱头恢复成两个亮点,画面渐隐,屏幕恢复黑暗。
从黑暗到黑暗,在片头的渐显与片尾的渐隐之间,在弧光灯所映射的屏幕上的视觉幻象中,电影完成了自己的叙述。
显然,通过对电影的放映机制及其历史和主题内容的模拟与再现,《假面》成为了一部关于电影的“元电影”,它获得了一个由电影自身的各种元素所构成的叙述框架。因此,关于电影的叙述成为了《假面》的第一叙事,在这第一叙事里,导演伯格曼是隐形的叙述者,他讲述着一个关于电影的故事,而发生在那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便成为了嵌于其中的第二叙事——一个故事中的故事。就其性质而言,这第二叙事更像是第一叙事为了论证自身而举出并完成的一个具体范例,所以第二叙事融合了许多由第一叙事所赋予的特性,如上文提及的由破裂和被烧毁的画面所象征的力量转折点的形成,以及那由两个半张脸拼构而成的一张脸,这张脸象征着一种扭曲的“结合”(言说与沉默的同谋性“合一”)。这些令人难忘的画面在第一叙事中都具有实际的叙述功能,都成为了具体的叙述手段,成为了分割第二叙事、呼应与构成第一叙事的叙述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在第二叙事中被巧妙采用的手法。
这个第一叙事便成为了伯格曼对电影和电影叙述的反思——对电影作为一种语言,作为一种介于物质与非物质之间、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镜像语言的反思。“电影”这个概念本身成为了思考的对象,电影不仅是一种具有言语性的言说而且还是极为个人化的言说。《假面》的第二叙事所呈现的言语与沉默的对抗及其力量转换因此可被视为关于电影的言说的一个具体个案,作为第一叙事的叙述者的伯格曼正是在这第二叙事的“言语与沉默”之上、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了自己的个体性言说。
现在,让我们回到上面那个关于真实或虚幻的问题。虽然那些令人疑惑的场景呈现于第二叙事中并在这一叙事层次内形成了独特的表达,但它们同时也属于第一叙事层面,是这一叙事内具有功能性的环节与符号,它们体现和证明着在第一叙事层面上所揭示的电影的语言性,它们因此也被赋予了语言的种种特性。这些特性正如语言自身一样,虽然意义在其中被建构起来,语言符号自身却介于确定和不确定之间。因而,这些场景在两个叙述层面内的不同功能正略同于能指与所指的不同功能。
对于由这些场景所体现的电影语言性的虚构性特征,影片有一个重要提示,即片尾时的医院场景:仅在第二叙事内看,这一场景突兀而毫无来由,显得仿佛前后脱节,但在第一叙事的层面上,它却与片头的医院场景构成了叙述文本上的呼应,这一呼应则体现出伯格曼对“电影文本是如何叙述的”这一电影叙述功能的反思。在这一叙述反思中,由文本呼应所体现出的叙述上的客观性却意味着这两个女人也许从未离开过这个医院,也许伊丽莎白从未离开过这个病房,也许连同在海滨和海滨上的小别墅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一个虚幻——个人的虚幻、叙述的虚幻或电影语言的虚幻——因而这整个第二叙事便可被视为由叙述文本建构起来的一场彻头彻尾的虚幻。
而在这虚幻之中,唯一显得“真实”的便是伊丽莎白在医院中所吐露的那个音节——“无”。“无”成为了这一切真实与虚幻的唯一内核,“无”在“无”之内成为了唯一的真实。
然而,在此“无”之中却仍包含着对语言之“有”的展示:虚幻建构于语言之内,真实也同样建构于语言之内;叙述和意义在语言中被召唤,在无中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产生的不仅是电影的叙述文本和电影的言说,而且也促使着意义在其自身的展开中形成并获得表白,即便这个意义是关于“无”的意义。但反过来,“有”却终将消泯于“无”。
伯格曼对电影的反思、对电影叙述的反思同时也成为了对意义生成机制的反思。在整个20世纪对语言和意义生成之间的关联的共同探讨中,这种反思最终将他对语言的感性的不信任纳入了对人自身本质的怀疑当中。
在《假面》提供的所有这些力量的运动、解释的框架和意义的表白的表层之下,一个同样在交错运动着的内层便是现代人对“无”的离弃和对“本源”之“有”的无穷尽的追索——我们总是在自己知性的框架内徒劳地在语言的幻觉中打捞着真实,我们总是在对事物本源的渴慕中徒然耗尽了自己。这正如艾尔玛在痛苦的倾诉中对伊丽莎白的追问:
“一个人能否做到表里如一?我的意思是,一个人能否成为表里相同的两个人?”
这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分裂或人格交换。如同语言一样,在“无”之中,生存的真实与虚幻本就是一回事,就是成为了表里相同的两个人的那同一个人。艾尔玛对人的生存意义之“有”的渴慕,或许,也终将归于无。
3.自我的勇气
伊丽莎白的沉默并不是表面的言语行为的静默,而是一种——如那位医生所揭示的——一种道德上的沉默,同时也是伯格曼所构想的,一种“对真理的渴望”,虽然这渴望以沉默作为呈示的手段。
“生存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望的梦……每一个音调都是一个谎言,每一个手势都是一次伪装,每一个微笑都是一次掩饰”,仿佛是为了避免欺骗和撒谎,为了避免掩饰和伪装,仿佛是为了寻求一种真实的存在并证明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伊丽莎白才选择了保持沉默。
然而,艾尔玛对伊丽莎白叫喊着道:
事情非得像是这样不可吗?不撒谎、说真话、用诚恳的语调跟人说话真的就那么重要吗?不能自由地说话你如何能生存下去?(像你这样)找个借口躺下?给自己一个偷懒并且躺下的许可难道不是更好吗?也许当你顺从着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你就会好起来。
在言语的沉默和道德的沉默之间,伊丽莎白实际上被迫跌落到了人的生存根基中最盘根错节之处,而这是一个超乎她的解决能力的矛盾之处:如果“真”就是真理和道德,就是不撒谎、不欺骗、不伪装和不掩饰,那么当她言语时,她难以避免言语的“不真”,但是,当她沉默时,她却同样难以避免自己的“不真”。
所以艾尔玛仅仅尖锐地质问着:“不能自由地说话你如何能生存下去?”在艾尔玛那里,所谓的“真”与“自由”具有密切的关联。“自由地说话”是人的语言存在,它存在性地包括着“真”与“不真”;所谓的“自由”便是同时拥有着“真”与“不真”的那种自由,因此当你单方面地认同“真”并否决“不真”时,你的“真”也就成了“不真”,你也就会随之失去了存在的自由。所以艾尔玛会这样认为:“也许当你顺从着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你就会好起来”——你的自由愿望便是一种“真”,便是一种对“真”的选择,便是一种不撒谎、不欺骗、不伪装和不掩饰,即便它有时并不那么“真”。
正如同大部分人一样(或者如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当中看到的那样),艾尔玛承认的是那仿佛能够无拘无束似的人的个体性,以及建立在这种个体性、个体主义之上的“自由”和“自由选择”。在这其中,“自由”以及“选择”仿佛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最强烈、最有可能的借口,仿佛真的能够掩盖并令人忘却“真”的存在性悖论——作为个体存在的孤单的人,艾尔玛以此作为借口,以“自己的愿望”以及“自由”作为借口,对“真”的存在性悖论进行了合理的否定、忽略与遗忘。
但是,伊丽莎白却凭借着一股顽强而天真的意志力与这个关于“真”的悖论进行了抗争。她的天真在于,尽管她对“不真”的否决表示了一种可敬佩的勇气,但她却没能看到这个悖论的虚构实质:人的沉默本无力成为“真”的同盟,同时也无力成为足以与人的言语性相对抗的那一方。
言语的对立面并非沉默。言语与沉默,仅仅是人的存在本质的语言性分裂。
所以,伊丽莎白从自己纯洁的沉默中所获得的只能是虚假的意志力量和自由的丧失,她以沉默所表示的对言说的抵抗只会成为一种虚妄的对抗——因此,在与艾尔玛的言说的对抗中她的沉默必将败下阵来,必将被揭露,并且被颠覆。
“我们不能知道语言本质。”我们已经普遍地失去了通往无限的路途。如今,人只能比以往更深地认识到,自己正是在自身所无法逾越的有限性中存在,语言因此成为了包容着人的有限性的那个最空泛的无限。人是语言的人,是言语的人,无论言语还是沉默都指示出了人的弱体地位,即便人通过虚拟的意志力或道德力来决定保持沉默,人也并不能从沉默的行为中超逾自身,获得自身所不具备的力量。因此,这沉默恰成为了人的一种不自由,成为了人的一种角色,成为了言语的“面具”,成为了persona。
无论言语还是沉默都成为了人的有限存在的分裂的面具,在面具背后掩饰着的正是人的有限性与弱体生存。语言成为了人的有限存在的证明。
伊丽莎白的沉默正代表了人类语言的失效和语言对人的有限存在的掩饰。但是,可宝贵的,却是她那沉默的姿态:她正是从自身的有限存在中学会了“保持沉默”,在这沉默的姿态里包含着的是她对人的语言性存在、悖论性存在的否认,包含着她对存在的有限性的贸然而天真的离弃。“必须保持沉默”正是这样的否认和离弃,虽然这必将是一种虚假而无效的否认与离弃,但是,在这否认与离弃中却饱蕴着一种茫然而纯洁的勇气。这不也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勇气?
然而,通过沉默,通过对沉默当中的不自由的接受,伊丽莎白却同时获得了另一种关乎自我的自由:沉默成为了对不自由的自我的固守,成为了一种受限的自由渴望;这自由渴望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与之相对的言说则被迫消融,被迫面临着丧失自我的危险,被迫成为了一种没有自我的“自由”。
这是在人的“自我”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当中存在着的一种矛盾形式,这矛盾的形式在人的言语与沉默的双重行为中明明白白地显露了出来。求真的伊丽莎白的勇气就在于选择了面对这存在的矛盾,所以她选择的不是去死,不是去自杀,不是去亲手摧毁这有限的身体与有限的存在并从这最大的摧毁中获取尘与土都被狂暴吹散之后那最微小的一点点“真”。她选择的也不是佯狂,而仅仅是沉默。沉默的意义在于希望,即便在最矛盾之处希望也仍然是存在的,虽然我们可能看不见它。是这贸然的纯洁的勇气而非那虚假的自由,始终抚慰着人类那孤苦无依的心灵。
而这也正是伯格曼那作为个体以及作为自我而存在的勇气。通过对言语和沉默的双重否认,伯格曼完成的是一种蔑视语言的言语行为,他承认了自己的有限、正视着自己的有限,同时他又表达了对此的否定与抗争。他所采取的,是用媒介语言去否定与对抗人的生存语言,这种对抗,正如同伊丽莎白的沉默一般,注定会成为一种虚妄的无效的对抗,但同时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