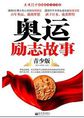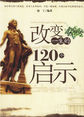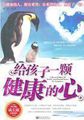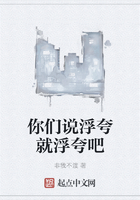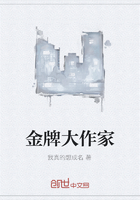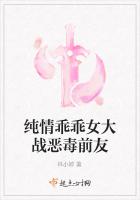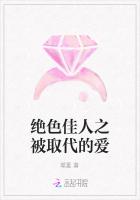手里拿着自己刚出版的诗文集《野菊花的秋天》,淡雅的书香里恍然觉得:这书不也是我的一间小房子吗?有最独特、最个性、最自我的设计和建造,我愿让自己的灵魂永远在里面逡巡徜徉。
小时候,走在野外,经常会看到田野间有小小的房子,那是阅读童话的年纪,我就扯住大人的衣襟问:“那是谁的家啊?拇指姑娘住在里面吗?七个小矮人住在里面吗?怎么没有门呢?”而大人们总是诡秘地笑,并不直接回答。
我也就好多年没有弄明白。直到长大成人,才懂得那小房子不是人住的,也不是童话里主人公住的。
在我们当地的风俗中,人死后,入材掩殓(放进棺材,然后对棺材进行密封),然后下葬。
然而下葬是要择日子的。人们认为这既是对死者负责,又是对活下来的亲属负责。
如果在风俗里碰巧是一些不宜下葬的日子,家人就会在庄稼地里找块地方安放棺木。四周用麻秆建成篱笆房子,大小形状都如棺材一般,叫丘棺。
原来,那小房子住的是风俗,装的是民情,是老百姓对生死两界的敬畏,对亲人和自己未来平安幸福的祈愿。
在乡下还能看到另一种小房子。位置一般在小路边田野不深处,房子比丘棺还要小,门向正南,里面陈放着观音菩萨塑像,虽然小到不起眼,但也总是香火不断。
这是乡下百姓自家修建的微型庙宇。乡下人信神,过年过节都要烧香,家里有个什么事情也要拜佛问神的。但附近没有庙宇,为了方便,就自家建设小庙一个,恭恭敬敬请进菩萨像。
简陋是简陋点,但烧香敬神的诚意与祈神保佑的迫切一点不比恢宏大殿里的虔诚逊色。
原来,小房子里供奉的是老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片心!
在田野里还能看到一种小房子,或是一种极其简陋的小棚,小到只能容纳一个人弯腰进出。这里面住的是看瓜看菜的农民。小房子卧在大片大片的瓜地菜地旁边,看起来甚美,尤其是在月光下,远远看去就像是童话世界。
心里也多次生出进去看看的欲望。当我真的进去了一次,知道了里面的黑暗、狭小与肮脏时,才明白美丽只是假象,是我们这些不事稼穑的人心里乌托邦的幻想,那些土里刨食的农民,种瓜种菜辛苦,看护也不容易,生活很现实根本没有童话。
原来,小房子陈述的是岁月的艰辛,是农民们对丰收的渴望。
也许人世间有很多我们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小房子:书包是孩子探寻智慧的小房子,日记本是心灵世界的小房子,手机是联通四海的小房子,电脑是装着大千世界、宇宙人生的小房子,人脑是人体信息控制中心的小房子。
也许这些房子建材不同,形状各异,但每个小房子里一定会有一个该有的灵魂。
今天停电,我靠在床头,心思遐飞,就想到了这些小房子。手里拿着自己刚出版的诗文集《野菊花的秋天》,淡雅的书香里恍然觉得:这书不也是我的一间小房子吗?里面有我的辛勤,我的汗水,我的思想;有我的智慧,我的思考,我的渴望;有我爱的执着,也有梦的迷茫;有我工作的劳碌,也有劳碌间隙里休闲世界的光芒;有现实的困顿,更有思接千载,遐想神游的万千风光。
这小房子蕴含的是一个缤纷的世界,是我多彩的心灵。拥有一间这样的、完全属于个人意识形态的小房子,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或者将来会拥有更多间这样的小房子,更是令人神往的境界!因为小房里的一切,都是个人精、气、神的凝聚,都是最独特、最个性、最自我的设计和建造,即使它或许只是一摞寂寞的纸堆,我也愿意让自己的灵魂永远在里面逡巡徜徉。
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王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