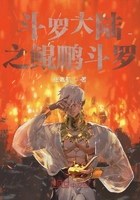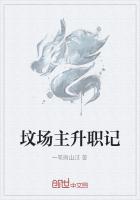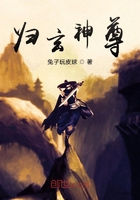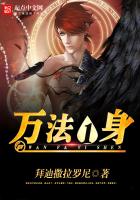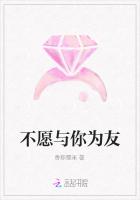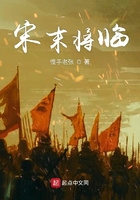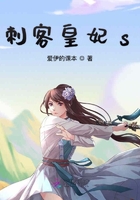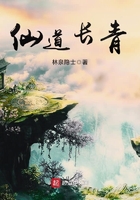说不清有多少编辑人员为我的作品付出过辛勤劳动,他们不仅编发过我的作品,而且给了我许多真诚的鼓励和帮助,使我们建立了真挚的情谊,这种情谊甚至远远超越了生活中常见的亲情或友情。
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成功》杂志即将创刊,两位年青的编辑人员热情地登门约稿,并出了几个题目供我选择。面对这个刊名,我犹豫起来,因为我算不上一个成功者,要写只能谈谈二十余年来我在对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中,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给予我的支持。特别是一些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是我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我从事创作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者。到目前为止,我共在各地数百家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一千五百余篇,上至《人民日报》《红旗》《诗刊》,下至一些地市报刊或专业报刊,几乎遍及全国三十个省市和自治区,先后出版了九本集子,说不清有多少编辑人员为我的作品付出过辛勤劳动。一批老少编辑不仅编发过我的作品,而且给了我许多真诚的鼓励和帮助,使我们建立了真挚的情谊,这种情谊甚至远远超越了生活中常见的亲情或友情。
我认识的第一个编辑
我参军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是与一位爱好文学的战友合写的。军区报社收到稿子后,立即挂长途电话到我们所在团的政治处,通知我们前往商改。我们那个团是刚组建的,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这消息引起了“轰动”,说团里出了“大秀才”,政治处和连里的首长高兴得比我们还急,催着我们尽快出发。来到军区,我见到了自己相识的第一个编辑,他叫严金海,长我们十多岁,负责军区报的副刊。即使是在当时看来,为一篇几千字的散文如此“兴师动众”,也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他说主要是看到我们的基础不错,想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以后好联系,争取“写出来”,改稿不是主要的。在我们住军区改稿的一周里,他不仅多次向我们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而且下班后还来和我们聊天,他讲的都是我们这种生活在山沟部队的文学爱好者从未听过的文学界的话题,使我们一下子懂得了许多,我好像从此知道了自己该怎样去争取当个作家。同时,他也使我想象中高大的编辑形象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一年以后,我随连队调防到另一个团,团部在大城市,团政治处仍把我抽调去专门搞写作。那年代时兴作者送稿,严编辑仍在办副刊,所以我有机会经常见到她。由于不好搭车等原因,有时赶到军区就该下班了,他总是把我的肩膀一拍,说声:“走,跟我到食堂吃饭去”,每次都是他自己掏饭票。部队都有午睡的习惯,那时他家属还未随军,住单身宿舍。有一次,记得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他有些疲劳,但又想留下我在下午商量稿子的事情,一定要我到他房间一起休息,就一张床,他执意让我上床睡,他自己却在藤椅上靠了一中午。那会儿年青,拗不过他,就上床睡着了,但这“细节”至今想起来仍使我感动。那时我还是一个“大头兵”呵。
几年以后,军区机关撤销,我们都转业了。严编辑在省委,我在市委,每次见到他,总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和我第一次同来军区改稿的那位战友,没有“写出来”,很早就复员回山西老家了,严编辑仍然与他保持了多年的联系,还经常向我问到他的情况,总为他感到惋惜。
一个大好人
初学创作的阶段,我爱的是诗,因而认识了省报副刊的诗歌编辑李光辉,说他是个大好人可能再恰当不过。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乡下当过编织竹器的篾匠,是靠写民歌,写戏曲走出来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一直保持着天生的厚道,在我的印象里,他对谁都很热情。我在他面前是小辈,可他连普通长者的架子都没有,我也很愿意与他打交道。每次去编辑部,他再忙也要陪我聊一会儿,隔些日子不去,他就会在电话里问:“小杨,你怎么不来呀?”
我们交往久了,他对我的关心就不仅限于创作上的进步,而且常问及我在部队的工作情况。当战士时,他关心的是我什么提干;提干以后,他又希望我能到连队去任职,说基层锻炼人,也有生活,对创作有好处。不久,我被提到了连职,他得知后很高兴,还戏言道:“正好编就了你的两首诗,我早点安排发出来,给你在创作上也鼓鼓劲”。这种鼓励用现在的眼光看,也不能认为是俗气,而是一个长者对年轻人的真诚希望。李光辉是个非常质朴的人,他曾多次对我谈到,他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自高自大的人,并告诫我,无论取得多大成绩,都要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对他的质朴,有的恃“才”傲物的年轻作者并不理解,当面央求他多发自己的作品,背地里却讥讽他“土气”。
在与李光辉老师的多年交往中,最令我难忘的还是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件事。那次我们在他办公室闲聊,说到我弟弟准备参加高考,他连忙问有没有复习材料。这材料是指有关单位专门为考生编印的一本内部参考读物,由于当时纸张紧张,印得少,很难弄到,此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专门材料,因此我断定在边远县城教书的弟弟是不可能有的。李老师听后马上起身说:“我两个孩子都准备参加,他们每人有一套,让他们合用一套,腾一套出来给你弟弟。走,跟我拿去”。那口气不容推辞。他家就在报社大楼后面的院内,当我们走进时,见他两个孩子各捧一本正背得聚精会神。离高考只有最后的关键一周时间了,他们对父亲的决定都面露难色,但还是服从了。我接过复习材料就匆匆赶往邮局,用挂号寄给了弟弟。几年后言语不多的弟弟才对我说起,他在考完后才收到,如果早一周时间收到,他考取的就不是一所普通的医学院了,因为考试的许多内容都在那本资料上。
李光辉退休几年后不幸去世,腾资料一事也过去了二十年,但我们至今想起来仍感激不已。仔细回忆起来,我与他的交往,除了编者与作者的忘年交关系,着实没有别的什么因素。那年月物资紧张,他只是托我在部队买过两斤白糖和几条肥皂,还坚持付了钱,也是唯一的一次。
又一个大好人
满锐,五十年代成名的满族诗人,退休前任北方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86年,正当我的系列诗话《诗廊漫步》散见于各地报刊之时,他一纸书信通过武汉大学的《写作》编辑部飞到了我手中,让我整理结集,从此我们开始了十余年的联系。平心而论,《诗廊漫步》受到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称誉,只是一方面;此书能够问世,并在两年后再版,多次追印,还被提名参加“金钥匙”评奖,如果没有他的积极促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反响的。他亲自担任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前后付出了不少心血。
我们之间的交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编者与作者的关系。自接到他的第一次来信,我就感觉出他是一个谦和诚厚的文学前辈,即使是《诗廊漫步》出版的愿望落空,我也会庆幸自己又结识了一个好人。后来我们关系的发展,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按他的话说,“我们彼此都没有看错”。
出书的事情已过去好多年了,我们的话题也早已从文学转移到其他方面了,诸如对人生的理解或彼此对对方生活的关心,等等。作为前辈,他给了我许多关怀,尤其是在他几年前退休后,他来信更多,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询问得更具体。我们的情谊日渐深厚,几乎无话不谈,彼此没有不可告诉对方的事情。他说,只要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武汉”二字,他就会想到我。有回他在电视中看到我家人的一个镜头,立即高兴地来信,对我们的生活给予美好的祝愿。那年,他在一次来信中索要我的家庭生活照片,我因为忙没有及时寄他,后来多次去信均不见复,他家的电话号码也变了,不知他出了什么情况,心中更加惦念起他来。春节前夕,我通过查号台问到出版社的电话,才知他和老伴去了美国,他儿子在那里工作。他们是临时动意去的,走得很匆忙。许久,我终于盼到了他的来信,开头便是“任蒙,我的好兄弟!”使我倍感亲切。起初,他执意不让我称他为老师,我只好采取让他“不知不觉”的办法,突破他的限制。论年龄,论学识,他都是我的长辈和老师,但年龄和辈序没有成为我们之间的感情障碍。
我敬重满锐,更重要的是由衷地钦敬他的为人。对我来说,从他思想品格上得到的启示,其意义远胜于他在创作上给我的支持。记得他在退休之际曾给我来信说,按照正常的人生年龄,他今后还有几十年的路程,此时他对自己的告诫是“不要学坏,千万别学坏!”我想,这句虽然质朴却很现实的话,何尝不是一个正直老人对我们晚生的崇高警策呢?
然而遗憾的是,我从未去过东北,他也一直没有机会来武汉,我们联系了十几年,竟一次面也没见过。如今他又去了美国,我们说好等他回国后我们争取找机会见面的,我期待着。
一群大好人
这样拟作小标题,也许有“文字游戏”之嫌,但都是实话。我们许多老百姓说,孔繁森是好人,吴天祥是好人,大家好像都不会讲究什么评价性的字眼。其实,“好人”就是一个最普通也最崇高的评价。所以,我把自己交道过的好老师和好朋友都称作好人。
八十年代,我偶然发现上海有家名为《杂家》的刊物,是几个出版社的同仁联办的,便试探性地寄去了一篇短文。编发此文的是该刊同仁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郝铭鉴,因此而与郝先生相识,后来他又编发过我的几篇文章。其中有篇随笔把乾隆的年龄记错了,直到快出刊时我才发现,急忙追信纠正。我怕这样也来不及,结果他们追到印刷厂改过来了,由此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上海出版界严谨的编辑作风。
那年,我到上海给郝先生挂了个电话,他听说我是第一次来沪,坚持要我第二天在宾馆等他。我考虑到他正忙于一项大的出版工程,加上当时他们社的一本书出了问题,他是主要“责任者”,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实在不忍麻烦他。可他一再说,你支持过我们的刊物,尽管刊物早停了,但不能忘记老朋友,一定要见一面。第二天中午他把我接到一家百年老店,并特意请了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先生前来作陪。这虽然是一次编者对作者礼仪上的接待,但上海文艺出版社那时已平均日出一书,并办有《故事会》《艺术世界》《文化与生活》等九种刊物,不知要接触到多少作者。我想,他们对我的热情还是有“老朋友”的因素。
第二次去上海时,我再也不敢打扰郝先生了。《解放日报》文艺部的老主任沈扬先生,多年来编发过我不少杂文,也只是在离沪之前给他挂了个电话。这次,我见了诗人张启国,他是我的同龄人,在《轻工机械报》任副刊部主任。1992年我们在黄山的一次研讨会上相识,以后我们经常通信,渐渐心心相印,他尽其所能对我的创作进行支持。他让我去他家作客,可我下午就要离开了,再说我们一行有七八个人,不能耽误大家,他只好赶到宾馆和我们共进午餐。临别时,我们依依不舍,交通车开出老远,我还看见他站在宾馆门前望着我。同事们还以为他是我的兄弟,我说是文友,这是第二次见面,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后来启国来信说,那次目送我远去时,不知怎么搞的,他竟“泪流满面”。
接着,我们到了苏州。《苏州日报》的总编辑助理简雄等了我一下午,无奈我们的日程太紧,实在无法离开。我断断续续地给他们投稿十几年,他还在国际级的报纸上发表过评介我的文章,可我还没见过这位仁兄的“尊容”。晚上我赶到他家都快十点了,许多话都来不及说了,好在见了一面。走时,他送我一件“小礼物”,在出租车上打开一看,才知是一架珍贵的“双面苏绣”。司机问多少钱买的,我说是朋友送的,他说这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一路上,我深感过意不去,我到他家可是空手而去的呀。
这次“东行”归来途中,有同事深有感触地说,还是你们文化人之间这种不带物质因素的感情真。不久,简雄先生在《姑苏晚报》上以“任蒙来苏州”为话题做了篇短文,说到我们这种编者与作者的友谊由来,要比我讲的准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