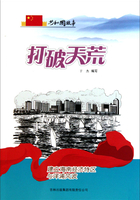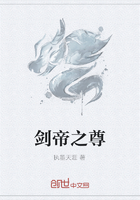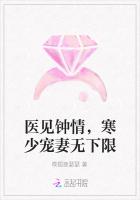1.有一句古话说:“三岁看大。”意思是说,一个人长大后会有什么造化,三岁时就可以看出来了。请问你对自己在三岁时的情形有些什么记忆或听闻?是否当年就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禀赋?
说到“三岁看大”,想到早前阅读过的一期《读书》杂志。杂志封二设置有关《世说新语》的诗话与漫画栏目,由陈四益和丁聪两位先生合作。记得那一期讲的便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由让人遗憾,若伤仲永。我以为人的造化最好不要一步到位,它也要符合事物的循序渐进。我相信温和的力量,如同植物承雨露阳光,而非急风骤雨。造化弄人,它可是一目了然,但不应是一目尽然,“三岁看大”未免武断。至于我的三岁时候的情形,自己无论如何也无零星记忆。但听长辈说,爱把小时的我的头发扎起来,两根小发辫,像小女娃。他们说,看上去,就是小女娃。现在我已经泯然常人,蓄须而非蓄发,看上去,该是怎样就是怎样。也会怅然若有所失,毕竟,能如女娃般灵气,也是幸事。至于禀赋,谁晓得。我能知道的是,自己就一凡人,有颗平常心。
2.你是如何写起诗来的呢?当时写完最后一行,你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写诗是自然的事。依稀记得小时候课堂上背诵诗文,也练对子,“天对地,海对空。”接着我就不知所以地写些合平仄的旧体诗。可能是对古诗相对熟悉,似乎出口就很合着这节奏。那还是在初中的暑假,我哥看到了,问:“这是你写的么?”我当时写下了莫名其妙的文字,便觉得愉悦,仿佛自己一不小心回到了前朝,仿佛自己是古人。我也确是个怀旧,甚至怀古的人。
3.你的父母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说说看。
我的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她是最爱我的人,而我对这爱的回应不及她的万分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我不会买菜不会煮饭,让人担心。在社会上,我几乎是弱者,不善人际交往,但凡一味信任。母亲是个朴素的家庭主妇,为人处世低调且正直,照料家人是她生活的重心。她对物质生活节制,对周遭事物珍惜,对应得权益保护,对他人别无所求。对我,母亲其实是有要求的,毕竟是她给了我生命。我的家乡常有台风,五岁的时候一个夏天,台风刚过,一片萧条,站在院中我突然害怕起死,向院落前面望过去,依稀有海岛,据说能看得见金门。而头顶天空显得那么辽阔。回屋时母亲还躺在床上午休,我害怕地伸出手指探触她的鼻息,真害怕她离开我。这把她弄醒,我问她人是不是都要死,她说好人长命百岁。当时我贪心地以为应该万寿无疆。如今,我知道人总有一死。我也知道,我的母亲并没骗我。她一直以为我是小孩,且要做个好人。
4.你第一次离开家乡时,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我的家乡在祖国东南隅的一个海边小村。我见闻的是台风天,渔市,村政府扩音喇叭里传来的提倡结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光荣。我生活的地方很小,也懒得走动,承受不住舟车劳顿。花大半天的时间在车里,简直不如我在床上看窗外老天的片刻安宁。我也曾赶上开往省城小巴士的车子到镇上读初中,更多时候,和伙伴追逐着拖拉机,攀爬上去,不去回应拖拉机主人的咒骂。但这不算是离开家乡。真正的离开家乡是赴沪读书的时候。火车我在自己的城市里见识过,坐上火车倒是没多大好奇。窗外的风景开始很新鲜,看久了也觉得疲惫。接着是漫长的暗夜。像是进了一条无止境的隧道。我感到新鲜的交通工具,该是地铁。脑海里冒出庞德的影子,人群中闪现的花瓣。但是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嘈杂的机械声。现在我居住在城市的一处,心里一直满足于骑着单车在坊间逛酒肆店铺,看其间人们的喜怒笑骂,呼吸健康的空气,如果彼时阳光正明媚,更好。我想把看到的所有印成内心的明信片。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记得明信片这过时的物什了。
5.你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在女性中间,你的表现如何?
单纯的女性。表现尚可。
6.你的诗弥漫着一股在现代诗中较为罕见的古典气息,请问对古典文学的纵向继承和对西洋文学的横向移植,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说过,相信事物温和的力量。同样,我也接受自己潜移默化的变化。如果我的诗确是弥漫一股在现代诗中较为罕见的古典气息,那也该是拜长时的盎然兴趣所赐:小时候过于喜欢类似对子这类的训练,也热衷吟诵古诗。毋论古典文学的纵向继承抑或是西洋文学的横向移植,首先都要找准自身的气息。像星空,有它的坐标,家族有它的谱系。我一直以为,诗人自有他传承的精神轴线,我为能发现与己亲近的诗歌兴奋不已。我还以为能就此做些什么,譬如写几则有关的随笔,翻译几篇打动自己的诗歌。说到传承,道法自然,不宜勉强为之。植物亦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淮南橘而淮北枳。法学里,朱苏力提倡法的本土移植。贺卫方说在一个法治还不是很健全的社会,运送正义的方式是很值得思考的。要送法下乡,也要根据本土资源,秋菊打赢了官司,但乡长被带走,并不是她的本意。
7.你有阅读哲学书籍的习惯吗?你激赏的哲学家有谁?他们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
有,庄子,在认识事物的角度,以及心灵的自由度方面影响了我。还有,海德格尔,沉醉于物的自在的气质。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就有提及,他沉醉于一块石头自在的气质——“阴沉”:“我们感到石头的沉重,但我们无法穿透它。”我想起那些乡镇的木匠,他们刨木,把粗糙的修整平滑;用抖动墨线取代直尺;眯上一只眼睛打量眼前的物体。以及镇上那些铁匠的锻造术,水浇在生红的赤铁上面,“哧哧”直响,还冒着青烟。他们正是在物用过程中把握物,分享物的气质;贴近物,最后呈现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本身的阴沉。
8.有人将作家定义为“写作有障碍的人”,你认同这种定义吗?为什么?
不是很明确这定义,作家是写作有障碍的人,从何谈起呢?写作过程中若有障碍,就不适合写作。作家写作,应该很愉悦,写的过程就像是谈对象,两情相悦,自然而然。
9.你读到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叫什么名字?它给了你哪些启发和激励?
我们不谈真正意义上的书。书就是书,看了就看了。它们如果有意义,那就是让人若有所获。我想谈的是那些一直放在身边的书。比如《顾城的诗》。高一时,同学的姐姐有本《顾城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元人民币。那时我拿来看了,想这孩子怎么这么胡说八道:“阳光成了羽毛;太阳烤着地球,就像烤面包;星月的来由;黄昏的儿子爱上了东方黎明的女儿,中间隔着黑夜巨大的尸床;特别是委屈的种子早发了芽,感受了冬天里的第一场雪,孤单倒下,周围成群成群的花草赶着参加开国大典。”于是我四处求购,甚至还动了偷这本书的凡心,幸好在福州新华图书城淘到了最后两本中的一本,并把它随身携带直到现在。我沉迷于顾城白描的神奇效果,仿佛可以化简单为纯粹。或许简单与纯粹并不适合进行比较?可我以为,纯粹是一种简单并超越简单而存在的。达到纯粹,这要求一个热爱万物的人,他能保持一颗敏感的心,身在其中又在其外,从而在繁杂的物象中把握物的本体。这种不施加色彩与渲染的白描,我还在叶辉的文字里体验到。如果追溯起来的话,陶潜可能是我最早倾心的对象,悠然得意,得意忘言。
10.说一说你对天才的理解。
我对天才没有多少理解,欠思考。
11.如果我现在给你一台地球仪,让你任意选择地方居住,你可能选择什么地方?为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暮气沉沉的年轻人。给我选择的机会,我也只会回答随便,略确切地说,随遇而安。相信自己能很好地适应周围生活环境,无论有多么大的变化也能入乡随俗。不久前我在西湖的一条小舟上,和亲近的人说,我喜欢随波逐流。尽管当时我们已经因不停脚踏踩板只为让小舟前行几许而气喘吁吁。我想起魏晋的阮籍,他习惯让他的小马车驾着,他喝着酒,随意走向任何方向,直到无路可进,才在一个方向的尽头痛哭流涕。这种盲目的率性前行,真叫人喜欢。我还喜欢一句诗:“每当我看见根府川与真鹤之间大海那美丽的颜色总为人生感到欣喜。”可能,我会偏爱靠海的地方?事实上,我就从小就生活在海边,打开窗子就能看见湛蓝大海。
12.你说你天生就是一个恋物癖者,请问你所恋之物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它们在哪些方面激发了你的兴致?
我写下《恋物癖者》,自诩天生是个恋物癖者。关心植物的生长、岛屿的分布、气候的瞬息状态,身边之物让我亲近,而距离我远的事物使我好奇。就像我热衷赴电影院、博物馆、摄影展览会,看影像、照片乃至实物。我所置身的建筑,它不是单一的建筑,它是建筑们,是一个让人好奇的陌生环境。我总是在幻想回归所见的场景中去。哪怕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差,在泉州晋江或者厦门思明区的街道上晃荡,我会记下路灯的颜色、形状、数量,也会留意途经的巴士站台,看它的站牌,诸如站牌上的首发与尾发的时间以及站牌之上我一概不知的地点。在眼睛与广场、高架桥、公交总站、酒店、酒店里的电梯与消防逃生铁梯、超级市场、招贴、近乎废置的电话亭、隧道、橱窗与橱窗里的衣物、有积水的十字路口、斑马线的亲近中,我感受这存在的乐趣,以此对抗并抵消生活的无趣与寡味。
13.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和哪些人坐在一起喝酒、吃茶、侃大山?
选择魏晋,感受魏晋风度。和“竹林七贤”不一定要喝酒、吃茶、侃大山。可以肩并肩坐在马车上沿着一个方向走着,走到无路可走,再换个方向继续。也可以只是躺着看天,等着被树叶和秋风打败。让该来的客人不请自到。
14.你喜欢在什么场合与朋友们见面呢?酒馆、茶馆、饭馆,抑或家中?说一说你的理由。
我喜欢朋友偶遇的场面。我们的世界那么的小,偶然相遇最是惬意。没有什么目的性,不谈主题,想到什么说什么,说完也就各自回去。自由,舒适,畅快。我就曾在旧书市场、打折扣的书店、回家的途中遇见他们。分享淘书、购书或者什么也没买的喜悦。我一般不主动联系朋友出来,有也是在德克士的白色塑料餐桌前和朋友喝黑色的常有小气泡的可乐,谈些不着边的话。
15.你相信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吗?你的酒量如何?有无酒后写诗的体验?
相信,李白说的我都相信,黄河之水天上来不是么。
我的酒量很一般。同事说你要学着喝酒。其实,我不是不会喝酒。
没有酒后写诗的体验。
16.在你的生命中,爱情占据怎样的位置?
爱情在生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甚至我的诗歌和小说都要围绕着它。它是生动的物,生动的美。它是注定要被赞美、被疼爱和被伤害的。
17.庄子有篇文章叫《齐物论》,论及物我关系时,他是这么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请问:你对庄子的这一说法是如何理解的呢?
这是物的工具说。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海德格尔提及的物的自在的气质。物我,该是平等和谐的关系。
18.你读西方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吗?他们中哪些人被你引为同道?
最近在读德国70后的作品。比如《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夏屋,以后》等。还有反复阅读的《焦灼的土地——以色列短篇小说选》、《绿荫山强盗》等短篇小说集。这里简单谈及《夏屋,以后》。这书是翻着看的,挑漂亮的篇目先看,先挑了《飓风》,因为我这常有台风。作者尤迪特·海尔曼确实是有意思的人,可能跟她个人的职业以及职业背后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生活有关,“年轻,从事艺术,其现实和感情生活都处在一种不定的莫名状态”。她的小说很贴近这个时代,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犹疑,不善与人打交道,过着主题为失败的生活。整本书就是一放大的孤独之书。《飓风》开头的那个游戏很吸引人,游戏就叫“自己——这么——想象——一种——生活”,通篇故事漫着忧伤的气息,想来是女作者的缘故。外界评她,“海尔曼善于将庸常乏味和徒劳无谓化为诗,化为艺术,传递出来自失意世界的信息。”单此这点,就很让我欣赏,并且学习。我想,我们是同路的。往艺术的大道上,没什么隔阂与距离。
19.你在美食方面的造诣如何?你的饮食习惯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些什么影响?
美食方面无半点造诣,就像赏花的人,我是单纯的食家。不过,我会买来食谱学习烹饪煮食的,我有的是耐心。我不提倡素食主义,但天生素食。饮食习惯和诗歌创作的倾向上,都是和人的品性有关。
20.读你的诗,我感觉你是一个好静的人,是吗?
是,非常好静的人。或者说,慵懒,遁世,晒太阳的人。慵懒到懒得言语,懒得露面,懒得要生长。将室内的椅子挪到阳台上,坐享懒洋洋的阳光。我是个选择睡莲的生活方式的人。让事物缓慢下来,一切好似闲庭信步般。
21.同为物主义诗人,请问你如何评价物主义的写作在当下诗歌格局中的表现?
物,自在自得。借用罗伯·格里耶《橡皮》里的一句:这些房子的外表朴素严肃,都是用红色小砖头精工砌成,给人的印象是阴暗、结实、单调、耐心。
22.最后,我们轻松一下吧:如果你突然拿到一笔巨款,不允许拒绝,对这么一笔巨款,你将会作何处理?
花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