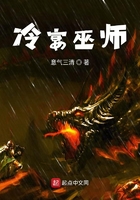小雨落在白马河,
也落在北京的后海,巴黎的左岸,
小雨不是同一片雨。
一片雨与另一片雨之间
隔着晴,多云;
又或雨,但不是小雨。
想到年初那么大雪,
七十年前,诗人写下: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而我和他之间隔着
尘世的光阴,以及诸多不解。
小雨停在白马河的上空,
就像一个故事的开头:
雨滴追逐着雨滴,
叶子颤动,枝丫摇晃,
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
收进衣物,我为这个故事
记起一句张羞的话,
他的“雨和朋友”:“——就像他
无法带走光熙门北里的
任何一场雨水:无法留下。”
我眼中的你的镜头:
走散的,松了鞋带的布帆鞋;
迟来的,人流长长的368路巴士;
白短裤,绿人字拖鞋,紧挨着塑料水桶。
你置身一辆散架的单车,
一个北京胡同的角落
和没落幼稚园的传达室门口,乃至在
斜放的,印有景田百岁山的
蓝色遮阳伞对面。
茫茫大海,横断山脉——
就像在巴黎的梧桐树下,
置身雨天的白马河畔:你可以。
就像消解一个场景,
人世里寡欢: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