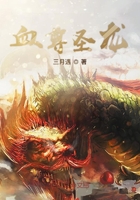“疽发背而死”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一个人,最后因患一种叫做“疽”的病,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搭背”,不治身亡。旧时代,因无抗生素类药,“疽”,西医叫做“痈”的恶性皮肤病,很难治愈。
通常用“疽发背而死”这五个字,加诸于谁的盖棺论定上,可以肯定,这个家伙生前,大概不是东西。人之常情,对死者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假如某个人因患此病而亡,并非臭名昭著之徒,也非行止恶劣之辈,死就死了,不会特别指出此人是“疽发背而死”的。
凡格外注明这个人,最后死于“疽”,而且将“疽”的所患部位,说得很具体而又明确,“发”于“背”,在那里烂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大窟窿,这种很丢人的死,不同于一般地死于非命,比较可耻。因此,这五个字,其落笔的侧重点,不言自明,告诉你,是报应。
中国人讲报应,外国人也讲报应。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书前,就从《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中引用了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每翻开这部不朽之作,先就看到这两行近乎谶语的词句,常有触目惊心之感。
凡是老百姓对之无可奈何,除了诅咒外,别无他法,只好任其作恶的家伙,最后,上苍总是有办法治他,或让其本人死得难看,或让其子孙后代付出代价,这种天道好还的惩罚,就叫报应。中国人相信老天爷,会主持公道,外国人则相信上帝,会惩罚恶人。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上帝正是这样实践着他的诺言,那个把耶稣出卖的叛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子,将他师傅的行踪,透露给祭司长和长老,还引着兵士,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客西玛尼园去搜捕。耶稣绑上十字架,处死了以后,他快活了,但报应跟着也来,就在他那块用赏金买到手的田里,“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使徒行传》),于是,那块田叫做“血田”。
这种“血田”的报应,和“疽发背而死”也差不多。
不过,中国人的报应观,比较复杂。信和不信,视这个人的状况而定。弱者信,强者通常不信;强者弱了下来信,弱者强了以后就不大信;无权势的人信,有权势的人通常不信;受人欺侮者信,欺侮人者往往不信。所以,讲求报应,相信报应,或者指望报应者,都是处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那些放开手脚,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倒行逆施的百分之百的王八蛋,心里绝无报应这一说的。因此,弱者,只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地念念有词,寻求心理上的自慰和平衡了。
若是老天开眼,碰上哪个坏蛋,遭了“疽发背而死”的现世报,而不是来世报,百姓就忍不住兴高采烈。看到那些祸国殃民的人,那些作恶多端的人,那些缺德透顶的人,在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老天爷就让他活受罪,让他背上害大疮,让他流血流脓不止,让他连心肝肚肺都烂得生蛆,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痛苦万状,又丢人现世的死去,能够亲眼目睹坏蛋受到如此报应,应该说是处于可怜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长出一口恶气的最高境界。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慵懒的老天爷,总是睡不醒,眼睛老闭着。或好人不长久,坏蛋活千年;或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倒先走了;或整人的人活蹦乱跳,被整的人呜呼哀哉;或那些理应得到报应的家伙,却总是不能有一个“疽发背而死”的结局,而那些受他害的遭殃者,却含冤抱屈而去,饮恨于九泉之下。所以,看到这些戴上白手套后,也掩不住的那双血淋淋的手,好像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地装冰清玉洁,装德高望重,真觉得老天爷应该到同仁医院去看看眼科。
八十年代中叶,一位类似这等戴白手套的某长,在某边陲省份,某次聚会上,晤得当年被他一闷棍打得一劫不复的同事某公,他居然腆着个脸,故作天真讶异状,啊啊,这多年没见,你怎么到得这样一个地方?其实,某公已经努力忘却当年他那张吃人血馒头的嘴脸,经他这样轻描淡写地一问,倒不禁勾起回忆,不由得反诘了一句:至于我,为什么到得这样一个地方,难道你不应该是最清楚的嘛!
顿时,空气中有股缺氧的感觉,这场面很难堪,在座的知道往事的人不少,大家不由得为某长感到尴尬。
但某长却好像突发一时性耳聋,和短暂性的视觉障碍似的,既未听到某公激动的话语,也未见到某公愤懑的表情,王顾左右而言它。转过脸去,与在座的不知五七年打右派为何物的年轻人握手,“相谈甚欢”云云,这是隔天报纸上登的,没有一字提到某公面部流露的那二十年之久的“积愤”。
九十年代末,“积愤”难解的某公,终于在贫病中,走完了一生坎坷的路。而那位给他制造坎坷的某长,至今逍遥于报应之外,优哉游哉地跨过了世纪,道貌岸然而鬼胎依旧,慈眉善目而歹毒如故,真是叫人深感天理之不公,世道之不平。
于是,我想起来清康熙年间的一件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或可说明“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八个字,不会是平白无故的空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经过无数历史经验印证的事实。
恶人总是要堕入阿鼻地狱,这应该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这样希望着。
1665年(康熙四年)8月,京城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人事变动,将一个叫做杨光先的安徽歙县人――瘪三兼王八蛋,一个以捍卫道统自任的伪君子――调任钦天监正。当然,对一个偌大帝国而言,在其统治机器中,有若干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是不会影响运转的。但是,一个在明代做过千户的小官员,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混到国家天文台当台长,也太荒唐了点。不过,这个最后“疽发背而死”的得到报应的家伙,休看他不懂数算,不通星象,谋到这个职位,却是由于此人有着非常之“损”的异禀,害死了几十口子人,才当上台长。而且,一当就是四年。
由于他压根不懂历法,哪月当闰,哪日当食,都一笔糊涂账,老百姓也就跟着他过起了四时八节都不准确的懵懂日子。这是发生在大清帝国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笑话。反正地球也不会因为这位天文台长狗屎而不转,老百姓也不因为该食,不食,不该食,天狗把月亮吃了而睡不着觉。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修养,耐心地等他玩儿不转的时候自动下台,很少把不称职的官僚轰下去的。
“损”是北京方言,意同“缺德”。杨光先的“损”,加上“阴”,比“缺德”,似乎更坏一点。此人当过千户长,可以说是一无所长,但“阴损”,却是强项。大凡一个人,托生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他的投资,本金总是有限的。因此,其精力,其天资,其聪明,其能量,绝不可能都达到百分百。黄鼠狼要是有老虎那份凶猛,也就不必钻进老乡家里偷鸡吃了。惟其短,才另有所长,杨光先就是这样一种货色。
凡长于此者,必短于彼,这就是人类自身的能量守恒定律。在文坛上,也是如此。譬如,大家都挂着作家这块牌子,难免有了成色上的不同。有的作品好,个人品德稍差;有的作品差,活动能量较高;有的作品出色,但拙于世道,断不了挨整;有的作品一般,但在搞个运动,整个人什么的,表现突出。艾青先生活着的时候,曾经以如下语言,形容一位文坛名流:“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却没有一部著名作品。”这是一位朋友在爱荷华听他说的。后来,艾老到澳门去领葡萄牙政府发的一个什么文化奖,我也适在那里访问,曾经问及这句名言,他“呵呵”地笑而不答。
无论如何,说明作家的才力高低与能量大小,不成正比,能量大,才力未必高,才力低,能量未必小。南朝宋时,谢灵运大言不惭地吹过,天下的才力只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他自己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了。因此,才高能小,能大才低,是作家队伍中的正常现象。能量无与伦比,才分屈指可数;政治水平一流,艺术表现一般;作品无可挑剔,思想稀里糊涂;整天夸夸其谈,著作没有一本……这种有长有短,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实际状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假如那位被艾老评价的名流,能写出著名作品的话,也就没闲心、没闲空在五七年那样兴致勃勃地大整特整别的作家了。这位名流,只要来了运动(除“文革”外),马上精神焕发,两眼冒光,说明他天生有这方面的禀赋。
康熙年间的杨光先先生,大概也是如此,本事有限,便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别人倒霉,给别人制造不幸方面,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整人,是一门学问。我翻了好几部辞典,对“整人”的释义,都是说:使别人“吃苦头”。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美化整人者的嫌疑。试想,一个可怜虫,被别人整得送了命或差点送了命,被整得妻离子散或接近于家破人亡,被整得一劫不复或即使平反也等于交待一生,是能用“吃苦头”这个轻松的字眼,来概括那全部苦痛的吗?
若我来编写“整人”这个词条,那释义应该是:一个绝非善类的家伙,在不担任何风险的状况下,倚靠身后的强势力量,以一种伪正义的姿态,去打击一个不会回手的无辜者。这才比较贴近“整人”的准确含义。
杨光先就是这样一个整人者,一个自封的道德警察。据《清史稿》:“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谓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
他深谙黄鼠狼单拣病鸡咬的道理,一只病鸡,也就是失去抵抗能力的鸡,而一只失去抵抗能力的鸡,也是不用费力就可能咬住并咬死的鸡。在十五世纪的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外国佬,被视作异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这个外国佬,引进的伽利略天文学理论,改了中国老祖宗的历法,被视作邪说,也是不必奇怪的事。这位来自日尔曼的科隆人汤若望(Schallvon Bell,Adam),恰恰是只毫无疑义的病鸡,不咬这只异端邪说的外国鸡,还咬谁?
黄鼬咬住一只病鸡的时候,决不假道学,假正义,目的就为果腹。而整人为业如杨光先者,通常不会承认自己是一只尖牙利齿的黄鼬,而总是要拉起坚持些什么,捍卫些什么的大旗,振振有词地来咬你。所以,他著《摘谬论》和《辟邪论》两书,高调与棍棒齐下,批判和揭发同举,攻击汤若望。但是,他白忙活了,背后没有强势力量的支持,跳嚷半天,无人响应,因此,只好草草收场,不得不等待适当时机。
平心而论,那位怀着宗教热忱的日耳曼人,背井离乡,不远万里,1622年(明崇祯二年),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起到科学启蒙的作用,应该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明代的政治不那么腐败,农民不被逼得起来造反,从十五世纪就赶上西方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也许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作为耶稣教传教士的汤若望,来到京城,很快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如徐光启,如方以智,成为朋友。“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清史稿》)。崇祯于是任用这个外国人,来当中国天文台的主管历法的官吏,读史至此,真是为明朝末代皇帝喝彩。这种胸怀和气魄,比之今天那些对改革开放政策还在摇头不已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顺治给朱由检立碑时评论道:“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认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皇帝,因为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其封闭内向的封建社会,“一板不许下海”,执行锁国政策,中国是从那时开始,便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祯重视汤若望的西人历法,改造传统的大统历,比现在那些闻夷,闻洋,闻西方,闻资本主义则倏然色变者,有这份择善而从的既清醒又开明的心态,难能可贵。
据后来揭发杨光先的材料,说他“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何谓“棍徒”?就是有事没事,逮谁就咬谁一口的青皮混混之流,杨光先稍稍人五人六一点,就有一张道德警察的面孔。他想咬汤若望,但崇祯拍板用这个外国人,他也就不敢张嘴龇牙了。等到清人入关,他认为时机到了,谁知满族统治者既没有汉族那种因循守旧的习气,也没有祖宗之法的束缚,多尔衮甚至会想:你崇祯帝设局令一个老外来修改历法,我摄政王干嘛要承袭你们汉族的华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汤若望为钦天监第一把手。并将汤所制定的西式历法,命名为《时宪历》,颁布实行。并给汤若望加官晋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旋又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清史稿》)。
已经剃了头,成为清人的杨光先,什么官位也未捞到手,就更加不开心了。何况此公整人成瘾,整不了人,鸡在眼前,硬是咬不着,急得直磨牙,直咂嘴,憋得他五脊六兽,浑身不得劲。估计他后来疽发于背,是从此时就种下病根,也未可知。
跋扈的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年轻皇帝屠灭其家族,肃清其党羽,修改其政策,进行全面的秋后算账,半点也不手软。杨光先认为这位皇帝,或许由于汤若望受多尔衮信任会加以排斥。孰料顺治对这个外国人毫无芥蒂,相反,很友好,或者,很感兴趣,这又让他灰心丧气好一阵。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汤若望”条目说:“汤若望遂成为少年皇帝顺治的心腹顾问,尊为长辈。”外国人的说法,确否存疑。但这位外国传教士治好了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病以后,顺治准许汤若望在西安门一带择地建筑教堂,允许传教,是见诸正史的。我不知道,汤若望奉旨修建的这座教堂,是否就是现在尚存于西什库的西堂?
杨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么能用洋鬼子的历法呢?怎么能让洋鬼子在京都建堂传教呢?他大声疾呼地上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术,日食都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那张“天丧予”的面孔。这番高论,也就是“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最早版本。杨光先要是能活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话,很可能被江青礼聘进中央文革小组当顾问的。
总算熬到顺治十一年,杨光先突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
那时没有社论,没有文件,只有谕旨,那时的整人者都从这些一道道的谕旨中,了解最高当局的动向。这份宗人府收到的谕旨,别人读了也许不会在意,皇帝说:“宗学读书宗室子弟既习满书,即可阅读已翻译成满文之汉书,永停习汉字诸书。”但杨光先读出了谕旨背后的文章,永不许满族子弟读汉文书籍,这表明汉族文化已在统治者族群中,占有非同小可的位置。
这给急不可耐想咬谁的他,注入一针强心剂。不到二十年功夫,入主中原的满族人,已经被他们所征服的汉族同化了,不禁心中窃喜。在屋里一跃而起,摩拳擦掌,因为满人愈汉化,必然愈益认同汉族的宗法伦理,礼教传统,三纲五常,和华夷有别,拒外排外的思想,这样,他这个夷汉之防的道德警察,兼打手的棍徒,也就有事可干了。
“满洲人入关后,多习汉书,入汉俗,帝虑及长此以往,将渐忘满洲旧制”,因此,发出这条谕旨,是统治者不得已而设置的意识形态上的堤防,但是,不管如何防范,挡得初一,挡不了十五,挡得一时,挡不了长久,是无法抵御强势文化的日久天长的冲击的。回顾有清一代,康熙宠臣明珠,他的儿子纳兰性德,能用汉文写出最优美的诗词,直逼南唐后主;而满族自己的文字,连满人也大都不识;八旗子弟,提笼遛鸟,不务正业,过着优裕生活,最后,悉皆变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而从帝王到贵族的满族统治阶层,除了妇女天足这点异同外,满汉之别,几等于无。
因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其流向总是如水一样,由高处往低处流去,低文化的民族可能凭武力征服高文化的民族,但拥有高文化的民族,最终会使低文化的民族,在精神上处于臣服的地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变的趋势。因此,清廷还想保持白山黑水间努尔哈赤部落的族群特色,关外风俗,萨满教义,弓箭文化,绝对是徒劳的努力。
哇!杨先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大清王朝的汉化趋向愈来愈对他有利了。果然,如他所料,顺治驾崩,康熙登基,实际掌握朝政的四辅臣,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倾轧不已,但其华夷畛域的儒家礼教精神,拒外排外的华夏中心思想,却能与杨光先如此卑微的小角色,同声共气,上下一致地合拍起来。“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清史稿》)。“康熙三年,六月,乙卯(二十六日),杨光先复具《请诛邪教状》于礼部。此举深得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
于是,杨光先放肆地对汤若望大张挞伐,状子送呈御览。一,“天?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居心叵测,想缩短大清寿命;二,“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阴谋险恶,竟敢在风水上做手脚;三,“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奏春气已应”,擅改法度,妄断节令。
所列这些今天看来纯系扯淡的罪状,却让那班与杨光先差不多水准的辅政大臣,着实当了回事,于是,以捍卫祖宗法度,坚持华夷大防的名义,“下礼、吏两部会鞫”。
结果,便是一场人头落地的惨剧。
“清廷遂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审讯过程中,年逾古稀的汤若望,激动过度,血压上升,发生脑血管意外,中风不语,有口难辩。他的年轻伙伴比利时人南怀仁(Verbiest,Ferdinand),刚到中国不久,汉语讲得不够流利,无法为之申诉,于是罪行成立。
什么叫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汤若望这回可真的让这只可怕的黄鼬,咬得死死的。当将汤若望押往刑场的时候,几位辅政大臣觉得汤“年已衰老,且效力前帝,得免死”。决定让其流徙到边远地区,诸如押往黑龙江宁古塔为披甲人奴之类。其实这更缺德,那会死得很惨。幸而孝庄太皇太后出面进行干预,汤若望得以释放出狱。但很快,这位在中国传播过伽利略天文理论的日耳曼人,终于奄奄一息地死了,埋葬在这块对他来讲是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杨光先这一状,损到极点,缺德也到了极点,凌迟的,杀头的,流放的,坐牢的,使得钦天监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白日见鬼的衙门。如果按辞典说,整人是使人吃苦头,这种人命关天的苦头,也太可怕和太痛苦了。如此伤天害理作恶多端的家伙,得不到报应的话,世无天理,老天也太不公道了。
然而,迟迟不来的报应,真让人等得不能宁耐啊!
汤若望死,“监内精于西法历算之三十余名监官翦除干净,废新历《时宪历》,恢复《大统历》”,“擢杨光先为钦天监正”,这就是发生在康熙四年八月京城里的一项人事变动。
杨光先坐在八人抬的轿子里,来到钦天监上班。虽然偌大衙门里死气沉沉,鬼影幢幢,但他很得意、很风光地登上了观象台。老实说,道德警察,好当,咬死病鸡,不难,老天爷给了他整人的全褂子武艺,却没有给他一个足以安身立命的饭碗。仰望着星斗璀璨,河汉亘天的夜空,全不知子午卯酉,连整屁也放不出一个。
切不要以为他会生出当初不如少整人,多用功,少作损,多读书的遗憾,不会的。别看他“既不懂西法历算,亦不通中国传统历法”,但“贬汤若望之历法,件件悖理舛谬,认为西洋之学乃左道之学,西洋人所著之书,所行之事,靡不悖理叛道”,搞大批判,上纲上线,这是所有整人者最拿手的看家本领。
但是,天文台仅靠耍嘴皮子能玩得转吗?
“自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后,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错误屡出”,因其“对历算茫然无知,采用在江南发现的元代郭守敬仪器,测算历法无效后,又查一千二百年前北齐候气之法”。其荒唐无稽,其倒行逆施,连开始亲政的康熙,也觉得问题之严重。“于万般无奈之下,杨光先乃以‘身染风疾,不能管理’相推诿,于是重新起用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
这是康熙八年春天的事,老百姓已经过了四年没有准确历法的岁月,现在终于等到这位逆历史潮流、反科学进步的主角,到了谢幕的时候了。“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报应,朝着这个既“损”又缺德的家伙,渐渐地逼近。杨光先藉以“推诿”的“风疾”,在汉语中常指下列三种病症:一是风痹,半身不遂;一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一是麻风病。这三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死。然而,就像托尔斯泰引用过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一样,老天爷(如果有的话),不会让这个整人者死得那么痛快的,不让他“疽发背而死”,不让他死得难看,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是,听说洋鬼子又要进钦天监,本来已经病了的杨光先,忍不住还是跳将出来,急不择言地上书:“臣监之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他甚至危言耸听:“若将此九十六刻历日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不过,经过“观象台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款款皆符’。因此,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历法,交由南怀仁推算。”康熙在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中,“持谨慎态度”,据《清史稿》载:“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他明白了孰是孰非,便作出抉择。终于在这年三月,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给汤若望冤案平反,另一方面,尽管受害人上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康熙倒也没有惩治这个棍徒,放了他一马。
虽然皇帝高抬贵手,报应却不能逃脱。结果,“杨光先以衰病之身,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据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抬着这位背部溃烂的疽患者,自然是流血流脓的一路,也是臭不可闻的一路,更是不流尽最后一滴坏水,不让他痛快死去的一路,这样酷烈的“血田”式的报应,难道不是罪有应得吗!
按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疽”,是感受风温湿热之毒,以致经络阻隔,毒邪湿聚而生。或由于情志内伤,气郁化火,劳伤肾精,火邪炽盛;或由于恣食厚味,脾胃失运,湿热火毒内生而致。总而言之,患者都是因为有一股邪火,有一份内毒,才在背上爆发出来。
具有这类邪火和内毒者,在我的周围,也时有所见。或憋得老脸铁青,跟谁都过不去,或憋得两眼冒绿,看谁都不顺眼。正是这股子无名毒火,在脏腑里作怪,才永远一副“天丧予”的德行,像瘟神一样,甚至如今大家好容易过上的一点好日月,也恨得牙痒。碰上这些“疽”的早期和前期患者,通常,我赶紧闪过一边,让这帮老爷先走,惹不起,躲得起。这也是鄙人受了数十年无妄之灾以后,才学会的一点聪明。虽然,我也知道,报应说,通常是不灵的,不过,想想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也足可以浮一大白。
满清末季,屡败于列强,所签不平等条约都以割地赔款了事。其中《马关条约》,赔款为二亿两,《辛丑条约》,也就是庚子赔款,为四亿五千万两,两者相加,为六亿五千万两,“仅和□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这贪污犯,当为中国之最,然而,他抠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