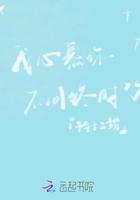近人治宋诗而比较了解王安石的要推钱书先生。他在《宋诗选注》中评王安石诗的一段话里曾说:
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辞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
这段话虽含贬讽之意,基本上还是搔着了宋诗也包括王安石诗的痒处。关于王安石诗的语言,实即遣词用字,后人举例总是推崇“春风又绿江南岸”和《书湖阴先生壁》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并认为后者是以“汉人语对汉人语”。现在索性把钱先生的这两段评注转引如下:
这句也是王安石讲究修辞的有名例子。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等等(洪迈《容斋续笔》卷八)。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宋诗选注》页56,“春风又绿江南岸”句评注。)
“护田”和“排闼”都从《汉书》里来,所谓“史对史”,“汉人语对汉人语”(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曾季狸《艇斋诗话》);整个句法从五代时沈彬的诗里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所谓“脱胎换骨”。可是不知道这些字眼和句法的“来历”并不妨碍我们理解这两句的意义和欣赏描写的生动;我们只认为“护田”、“排闼”是两个比喻,并不觉得是古典。所以这是个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宋诗选注》页55,“一水”、“两山”二句的评注。)
钱书先生认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是王安石的得意语,我则以为那整首诗都是为王安石所偏爱的。他的《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第一首末句云:“金山只隔数重山。”然后自注说:“某旧有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自绿江南岸,明月何曾照我还。’”第三首前两句云:“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则原诗的第二句和第四句都曾重说过一遍了。此外,作者在《北山有怀》一诗中还写道:“伤心踯躅岗头路,明日春风自往还”,意境也差不多。其实《泊船瓜洲》一诗在王安石集中并不是最精彩的,第三句各本都作“自绿”而非“又绿”,鄙意“自绿”比“又绿”好,好处在“自”不在“绿”(详下篇拙文)。至自注末句作“何曾”不作“何时”,疑为作者笔误,仍以作“何时”为是。而“一水”、“两山”二句之所以脍炙人口,也不在于用了什么“汉人语”,而是由于形象鲜明突出,造语活,创意新。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最近读王安石的古诗,发现在钱先生所说的各种情形之外,还有另一面,即所用的字或词看来并不新鲜,其实却是“不经见而有出处”的。如《省兵》云: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未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
其中“省兵当何缘”一句很容易被人忽略。粗粗一看,好像“何缘”即是“缘何”,等于现代汉语的“为什么”或“何故”的意思。但上面已有一句“万一虽不尔”,则下句应当是深入一层的问句;如果只泛泛讲成“何故”,反显得累赘而不接气。检《方言》卷十三云:“毗,缘,废也。”钱绎《方言笺疏》云:
《管子·侈靡篇》云:“好缘而好驵。”房注:“缘即捐也”。《说文》:“捐,弃也。”《众经音义》卷六引《仓颉篇》同。捐与缘同音,弃与废义亦相近也。
“捐”即“蠲”,是废除、减免的意思。然则“当何缘”者,是说省兵的结果到底捐除、减省了什么呢?(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有“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薄书之弊”的话,“缘”也应解作“捐”,“缘绝”即“捐弃”、“弃绝”之意。)接下去说这些兵骄惰成性,即使还乡也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衣食犹兵然”,还是跟没有省一样。这样讲上下文就贯穿一气了。
至于以“史对史”,以“汉人语对汉人语”,这在作旧诗的人并无什么规定,一定要上下句用语都出于同一书或同一朝代。不过古人写诗,在语言上总要铢两相称,不能深一脚浅一脚,忽古忽今,忽雅奥已极,忽鄙俚太甚。这从唐代的李白、杜甫,下而至于元白、韩孟以及李贺、李商隐等,都已注意及此,只是王安石对此格外下工夫罢了。这里举一浅显例子,即以《毛诗》对《毛诗》者,如《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法利害见寄》中的两句:“哿矣富阡陌,哀哉此无糗。”这一望而知用的是《小雅》。《正月》篇云:
哿矣富人,哀此独。
又《雨无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王安石以“哿矣”对“哀哉”,显然径从《雨无正》搬了过来,工稳是不消说了。但上句作“富阡陌”,下句却不说“贫无糗”而作“此无糗”,则是兼用《正月》的“哀此独”和《小雅·鸿雁》的“哀此鳏寡”。这里的“此”,正是指的“独”和“鳏寡”,比径用“贫”字还显得丰富有力。但首先要有个前提,即必须知道王安石是在用《毛诗·小雅》里的典故或成语才能体会得出。钱书先生在评王安石时曾说:
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努力的烟幕。
又说:
除掉……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
其实,艺术上的原因原是服务于社会原因的,语言的色泽、深度和富于暗示力,都和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分不开。但引人注目和值得玩味的毕竟是那些经过锤炼和推敲的、即在造语用字上有其独到之处的诗句。即以上引“哿矣”两句而论,正是全诗中深刻有力的警策语,如果把“哿矣”、“哀哉”这些词汇去掉,这两句诗就肯定不会有较强劲的艺术效果。可见他在写诗时用这样的字面也并非出自偶然或只为了追求以《毛诗》对《毛诗》,而是着力要写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