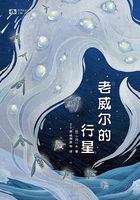四月十二日,星期二,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这消息震撼了马克汉。跟往常一样,当他一激动便会站起身,双手背在身后踱来踱去。希兹慢了半拍才了解这则信息的重要,正用力抽着口中的雪茄——说明他心里正忙着整理案情。
两人都还没来得及开口,大厅后方的门突然打开,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了起来,朝会客厅方向走来。从杜瑞克夫人处回来的贝莉儿·狄勒,出现在走廊上。她满脸疑惑,目光落在马克汉脸上。她问:
“今早你对艾多夫说了什么?他的情绪十分糟,他几乎把整间屋子的每一个门锁、窗户都测试遍了,好像在担心什么窃贼闯入似的。他还恐吓葛瑞蒂,让她晚上睡觉前得把门上锁。”
“你是说,他警告葛瑞蒂?”万斯说,“真有意思……”
女孩的目光移向万斯。
“是的,但是他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他显得十分紧张,而且神秘兮兮的。最奇怪的是,他不肯走近他母亲……这究竟怎么回事,万斯先生?我感觉,像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我也不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万斯的声音有些低沉沮丧,“我甚至不敢去了解。要是我想得没错……”他顿了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我们还是再观察观察,或许今天晚上就能知道答案了。不过,就你而言,狄勒小姐,这倒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万斯露出温馨的微笑,问道:“杜瑞克夫人还好吗?”
“她看起来好多了,但似乎还有些事情让她十分担心,我猜一定和艾多夫有关,因为她从头到尾都在跟我谈艾多夫,不断问我,他近来举止有没有什么异常。”
“这种情况下,她的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万斯回答说,“但你可不能让她的态度影响你。好啦,我们换个话题吧。据我所知,昨天晚上,到剧院看演出之前,你在图书室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告诉我,那时候你的皮包还在你身边吗?”
她被这问题怔住了,迟疑了一会儿,她才说:“我进到图书室时,把皮包跟外套一并放在门边的小桌子上。”
“是那个放着钥匙的鳄鱼皮包?”
“是的,西古德很讨厌晚装,所以每次我们一块儿出门,我都穿着白天穿的衣服。”
“也就是说,除了那半个小时,接下来整晚你都没离开过这皮包。今天早上呢?”
“早餐前,我带着皮包出去走走,之后我把它放在大厅的衣帽架上,大约放了一个小时。不过,大约十点钟我要到玛意夫人那儿时,又将它带着。也就是在那时,我发现那短枪被人放了回去,临时决定先不去玛意夫人那。在你跟马克汉先生来前,皮包被我留在楼下射箭室里。之后我一直随身带着它。”
万斯向她致意,感谢她的回答,然后说:
“现在,我们已经对皮包的行踪了解得非常清楚了,请你也将这事情全部忘掉。”她显然喉咙中哽着问题,但万斯很快地接口,浇熄了她的好奇心,“你叔叔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你到广场去吃夜宵,所以,你一定很晚才回家的吧?”
“平常我跟西古德出门,都不会太晚回家的,”她答道,语气中有些许抱怨,“他不喜欢夜生活,我本来要求他玩到晚些回家,但他看起来痛苦不堪,我也不忍心再强求。我们到家时十二点半。”
万斯微笑地站起来,说:
“你实在有非常好的耐性,忍受我们这些愚蠢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去找帕帝先生,看看他有什么高见。通常这时他都在家吧?”
“我确定他在,”女孩陪我们走向大厅,“你们来之前不久他才离开,他说他必须回家一趟。”
我们正要踏步出门,万斯却停了下来。
“哦,对了,狄勒小姐,有件事我忘了问:昨晚你和安纳生先生回家时,你怎么知道是十二点半?我发现,你并没有戴手表。”
“西古德告诉我的,”她解释,“我有些气他这么早就带我回来,进到大厅时我故意刺激他,问他现在才几点钟,他看看表,说是十二点半……”
就在这时,大门打开,安纳生走了进来,吃惊地望着我们,接着,眼光跟贝莉儿·狄勒相遇。
“小姐,你好?”他亲切地和她打招呼,“看来,你被警察包围了。”然后转头对我们说:“又有什么贵干?这屋子快变成警察局了。你们还在寻找史普立克的破案线索?哈,莫非是‘聪明学生被嫉妒的老师干掉!’不会真是这样吧……”
“才不是这样呢,”女孩说,“他们还挺周到的,我正在告诉他们,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古板,十二点半就把我带回家!”
“我想我宠你已经宠过头了,”安纳生笑道,“对你这种年纪的女孩子来说,这已经算很晚了。”
“沉迷数学的老家伙,实在太可怕了。”她有些生气地回了一句,然后转身直奔楼上。
安纳生耸耸肩,望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然后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看着马克汉说:
“有什么好消息吗?这件新的案子,有什么进展?”他边说边把我们带回到会客厅,“你知道吗,我实在很怀念那孩子,实在倒霉透了,竟然叫‘约翰·史普立克’,取什么名字不好……”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安纳生,”马克汉打断他的话说,“案情没什么进展。”
“这么说,只是来看看老朋友?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午餐?”
“我们有权利,”马克汉冷冷地说,“保留任何调查结果,我们也没有必要向你报告我们的任何行动。”
“果然!案情确实有了令人难过的进展,”安纳生酸溜溜地说,“我本来还以为,我可以成为你们的一分子,现在看起来,很多事情我都被蒙在鼓里。”他缓缓叹了口气,拿出他的烟斗。
万斯一直若有所思地站在走廊上抽烟,显然无视安纳生的抗议。这时,他走进来说:
“是的,马克汉,安纳生说得没错。我们曾经答应过他,让他跟我们同步掌握案情发展,要是他想帮我们,一定得让他知道所有细节。”
“是你自己说,”马克汉反驳,“要是我们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讲出来,会有危险……”
“话虽如此,但当时我忘了曾经答应安纳生先生的话。我相信,他是可以信赖的。”接着,万斯详细地把前夜杜瑞克夫人的遭遇告诉了他。
安纳生仔细地听。我发现,他那玩世不恭的态度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认真思考的表情。他静静坐了几分钟,手里握着烟斗。
“毫无疑问,这是整个问题中相当重要的因数,”他缓缓地说,“虽然这因此改变了我们的侦查方向。我看得出来,这件事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看来,主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可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找上杜瑞克夫人?”
“因为,在罗宾死时,她曾失声尖叫。”
“啊哈!”安纳生坐直了身子,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公鸡罗宾被杀的时候,她从窗边看到了主教。他去转动她的房门门把,算是让她闭嘴的警告。”
“可以这么说吧,我想……你要代入公式里的数值已经够了吗?”
“我想看看这黑色主教棋子,在哪儿?”
万斯伸手进入口袋,掏出棋子,安纳生急忙将它接过去,仔细端详许久。之后,他把棋子还给万斯。
“你像是认得这颗棋子,”万斯说,“你想得没错,是从你图书室的棋盘上来的。”
安纳生点头。
“我想它的确是来自那棋盘,”他突然转向马克汉,话中带刺地说,“为什么要瞒着我?因为我也有嫌疑,是吗?真是太可笑了,把棋子留在邻居家里,算什么天大的罪?”
马克汉站起来,朝大厅方向走去。
“你并没有被怀疑,安纳生,”马克汉回答说,“主教这颗棋,是半夜十二点钟被留在杜瑞克夫人门外的。”
“而我晚了半小时回来,真抱歉,让你失望了。”
“要是你算出公式的值,请通知我们一声。”我们穿过大门之后,万斯说,“现在我们要去找帕帝先生谈谈。”
“帕帝?哦……向西洋棋专家请教关于主教的事?我明白了……可能,里面包含了极单纯的答案……”
他站在门廊下,像个滑稽的稻草人望着我们穿越马路。
帕帝一如往常,没说什么客套话就来迎接我们。他脸上的悲剧感和挫败感,看起来比过去都强烈;在书房里,当他为我们拉椅子时,举止看来像个已经对生命完全绝望的人,只是具行尸走肉。
“帕帝先生,”万斯开场白说,“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进一步了解昨天上午史普立克在河滨公园被杀的案子。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相信,接下来这些问题有必要向你请教。”
帕帝只是微微点点头,说:
“我明白你们的难处。我看过报纸,知道你们正面对一个非常怪异的难题。”
“既然这样,首先,请告诉我们,昨天上午七点到八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帕帝微微涨红了脸,但仍镇定地回答说:
“我在睡觉,直到九点才醒来。”
“你是不是有习惯在早餐之前,到公园里散步?”
“是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过,昨天我没去,因为前夜我工作到很晚。”
“你何时知道史普立克被害的消息?”
“吃早餐时,我的厨子把街坊八卦的话告诉我,接着才在《太阳报》的午报上,看到完整的报道。”
“这么说,从今天早上的报纸上,你应该也看到主教的字条再度出现。帕帝先生,我想请问,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知道得不多,”第一次,那双无神的眼睛出现光芒,“这案子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就数学概率的角度来说,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是的,”万斯说,“说到数学,你有没有听过雷曼—克瑞斯托弗尔张量公式?”
“我听过,”他承认,“杜瑞克在他的书中提到过。不过,我擅长的数学领域不太一样,要不是因为迷上西洋棋,可能我会是个天文学家。撇开钻研复杂的棋局,对我而言最大的满足应该就是探索天空,发现新的星球。我们家阁楼上,还有台直径五英寸的望远镜,是我用来业余观测天文用的。”
万斯仔细地听帕帝答复,并跟他聊了一下毕克林教授在海王星之外发现新星球的故事。这让马克汉一头雾水,希兹也听得一肚子气。不过,后来话题还是回到“张量公式”上。
“据我所知,上个星期四当安纳生在狄勒家,跟杜瑞克及史普立克讨论这公式时,你也在场。”
“是的,我记得,当时确实提起这个公式。”
“你和史普立克熟吗?”
“普通,安纳生介绍我们认识,见了一两次面。”
“史普立克似乎也有习惯,在早餐前到河滨公园里散步,”万斯说,“你在那里遇见过他吗,帕帝先生?”
帕帝睫毛微微动了动,回答之前迟疑了一下。
“从来没有。”他终于挤出这句话。
万斯似乎毫不在意他的否认。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往外看。
“我还以为,从这里可以看见射箭场,但现在才发现,那屋角完全阻隔了视线。”
“是啊,射箭场还挺隐秘的,墙边甚至还有一条空巷子,所以更没有人能看到里头……你们觉得,有人目击了罗宾被害?”
“是的,还看到了其他事情,”万斯回到椅子上,“我想,你不会去射箭吧?”
“那玩意儿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狄勒小姐曾经要帮我培养运动方面的兴趣,但我实在不是那块料。不过,我倒是陪她参加过好几回比赛。”
帕帝的语气中,隐含着极少见的温柔,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也喜欢贝莉儿·狄勒。很显然,万斯跟我也有同感,因为他接着说:
“你应该了解,我们绝无意刺探别人隐私。但由于我们调查中的这两桩谋杀案,背后的动机依然不明,而罗宾先生的死,表面看来会让人以为是为了狄勒小姐争风吃醋而造成的情杀。要是我们能知道这位小姐究竟喜欢的是谁,或许对我们能有些帮助……身为这个家庭的好友,我想你或许知道答案,而且我们希望,你可以保守秘密。”
这时,帕帝的眼神飘向窗外,叹息声也从他口中飘出。他说:
“我总是有种感觉,她跟安纳生终有一天会结婚,但那只是我在乱想。她曾经很笃定地告诉我,三十岁前绝不考虑结婚。”
“也就是说,你并不认为,”万斯接着追问,“她真爱上了史柏林?”
帕帝摇摇头。“不过,”他补充道,“像他这么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对女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狄勒小姐告诉我,今天上午你去找过她。”
“我常会到他们家串门。”他很明显地有些不自在,也有些尴尬。
“你跟杜瑞克夫人很熟吗?”
帕帝看着万斯的眼神闪过一股莫名其妙。
“不是很熟,”他说,“只见过几次。”
“你有没有去过她家?”
“去过几次,但都是找杜瑞克的。多年来,我对于西洋棋和数学之间的关联,一直很有兴趣……”
万斯点点头,说:
“对了,昨晚,你和鲁宾斯坦的棋赛,结果怎样?今天早上我没看报纸。”
“我在第四十四步时弃子投降,”他如斗败公鸡似的说,“鲁宾斯坦看出了我攻势中的破绽,我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个破绽。”
“狄勒教授告诉我,昨晚,当你跟杜瑞克在讨论棋局时,杜瑞克已看到这个结果。”
当时,我真不懂万斯为什么这样直截了当地提起这件事,他明明知道这会刺痛帕帝。马克汉也皱着眉头,暗暗责备万斯的莽撞。
帕帝脸色大变,说:
“杜瑞克昨晚话太多了,”他语带讥讽地说,“即便他没有参加过比赛,也应该知道在棋赛期间那种讨论是被严格禁止的。不过,说实在的,我也挺佩服他的。我以为我之前那一步已经解决了问题,但杜瑞克想得更远,他的分析一点也没错。”语气中有些自卑跟嫉妒,我能感觉到,这温和的人,已经痛恨杜瑞克到极点。
“那盘棋下了多久?”万斯问。
“到一点多钟,昨晚一共才下了十四步。”
“很多人在旁观赛吗?”
“那么晚,那样的人数已经算很多了。”
万斯按熄烟后站起来。当我们朝大门走准备离去时,万斯突然停下,转过身来望着帕帝,说道:“你知道吗,昨天半夜,主教又发威了。”
这话一出,帕帝十分震惊,他站起来,似乎遭到极大痛苦,脸色惨白。整整有半分钟的时间,眼睛动也不动地瞪着万斯,嘴唇不断微颤,一句话也没说。接着,就跟下了极大的决心,他僵硬地转身走向大门,颤抖的手撑着门,让我们出去。
马克汉的车停在七十六街上杜瑞克家门前,当我们沿着河滨大道朝车子走去的路上,马克汉质疑万斯最后说的那些话。
“我的目的是希望,”万斯解释道,“让他大吃一惊,看看他是否对此事有了解。但天晓得,马克汉,我实在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他竟然这样吃惊,我实在搞不懂,完全搞不懂……”
接着,他陷入沉思。正当车子在七十二街上转入百老汇大道时,他仿佛突然回过神来,指示司机去薛尔曼广场饭店。
“我想知道更多有关帕帝跟鲁宾斯坦那盘棋的细节。说不上原因,我也还没想清楚,但自从狄勒教授跟我提起这棋局之后,我就一直有这个念头……从十一点钟下到一点钟……对于只下了四十四步还未结束的棋局来说,这的确花了很长时间。”
我们的车在七十一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交叉口靠边,万斯下了车,身影消失在曼哈顿西洋棋俱乐部里。他在里头整整待了五分钟,回来时手中多了一张写得满满的纸条,不过脸上没有雀跃的表情。
“我原有个疯狂而有趣的假设,”他微笑地说,“现在,这个假设有了具体的证据支持。我刚刚跟俱乐部的秘书谈过,昨晚的比赛前后花了两小时又十九分钟,扣人心弦的一战,吸引了很多会员棋迷和看热闹的人围观。十一点半的时候,旁观的人都以为帕帝会赢,但接下来,鲁宾斯坦沉着应战,最后一一破解了帕帝的布局——就像杜瑞克所料。真了不起,杜瑞克这人……”
万斯对这发现并不十分满意是显而易见的。果然,接下来他说:
“刚才查这件事时,我在想,可能得学学希兹警官,做点一般办案程序该做的事,所以,我把昨天晚上的棋步借来抄了一份,等哪天闲着没事,也许可以拿出来复习一遍。”
他格外谨慎地把那纸条折起来,放到皮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