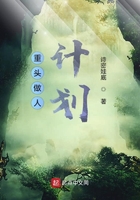“国泰——民安!天下————”五更天了,这是也守更人的最后一通吆喝:“——太平!”梆子声和格滋格滋涉雪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连绵下了几天的雪渐渐也停了下来。
这是咸丰七年的冬月底了,依照西洋的耶稣教历,正是1858年的一月份,但在帝国的心脏北京,自然还是在咸丰七年的严冬。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冬月廿七日晚上开始下的一场大雪一直断断续续,絮絮扬扬飘到廿九早上,差点快要进年关岁尾的腊月了,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阴暗的白色之中,厚厚的积雪像是这个帝国缠身的病症一般,看上去没有一点消融的迹象。
这会儿天色还早,白皑皑的街面上并没有多少人,除了供差大小衙门要早起的仕宦人家,也就是几家忙活着做早点生意的小店已经开始在蒸腾着包子点心了,今年米粮价钱高涨,做小生意的开张早些也能多沾些光儿。几天的雪积下来,反映着灰沉沉的天色,倒也省了点灯的油钱。
顺天府衙门十来个苦命的差役哆嗦着抄着手骂骂咧咧两句,列成一队开始巡街,尤其是关照路边有没有冻死的饿殍,须知再有一会功夫,便是应差的高峰期了,若是万一有什么碍眼的东西落在哪个不对付的都老爷眼里,上表弹顺天府一章,老爷们日子不好过,下面的小虾小米自然也不得安生。
尤其是这南城。
虽说北京城向来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说法,但毕竟也有例外,比如城南琉璃厂附近的几条胡同里,便颇住了些小京官——没别的,这里地价也贱,富贵的地方落不下脚,只有到这等贱地方住下。再一个,打清朝开国以来满汉分城居住,这里便因是左近琉璃厂的缘故,聚集了不少汉人大小官员的的寓所,无非是有钱的没钱的大小贫富有差而已。其实俗话说的好,天子脚下,哪里不是和光同尘?
带队的苦命班头叫邢彪,昨日便层层级级的得了转发下来的府尹黄大人的谕纸儿:年关岁尾,顺天府首善之地,要做出表率来,天寒地冻,大雪封路,今年京师粮价大涨,更易有所不测,京师外围各巡检衙门,顺天府诸县,都要每日派人巡街,境内但凡有一个饿殍冻尸,年节就不要想安稳了。所以这才有了今天这一大早南城巡检司衙门排除各路差役出门巡视的事情。
只是这天大地大,便是皇命也敌不过肚皮大,就着雪地反光喝了一通豆汁就油条之后,十来号人这才热乎起来,哈着热气搓着手上了街面,几个平日里亲近的差役便瞄着头儿的脸色发起牢骚来。
“妈的,搁这当差也他娘的十好几年了,前后也伺候过七八号大爷,就数这位爷难伺候,往年哪有这等子事?怪道的二爷提起他没个好脸色儿,******这下冰刺儿的天叫老子出来趟这冰愣愣的地儿!我说头儿,昨儿袁小五来窜门,其它各路都说二爷交待了,这差事不用上这么大的劲吧。万事有二爷罩着呢!要不,咱们也都回去吧,我估摸着咱南城二十好几小队,这会儿也就咱们这一路上了路吧?”一个差役小心翼翼的避过一块结了冰的坑洼地而,凑在邢彪身边发牢骚。
你懂个屁!邢彪心里嘀咕一句,嘴上却没作声,回头笑呵呵的看了他一眼算是应付了。转过脸来在街面上扫了几眼,转左进了贾家胡同。
一面走着,一面看着,一面有一声每一声的吆喝着下属们,邢彪心里默默的在想着他自己的心事。这么多年差办下来,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在这顺天府这南城巡检司衙门里做到不大不小一个小班头,管着十六七号人,就是因为自己比身后这帮混吃等死的爷们聪明些,知道好歹些,眼睛也亮堂些。二爷什么人?人家旗下大爷,后台硬梆梆的,你跟人家比?上头一棒子扫下来你顶着还是他顶着?
这差事不能不做。这阵子不住有小道消息往耳朵里传,都说这府尹黄宗汉大人从夏天里就传要高升,他是做过黔抚,川督等地方要职的人,调任进京的封疆大吏,眼下已经是内阁学士,刑部右侍郎兼署顺天府尹了,再高升那还得了?一说是要外放封疆练团,也有一说是要进军机,无论哪一条,都不是眼睛里能叫你揉沙子的。如今就要撂这顺天府的摊子,他这般从来爱惜体面的人一定会做个善终的样子出来的,这时候一丁点纰漏都不能出,虽说是到了这冬天了也还没动静,听说是刑部差事上颇得罪了人还没提调成,但爷们的事情谁说得清楚?指不定哪天就升发了呢!就冲这一点,哪怕天上下刀子下炮子,今天这差事也得办。不光办,还得办的干净利索。
再一个,今年朝廷总算有些好景象,自打咸丰爷登了宝座以来就扯了反旗的长毛这一年闹了内讧,石达开扯了人马闹分家,说不准这七八年的乱子就要这么平定下来,这节骨眼上,朝廷老子们格外要注重京师颜面。大雪下了这多天了,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黄大人官儿升不成,你们这些小喽啰蛋子能有好日子过?
想到这里,邢彪回头又吆喝了一嗓子:“跟上些!他娘的咱老爷们精神些,巡完了这贾家胡同,就一条潘家河走一遭完事儿了,打发完差事咱兄弟喝酒去!辰巳时分咱酒足饭饱还有差事呢!报国寺放粥铺一直放到腊八,都盯着些!别叫那些穷蛋子们坏了大事!”
叫他这么一吆喝,差役们果然都提了点精气神来,大步大步揣着半截小腿肚深的积雪迈进胡同深处。
这里住着一家挺重要的小京官,邢彪往前看去,这爷们虽说年纪不大,但跟知府老爷却有个同乡的关系在,本身又是刑部衙门的职官,可得巴结好了,说不准年节过了就能往内城里拔一拔。这么想着,邢彪知道这胡同是个两面通的胡同,便叫手下分成两列,分别趟着胡同的两边走,以免出什么纰漏,这差事都做了大半了,最后这关键节点出毛病划不来。
一行人已经趟过了半截胡同,留下两串凌乱的脚印。
“妈妈呀!”邢彪左手那列领头的差役不知道撞了什么邪,突然扑通一声跌坐在雪地里,哆嗦着顺了半天气,这才回过神来道:“头儿,这有一个!”
晦气!邢彪正观察着门头琢磨着是不是到了那林大人的府上的时候,叫他吓了一跳,趟过积雪到了街对面,用脚拨拉开松松的积雪来,眼前黑乎乎的一片,依稀正是个蜷缩的人形。
邢彪注意到这人的服饰并非是那种饿殍的破烂衣衫,心里先就是一凉,完了,这爷们要是真翘辫子,这就要出大事!
“扶起来探探!”
“头,这还有一个!”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邢彪心里正有些发毛的时候,边上一个差役一脚又扫到一个!
“起!”邢彪顾不得自矜身份,抢上前去将人扶起,抬手用嘴咬掉手套,将手指伸到那人犹带着些雪粒的鼻翼下吼道:“那边探探!”
差役们也大抵看得出来点名堂,这会儿听他语气严峻,更是不敢怠慢,七手八脚的忙乱起来,在眼前那位不知死活的年轻人身上忙活起来。
“头儿!还有气!”一个差役来不及收回探鼻息的手,惊喜的回头跟邢彪喊道。
谢天谢地!邢彪抽回手指,眼前这位大爷也有气,那就是没出人命了。虽说这两位爷不是什么小脚色,倒霉是免不了的,但总比两具冰尸要强得多了。
所以此刻他虽是面上冷峻,但方才一直扑通直跳的心脏知道这会儿才安分下来。
“府上有人吗?府上有人吗!”扑通扑通的敲门声好不容易才将这户看上去听破落的院门敲开,开门的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儿,差役们也不管他是聋是哑,抢着把两具具硬挺着的身子抬进屋里。这会儿那老头才反应过来,看清先抬进来的这年轻人的眉目之后,扑通一声瘫倒在地,爬将两步凑了上来嘶哑着叫了一声“少爷”之后,便昏了过去。
“刘小七!快******找郎中!你们,去几个人弄点热汤热水来,甭指着老头儿了,赶紧的!”邢彪吼叫着,一面盘算着这两年轻人要是救不活的话,自己将会有什么下场。
片刻工夫之后,终于弄来了热水,邢彪亲自动手,拧了一块热巾轻轻擦拭着年轻人的人中,许久之后,终于见到年轻人的嘴角动了一下。
“你是谁?这是在哪儿?”尽管声调有些奇怪,但邢彪长年跟五湖四海的外乡人打交道,从嘴形眼神就能判断出来这年轻人在说什么。
“大人,您醒了!”邢彪放下毛巾虚打了个前儿,忍不住高兴的笑了起来回答道:“标下顺天府南城巡检司邢彪,巡街在您府前正见您大人。。。”
他是真的高兴,也许是才脱过一场大难心里还没定下来,也许是担心着另外一位仍没反应的爷们的生死,是以他自顾说着,全然没注意到床上的这位年轻人已经完全没有在听自己说话了,更加无从注意到这年轻人根本已经不是以前他所知道的那位林大人。
如今这位躺着的这位年轻人,呃,其实也不年轻了,看上去总有三十来岁,也正在迷糊之中呢。我是姓林,不过可不是什么大人啊。。。这什么地儿啊,弄得跟拍戏似的。。
他本来的名字叫林山,身边这位看上去很恭敬的人所说的,他一句也听不下去,现在他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前一天的晚上——
多喝了几杯之后,不顾朋友的劝阻,开着车上了南三环。。。有点酒寒,有点晕晕的,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他都无从知道了。他只知道自己似乎遇上了什么奇妙的事情,盛夏炎炎的酷暑夜北京的街头,到如今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一个陌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