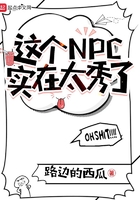头顶嗡嗡作响,飞机的尖叫声从昨天就开始了。我很沮丧。为自己的一次小小忽疏。结果错失了方向。尽管你一再叮嘱:不用的,没这个必要。或者,不要让我看到你。否则全乱了,我会不顾一切地扑上来的。我说好吧。我手拿一张报纸,把自己的脸盖住。这时,手机响了,你说,你在哪里?对面有个人太像你了,你告诉我究竟是不是你?如果是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如果是你,请你转过身。我哭笑道,如果他没举着手机,那就不是我了。事实上,我在西边的虹桥机场。已经知道弄错了。你哈哈大笑起来。说,真它妈天意。我说是的,天意是难违的。那就这样吧。我说怪我,因为这个差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我看了看表:2004,下午三点。你在登机口。
然后我一个人往回走,正午秋天的大太阳照耀着我,上海的太阳有点莫名其妙的灼热,充满了商业和嘲弄。我没有打车,车在高架桥上黑鱼般穿梭过去。我满头汗水,哗哗地湿透了短袖秋衫,我戴着一副大大的墨镜,看上去一定阴险毒辣,像个坏人。几天来你不止一次地说我的眼神像刀片一样锋利,你不敢正视,说这间或的一瞥“太像坏人”。事实上我高度近视,看什么东西不得不使劲把眼睛睁大,再猛地眯起,收拢四散的光芒。我想起昨天在四川路上的天鹅乐园,你忘情地谈论墨西哥:迷人的峡谷和瀑布。水一下子全落下来。整个生命都是如此清凉。那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孤独旅程。在生活的别处,在肉体的内部。
呵,曲折静默的弄堂里,还收藏着多少故人的气息?前面的胡同竟然走不出去。新月在黑洞洞的屋角潜伏,透过高大的水杉树枝,它盯着我们一遍遍地走啊走。并且记下了许多深层次的交谈。感动,碰撞,冲突。每一个波浪都在心尖穿过。你肩上悠荡着一只大大的黑色布包,拉着我的手穿越一条又一条陌生的街巷。你的步子迈得放肆而又均匀,似乎不能叫做散步。你不停地述说成长,从幼儿园到那座由德国人建造的中学校园。白天的人流被我们的瞳孔鱼群般放过,我们站在校园门口久久驻足。望着一个穿白衣的少女在香樟树下石椅上的阅读,你久久驻足,投去如此深情的凝视。我看见不可往返的岁月,时光流失的特性让人恐惧颤抖,不敢深究。天真烂漫,或纯洁无知。五岁那年,春天,矮墙上的紫滕花一朵朵地开着,刺鼻的香气像阳光筛落到地上,美丽的母亲眼窝深陷,她为你最后一次梳头,在深情眸子闭上的刹那,哀伤已经注定。从此,你就是一个心怀忧戚的女孩了,一夜间就长到了十岁的成熟和懂事。你被寄养到舅舅家里,接受严厉正统的管理和约束,那样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谈到这里,你说,不要管你的女儿过严。否则她长大后会像我一样的心理反叛。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多伦路上,这个依然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小街,我仿佛看到身着长衫的鲁迅,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绍兴口音,和他的同道们在“左联”聚会,热血沸腾的柔石和冯铿在搞婚外恋,脸庞黝黑的小个子殷夫,夹一卷裴多菲或契诃夫。你喜欢“莎菲女士”时期的丁玲,赞美有加。还有胡风的夫人梅志,多么贤淑美丽的妇人。唉,过去了,龙华的桃花开着无耻的出卖。如今,在鲁迅笔管里喷涌的血迹和墨迹里,当年的思想者们被雕塑复制在石椅上,成了打瞌睡的老者们争相怀旧的最佳参照。一所旧式建筑里,正在播放默片时代的老电影,卓别林的小胡子上沾着一滴可笑的露水,闪过希特勒激情如“文革”般的面影。从什么时候起,连怀旧也成了商品和麻醉剂了呢,伸出孔已己的手掌收敛发霉的铜板。多乎哉,不多也。
“是的,你应该写点什么,最好写写1920.”
今天上午,我们从鲁迅墓地的广玉兰树下钻出来,坐在“1920”的二楼,激荡心魄的萨克斯从老远就飘过来。空荡荡的客厅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你说这是第三次到这里来了。三次都是和你在一起来的。只是我们没有进去喝过咖啡。三天来我捕捉着你所迷恋的三种事物:上网。制造事端。喝咖啡。你最为迷恋后者。喝完咖啡,老板微笑着来到我们面前,说凡是来1920的顾客,都要赠送一双被红绳子系紧的象牙筷子。
十点钟,我们在街上准时分手,并且谁都不许回头。每人揣着一双颜色相同的筷子。事后得知,你在街上不顾一切地哭,一根手指被牙齿咬住,另一只手拒绝行人或许是好意的帮助。不到三百米的路程走了半个小时。而我却是如此决绝,麻木不仁地收拾残破的心绪,脑海里构思着拐过这条街口,你仍会像昨天一样灿烂地出现,多么好玩呵,让我们和时间捉一个绝望的迷藏。
此刻当一切都静下来,剩下孤独的自己,我才发现男人与女人离别的方式截然不同。男人的离别像是秋天的阵阵寒意,伴随着树叶一片片从枝间掉落,它才会一波波地逶迤来到。更像雨夜里的猫蜷缩在阴冷的壁角,我感到自己再一次被上帝无情抛弃。你说:
“来两杯黑咖啡。不加糖。”
(原载《辽河》杂志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