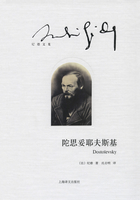红薯的叶子是心形的,茎是匍匐着的,当缠绕的茎几乎要铺满地面时,父母们就开始给红薯翻秧,婆姨们在绿海似的红薯地里劳作着,欢声笑语就在碧绿的叶片上颤动着。
秋意袭人,色彩斑斓的田野上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走在小城的街道上,也能闻到扑鼻而来的烤红薯的甜香了。甜香弥漫到生活的各处,觉得每个日子都有滋有味起来。每年,我家都要储备一些红薯,能一直吃到明年五一前后。可以煮着吃,做红薯粥,炸薯片,等等。有了红薯,觉得每一天都是甜蜜的。
对于红薯的深情,要追溯到30多年前我的童年时代。
小时候,农田还没有包产到户,每年春天,生产队都在南场院那几间废弃的房子里养出很多红薯秧苗来。大人们在火炕上的红薯身上小心翼翼地采下一棵棵嫩绿茁壮的秧苗,然后运到田里。一人在田埂插秧,一人随后浇水,我们小孩子就乐呵呵地拣出还不算太干瘪的红薯,它们虽然丧失了大部分养分,但仍然能寻出块大一点的,一边吃着,品味着甜丝丝的味道,看着暖暖的太阳,觉得春天是那么可爱。
红薯的叶子是心形的,茎是匍匐着的,当缠绕的茎几乎要铺满地面时,父母们就开始给红薯翻秧,婆姨们在绿海似的红薯地里劳作着,欢声笑语就在碧绿的叶片上颤动着。被拨拉下来的秧苗,大家也舍不得让它蔫掉,收工时总有村妇捡些嫩些的叶子,拿回家,午饭的时候作为下面条的佐料。
当天气转凉,小心拨开纠缠着的浓密的叶子,就会看到地面裂开很多口子,那是地下的红薯在迫不及待地想拱出地面。于是,人们欣喜地看到若隐若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红薯,嫩红的皮儿,像婴儿娇嫩的皮肤。到了丰收的季节,开镰了,人们把红薯秧割下来,滚到地边,用头铁锨等小心地刨出一嘟噜一嘟噜的红薯来,胖乎乎的红薯恣意地曝晒在翻出的新土上,那么满足惬意。
当红薯身上的土晒干,村妇就用小笤帚轻轻扫去红薯身上的泥,红薯就露出洁净明媚的样子,村妇的脸就笑成了朵朵花儿。黄昏的时候,生产队长和会计就开始张罗着分红薯了,一堆一堆,人们把分到的红薯小心地用推车运回家,将没蹭破皮儿、完好无损的红薯贮存在地窖里,有伤口的就放在屋子里现吃。小孩子们总是等不及,还没等红薯储存一段时间控甜,就着急让母亲煮着吃了。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还是缺衣少食的年代,当天气转冷,田里的蔬菜断了顿,红薯就成了餐桌上的美味。有时,母亲会在大锅里煮上一锅,当掀开热腾腾的圆木锅盖,母亲总是挑出最软最甜的红薯给孩子们吃。而且,母亲还会在锅边收集红薯的油儿,黏稠的,晶亮亮的,金色或红色,我就用两根干净的小棍儿搅来搅去,能拉出长长的丝来,我们叫它糖稀。用舌尖轻轻舔一下,那甜味就沁入肺腑,仿佛整个童年都是甜的了。
冬天冷,几乎每天晚上母亲都要煮一锅红薯粥,母亲把红薯洗净削皮切块,和玉米楂子一起煮,于是,金灿灿的红薯粥就能让全家身上都暖洋洋的。红薯的甜仿佛是冬日里的阳光,让清贫的岁月也充满着光泽。
那时白面少,餐桌上主要还是玉米饼子窝窝头,因此要吃一碗面条是很奢侈的,由于生产队里种的红薯多,父母也会把分到的红薯切片晒干磨成面,做成面团,可是面太散,无法擀成饼状,母亲就用擦子擦面,在擦子的孔里就断断续续漏下一个个粗粗的短条条,很像老鼠的粪便,村里人戏称用这种面做成的面条叫老鼠粑粑汤。老鼠粑粑汤可没有红薯那么好吃,有点甜,但还夹杂着怪怪的味道,而且颜色黑褐,大家都不太喜欢喝。
晒干的红薯干除了磨成粉做面条外,在过节的时候,母亲还会把红薯片在沙土里爆炒,随着沙土温度的上升,红薯片逐渐变成金黄色,吃起来又甜又脆。当然,现在的人们喜欢把生红薯切片油炸,也很好吃,但我小时候食用油很金贵,人们是绝对舍不得用油炸红薯的。
那时,生产队每年都种很多红薯,除了分给每家每户一部分之外,还集中在一个作坊里加工粉条。我曾经去看过做粉条的,院子里一根根横杆上挂满了粉条,像一条条细细密密的瀑布,做工的叔叔阿姨在其间穿梭,很是壮观。当然,每年,家里也会分到一些红薯粉条,更多的粉条则被运往市场,为生产队挣得一点外快,这样,过年的时候,每家就会多分到一点零用钱了。
后来,包田到户之后,父母舍不得大块田地种红薯,只是在边角地里种点吃。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就只能遥望家乡遥想那份红薯的甜了,但每年一到深秋,一想到沉睡在丰腴土壤里的可爱的红薯,我就禁不住唾津的潜溢了。
科学是一种强大的智慧的力量,它致力于破除禁锢着我的神秘的桎梏……
——高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