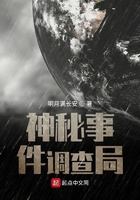突听一女声喝道:“痴能,你干什么。”
朱慈燝感觉身上一轻,痴能从他身上站了起来,朱慈燝心下一松,必竟没到非得出手的地步,他并不打算出手,他要想真的出手,痴能根本无法将他的头按到泥地里。朱慈燝用道袍擦干净脸上的泥水,原来是那女道姑真琴带着女弟子经过这里,想必也是去上观问道。
痴能笑着对真琴道:“真琴师伯祖,你老也来道观问道呀!”
真琴肃着脸道:“我以为我想来啊,还不是带她们过来。你刚才在干什么呢?欺压自己师弟,哼,信不信我告诉你师祖。”
痴能笑道:“师伯祖,你跟我师祖是什么关系,又怎么会难为我这师侄孙呢!”
真琴哼了一声,脸有绯红,知道这师侄孙没少欺负一些痴子辈弟子,正要骂上几句,待看清那给欺负的竟然是那个有废材称号的家伙,便只瞪了痴能一眼,没再说什么,带着一众女弟子走了,没有法子,在武林中,毕竟是以实力说话的地方,没有实力也就只有轮为被欺压的份,如果是官家子弟要学武,虽然不济,家里也会揖赚银两,派中也有所照顾,没人没钱又没才的,怨不得他人,就象朱慈燝这种被称废材的弟子。
痴能给真琴瞪的有些啈啈,便只推了朱慈燝一下,道:“还不快回队。”
朱慈燝心中有点发闷,虽然自己实力爆表,却只能忍着给一个小青年欺负,但又一转念间,他已经学得了内力,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心下也释然了。
朱慈燝一众痴字辈上得道观再也没发生什么事,那凌烟大殿还是一副的仙家气派,只是那上百的破旧蒲团有点俗气。在三清像之前其中一个蒲团上盘腿坐着个老道士,不知道这老道士有多久没打理过自己了,一头凌乱的白色长发几乎将他整个人包裹住,道冠随意的在蓬乱的头发上放着,也不见有系绳,竟平稳之极的放在他头上,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这是没系绳的道冠。长而乱的寿眉与更长更乱的胡须纠集在一起,让人很难看清他的长相,也不知道他年纪有多大了,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他的道袍很干净,就像昨晚才洗好的一样。
新来的弟子在长门弟子的带领下躬身行了一礼,便在破旧蒲团上坐了,之后陆续缓慢进来大殿的才是其他辈份的弟子。
那老道人在弟子还没有坐齐前,已经在开讲了:“道是独一无二的,道本身包含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适匀的状态,万物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万物背阴而向阳,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孤”、“寡”、“不谷”……”朱慈燝虽然身上道袍脏乱於泥,脸上只是草草擦拭,并不在意。对这所谓的问道是一句也听不懂,即然是如此,他也不客气,便也练起了内功。
只是他不知道这问道参禅可不是单那老道人在讲,他还会偶尔点几个人提问,幸好朱慈燝坐的蒲团比较角落,才能专心的练功。
练功也不知过了多久,便收起玄功,想是应该结束了,朱慈燝刚睁开眼皮,一个俏美的大眼睛正睁的大大,双眼皮上睫毛已经快要贴到他的眉毛上了,人脸正凑着贴了上来,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直瞪着朱慈燝,眼瞳左转右转瞅个不停。朱慈燝吓了一跳,忙让自己的头往后退了退,以便看清这双眼睛的主人是谁。一见这人五官绝丽清俗,真是美的让人窒息,朱慈燝竟看的呆了,以为是见到了狐狸精又或是天仙下凡。要知朱慈燝来自未来,网络上各色天然美女、网红、人妖、人造美女也不知见过多少。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人,比之和他订婚的宁宁和司沁诗还要美上三分。一时让朱慈燝呼吸急促,大口大口的呼着气。
那绝美之人看见朱慈燝如此,便不再靠他这么前。朱慈燝这时见这绝美之人站直,心才稍稍安定下来,没有跳的这么利害,呼吸也略微好点了。那是一个年约七八的童子,作俗家打份,一身文仕粉白长袍,头戴四方平定巾,做书童文士打扮,左手使粉红色折扇,他轻摇折扇,轻摇间有淡幽香飘来,只见扇面绘有寒梅胜雪。美人配美扇,当真是无法用任何词语来形容这种美。
那绝美之人见朱慈燝还在发呆,便作揖唤道:“师兄,师兄!”声音轻灵动听之极,但却逞中性。
朱慈燝听的唤声,醒过神来,见这美人做男装打扮,难分雌雄。而且听这人唤自己师兄,朱慈燝自入门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人喊了师兄,要知他废才之资闻名,就连同是痴字辈也喊他师弟,而且见这美人比他高,年纪至少比他大,连忙道:“哦,不敢当,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这绝美之人边笑边摇折扇,从禅会结束发现朱慈燝打座到现在,他已经观察了他整整一柱香的时间,见了朱慈燝还有点二,咘哧笑道:“师兄,你看看殿窗外天色,都几时了,你还在这里参禅。”
朱慈燝从他绝美的脸上离开,望向凌烟大殿窗外,果然天色已经黑了。朱慈燝有点不好意思,摸了摸头,道:“谢谢师姐提醒!”
绝美之人听到朱慈燝唤他师姐,不由的哈哈大笑,笑的没有了美人的形象。绝美之人见朱慈燝还在看自己的脸,控制笑容道:“师兄,师弟我可是男儿身呐!”
朱慈燝一愣:这竟然是一个伪娘,听罢不由的一阵恶心。长的像女人一样美丽的童子,不,比真的女子还要美。
绝美之人文雅之时,竟现出娇艳无比的面容。让朱慈燝感觉到格外的别扭,长的比女人还要女人,比女人还要漂亮,可这竟然是个男人,所以朱慈燝收起了拘谨。不过一看到他那张娇艳美到不可方物的脸,他就不由自主的从心里直冒寒气,直打牙颤,生怕自己会有同性恋倾向,幸好,他是正常的。
绝美之人不知朱慈燝在想什么,他美丽的脸上似乎透露出一些兴奋,指着朱慈燝开襟的道袍道:“师兄,你里面穿的是什么!”
朱慈燝吓了一跳,以为他要非礼自己,荒忙用手捂住开襟的道袍。
绝美之人看他这个样子,一怔间,已经知道他想歪了,想他自负美貌,不论男女都和他关系极好,巴不得和他来往亲近。从不会像朱慈燝这样畏畏缩缩,生怕和自己靠的太近。便觉得这小子有意思,很对他的胃口。但为什么对他的胃口,他又说不上来。
他捂嘴笑道:“师兄,我指的是你道袍下的那件顺龙战衣!呶!黑红色的那件,内里的?”掩笑间,姿态尤美无方,虽还是个童子大小,但已经不知胜过了多少美女、名角,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朱慈燝反应过来,叉开道袍低头一看,见到自己贴肉而穿的黑中泛红那件陨石衣服。这件衣服除了偶尔睡觉、如厕、还有昨晚下山没穿外,其余时间都是贴身而穿,在上的道观来之后,就给他随便洗了下道袍,没注意盘坐时道袍开襟而露出来了。便道:“原来你说的是这件,这就是一件比较重的衣服而已!”
对面那绝美之人此刻看上去,下巴都要掉了下来似的,但依然美及,奇道:“就是一件比较重的衣服而已,就是一件比较重的衣服而已!”
朱慈燝见他神情怪怪的,摇了摇头,转身就往大殿木门走去,不料还没走几步,那人居然也跟了上来,堆出满脸笑容,一脸谄媚道:“这位师弟,哦,不,师兄,你?”看到自己比朱慈燝高,就改口师弟,但一想,要巴结他,又改了口,叫回了师兄。有多假就有多假。
对于这样貌比女子还像女子,声音虽是温柔动听得很,但朱慈燝一想起他是男儿身,就觉得一阵寒气袭来,说不出的难受,更是不去理他,反而加快了速度。
绝美之人见叫不住他,顿了一下,显然他从未有这样低声下气过,连忙和他一起步行,满脸堆笑,对朱慈燝道:“呵呵,师兄可真英气不凡,哦,不是,是平易近人,啊!这样吧,我先自我介绍一般,鄙姓宋,草字少杰,道号宏杰,是破军峰的弟子。不知道师兄你的名字是?”
朱慈燝听得他是宏字辈,竟然比自己高了一辈,连忙停了下来,在派中不尊长辈可是大不敬之罪,便道:“原来是师叔!我道号痴惊,乃大岩峰弟子!”
绝美之人宋少杰看他停下,便也停了下来,自带自来熟的搂住朱慈燝肩头,道:“不用叫我师叔,你我一见如故,不如我们平辈论较,我叫你痴惊,你叫我少杰,名字吗!都是用来叫的!”
朱慈燝见他和气,所谓抻手不打笑脸人,也不推开他,但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不自觉得头尽量离他远点。宋少杰娇美道:“人家的衣服如何?那可是辛苦用好几种花熏过的,还不错吧?”
朱慈燝完全是楞住了,只觉得冷汗立时便顺着自己的脖颈流了下来,直接这人不正常,回去以后一定要给他搂过的肩头消毒,以防有那种病。
宋少杰见拉关系拉的差不多了,放开朱慈燝肩头,便道:“是我一时疏忽,忘了自我介绍了,才让痴惊兄如此以为我是不安好心,对了!你这衣服就真的只是重吗!那可是顺龙战衣?”
“顺龙战衣?”朱慈燝疑道。
宋少杰郑重点点头:“顺龙战衣,据说柔软贴肤,可伸可缩,遇人而异,沉重已及,乃天外陨铁打造,是本派不可多得的宝贝!”
朱慈燝点点头,没想到这件衣服还挺出名的,对自己师父宏观更感感激。
宋少杰见他点头,显摆道:“不是兄弟夸口,我自幼过目不忘,览群书无数,博闻广记那可是出了名的!不信惊兄你考考。”称畏又变成了惊兄。
朱慈燝虽见宋少杰长的娘,但不像其他人那样心高气傲,便认了他这个兄弟,便道:“没想到兄弟竟然这么平易近人,我就认了你这个兄弟了,那我就考考你,就比如奇珍异兽,看你知道多少!”
宋少杰听得他用平易近人四个字来形容自己,不由的脸红,嗯了一声,道:“惊兄,你尽管道来,从我丹霞派的镇派神鹰,再到天阀军的紫雷神虎,那一个奇珍异兽我是不知道的!”朱慈燝本是要拿澳洲的袋鼠和南极的企鹅来打击下他,没想到他尽然知道自己身边的老虎,一时给惊呆了:“你竟然知道紫雷!”
宋少杰得意道:“那是,想我如此天才,那个不晓,那个不知。”见周围没人,又道:“天阀军的紫雷神兽,全身通体紫蓝相间,相传乃天上神虎,随天阀将军下得凡间来,见了人间不平事,以是化做天上落雷,击金虏,除海患,镇海域,呼风唤雨。”
朱慈燝听他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便道:“你见过?”
宋少杰脸红道:“未曾得见,不过我见过另一神兽,我派中的镇派神鹰!”
朱慈燝奇道:“镇派神鹰!”
宋少杰点头道:“对,我派的镇派神鹰,相传当年随我开派祖师爷一同行走江湖,就连祖师爷的武艺都是它所授!此时已经不知活了多少时日!”
朱慈燝根本不信:“去你的,那有会武功的鸟,我还说我见过只会游泳不会飞的鸟呢!”
宋少杰听他说脏话,脸有慎怒,但即闪而逝,道:“靠啊!镇派神鹰就是不会飞,听说就只会游泳和走路,原来你也见过!”
朱慈燝摇摇头:“我没见过什么镇派神鹰,我说的是另一种鸟!”当下说了下南极的企鹅,形容了下样子,生活习惯,见他听的乐,又说了鸵鸟,形容的很祥尽,这时看的天色已经很晚,便想去吃饭,稍微打断道:“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先去吃过饭,改日有空,再来和杰兄你聊!”。
宋少杰听的精精有味的,那里舍得和他分开,便道:“惊兄,不如这样,你我一见如顾,不如我们义结金兰吧!”
朱慈燝有点纳纳,心想和比自己大一辈的人称兄道弟,可不好吧,但宋少杰根本不依,非和他在三清像前,拜了三拜,道了姓名,原来宋少杰和朱慈燝同年,只是宋少杰长的高得多了,按月份还比朱慈燝小。朱慈燝见拜得差不多了,也应该是去吃饭了,没想到宋少杰说道:“慢来,还有一拜!”即认两人相互对拜,相击了三掌,朱慈燝不知道古人义结金兰的礼节,便也没什么奇怪的。
当下便和这个新得来的兄弟去了山上道观的用膳厅,边说边聊天,见用膳厅还有几人,知道还有饭吃。吃饭时宋少杰问道:“燝兄,你的道袍怎的这么脏,脸上还有沾了点泥巴!”
朱慈燝当下便说了日间受痴能欺负的事,还没说完,那知宋少杰竟拍桌而起,骂道:“连我的男人也敢欺负,当真不要命了吗?”
朱慈燝立时冷汗直留,看了一旁桌上吃饭同是大岩山的宏字辈弟子目光,连忙纠正宋少杰道:“杰弟,你说错了,我是你兄弟!不是男人!呸,不是你的男人!”
宋少杰道:“一样!”
朱慈燝道:“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