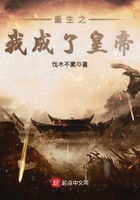米脂县的田野正处在一片焦渴的枯黄色中。
刚刚收割过了小麦,地里空虚了许多,许多的村头地尾还在吱吱扭扭地滚着场脱着麦粒,荡起一阵阵愉快的灰尘,许多的农人已经星星点点地“撒”在地里播着谷种,牲畜劳累地吼叫着,鞭子嘹亮地响应。桑林里桑叶已经采摘得差不多,青白的桑椹却开始发红发紫,露出诱惑的一面,在这繁忙喧嚣的世界里,几个迟到的布谷鸟轻轻地遥相呼应。
李继迁寨子的外面,李守忠正驱赶着一头老掉了牙的老黄牛,“得!得!”
老牛浑身上下都是光滑的纯粹的黄色,好象一团锦,在努力地带动小滚盘旋的时候,一群牛蠓疯狂地追逐。
“得!得!”
老牛突然停滞不前,因为它太老了,已经干不动了。
呼嗵,老牛两只前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李守忠大声地吆喝了几声,见牛不动,赶紧跑来,不料,那老牛居然彻底倾倒,抽搐了几下,一命呜呼了。
李守忠观察了一会儿,见老牛确实已死,心疼得顿首捶胸,嚎啕大哭。“唉呀,我的老天爷呀,天塌了!”
李王氏听见别人叫她,赶紧跑来,一看也急得没有了主张,在边上偷偷的抹泪/
亮大爷听说了这事,也出来安慰;“咱再想办法吧!”
李守忠坐到地上:“老天爷不叫我活了,先是一个好端端的干儿子被黑心烂肚肠的官府们逮了去,现在还生死不知,现在我的宝贝老牛王又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一些小孩子们也来看热闹,他们没有多少同情心,只是高高兴兴地喊:“快看,黄来僧他家的牛死了!他得正哭哩,哭得鼻涕长啊长。”
牛是农家的宝,失去了宝贝的农人象丢了魂,哭得如丧考妣。
这时,一个清亮的声音突然从人群里挤出来说:“死就死了,有什么大不了?”
李守忠一愣:“嗯?”
“死了大黄牛,再来头黑花牛!不是?”
“廉树!是你吗?”
“是我!爹!”
“可是你?”李守忠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个失踪了好多天叫自己牵肠挂肚的小子现在穿戴一新神气活现象个富家公子哥儿啦!
“喂,是廉树!他回来了!”
“哪个?”
“忘记啦?那个讲故事好好的!”
“呵!这****的好小子!我可想死他啦!”
人们再也不关心老李先生的那头老牛,一起把视力转向了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那个神秘小男人。
亮大爷:“喂,小子!你这些天在哪里享福气?嗯?为啥早不回来?”
严树把手中的扇子一摇:“亮大爷,我想死你们啦!”
“树儿!”
严树赶紧回过头来,一把抱住李王氏:“娘!娘!”
“我的儿!真是你吗?”
“是呀,我是廉树,是你的儿子!”严树见老人家老泪纵横,再也开玩笑不起,慌忙擦她眼角汹涌澎湃的泪水。
李王氏上下打量着严树,喜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李守忠拥挤过来:“孩子,回来就好!那些狗县官狗捕快们没有很难为你吧?”
“爹,我好得很!您放心,黄牛死了,您别难受了,您看,那边是什么?”
众人搭眼望去,只见不远处的大柳树上拴着有两头黑花大牛矫健地甩着尾巴驱赶着蚊蝇,一面从容地咀嚼着反刍的草料。
大家的眼睛都是一亮:“呵,谁家的牛,好俊!”
严树把头一点,笑一笑:“爹,咱家的,从今天起,它们就是咱家的了!”
“是你买的?”李守忠眨巴着眼睛,根本就不相信。
“是啊,他从哪里弄的钱儿?”
这时,一个人骑着马得意洋洋地过来:“唉呀,你们给我让开道儿!”
大家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姬家堡子的总教头洪峰!
洪峰的后面,还跟着几个人,有的是家丁模样,有的是公子模样。
百姓们最害怕的就是见官见富的,立即战战兢兢地看着。
亮大爷到底有见识:“喂,那不是三管家么?”
“嘿嘿,是我呀。”
“你们来干什么?现在就收租子啊?”
“不收,”
“那你们?”
“呵,今年这李家所有欠交的租子全部都免了!”
“啊?”
李继迁寨子有一半的百姓都欠着姬家的租子啊。那数目能小了去?
三管家把马鞭一指:“你们大家都要感谢廉公子!”
“廉公子?”
“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廉树廉公子!以后呀,他就是咱姬老爷子的三女婿了!哈哈,这是天大的喜事!老爷一高兴,就免了你们以前所积欠的租子啦!”
“这是真的吗?”李王氏拉住严树的胳膊。
“是真的,娘!”
李王氏怀疑地观察着严树,不敢再吭声了。
“娘!”
“我,我,我,我不是您的娘,唉,廉公子!”
村人都被突然大富大贵的严树吓坏了,赶紧往边上躲避!
严树命人把两头黑花大健牛牵了来,交到李守忠的手中,李守忠迷迷瞪瞪地抓着牛缰绳,不由得笑憨了:“天啊,多壮的牛!”
严树拉着李王氏回家去。众人跟着看了再看,议论纷纷地,又是羡慕又是怀疑,都猜测着严树的真实身份。
亮大爷颤微微地说:“守忠啊,你这个孩子儿果然不同寻常啊,你下半辈子情享福气了!”
洪峰和管家等人商量了一下,就在村前村后游走,然后往别的地方去了,只剩下了一个白衣公子不远不近地跟着严树。
回了家,严树赶紧招手:“喂,青弟,你来呀!”
白衣公子昂然而入,东瞅瞅西往往,好奇得很。“喂,廉哥哥,你在这里呆了多久?”
“十几天呀!”
严树和两位老人拉家常,两位老人终于从大悲大喜中反应过来,高兴得直叹息。
说了一会儿话,严树就要走,在身手摸索着。这时,那白衣公子一笑,从肩膀上摘下一个小布兜儿:“两位老人家,多谢你们救济过廉树,这是三十两银子!”
“三十两银子?”两个人匆忙打开布兜儿,惊喜地抓着银子,高兴得象是在做梦。
“天啊,我们有三十两银子啦!”
“哼,才那几个小钱儿就开眼了!”白衣公子轻轻地讥笑道。
“三十两还少?!!!喂,公子,您是谁家的?”
白衣公子抿嘴微笑。
严树道:“喂,青弟,他们是我的爹娘,难道就不是你的爹娘了吗?”
“是啊!”白衣公子无奈,只好轻轻一作势,“爹娘两位好!”
李王氏搀起白衣公子。开始详细地询问严树情况。
这时,在地里忙碌的黄来僧回来了。
“兄弟!”
“哥!”
两个人抓住各自的肩膀,激动得严树鼻子一酸,要流泪了。
说了好一阵话,严树要走的时候,说:“哥,你能不能跟着我一起到外面闯闯?因为,我准备到外边做生意去。”
黄来僧看看爹娘,他爹娘都说:“行!打仗还是亲兄弟!有了你的帮衬,廉树一定能更发达!”
“好!那我黄来僧,我李鸿基,李自成,就跟着兄弟你往外闯了!”
“什么?”严树的身体给定住了似的。
“喂,哥?你怎么了?”白衣公子拉了拉严树的衣裳。
严树迷瞪了半天,又追问:“哥,你不是黄来僧?怎么会是李自成?”
“黄来僧是我的外号!我的大名是鸿基,小名是自成啊!”
“李自成?大明朝末年西北米脂县的李自成?”
“是啊。”
“天那,我真是傻瓜!大傻瓜!”严树稍一思考,就兴奋得疯狂了!
这时,一大群人都跑过来,在家门口跪着,来感谢严树帮助他们把积欠的租子都免了。
“廉兄弟,你真是大好人啊!”
“是啊是啊!”
“喂,廉树!”
一个怪怪的声音传了来,竟然是三癞子。
“树公子,真对不住!你叔是个傻瓜!是个混蛋!真不该多嘴啊。真不该那个啊。”
“算了!”严树把他搀起来。
“天那,你真是那普度众生的菩萨啊。以后呀,我三癞子一定给你摆个牌位,天天供着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