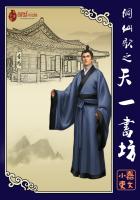严树答应一声,就讲起了自己的经历,什么官宦之家呀,家道中落呀,遭遇土匪呀,遭遇水灾呀。流落街头呀,点点滴滴,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娓娓动听地道来。
严树讲得非常投入,感情酝酿得也很到位,可谓有声有色,恰如其分。
不说管家开始抹眼泪,二公子神色黯然,就是严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
呜!
“哦,怪不得你年龄不大心计甚深,也知书达礼,折节自重,原来也是官宦之家,斯文种子!唉,命运造化弄人呀,好了,你也别太伤心了!廉树,本公子今天赐你座位,我们不再拘泥于什么主仆名份,就以平常的兄弟情份见礼,你觉得怎么样?”
姬公子连连感叹着。
“这个?小弟儧越了。”严树发现自己今天的第一步棋已经完全成功了。
意料之中!
要想能赢得上位者的重视和赏识,一要实干,二要巧言令色,嘿嘿,后者或许功效更大些吧?而要赢得他们的支持,就只能晓之以悲情了。
一般说来,富人们的同情心的熔化点儿并不低,但是,和他们同一层次的遭遇能立即突破瓶颈。
二公子热情洋溢地挽住严树的衣袖:“本公子以下人来对待你,也确实有些委屈了!还望兄弟见谅一二。”
“多谢公子!”严树马上就“照顾”了公子的情绪----答应了。
前生商场金场,练就了多少阴谋诡计,花花肠子?
这一次轻松容易,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凑效了,嘿嘿,没事偷着乐吧!
“请喝茶!”更客气了。
“不敢。”
嘴上这么说,手上却毫不客气地接了,一番大大方方地牛饮,爽!
严树开始实施计划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公子,您真是菩萨心肠啊,小弟弟感激不尽!所以,小弟特来献上一策,以尽报效之意!”
“哦?贤弟果然高人,有何见教,但言无妨!”
“今天小人非为讨茶而来,亦非为倾诉心中苦闷而来。实在是有一件关乎姬府上下百十号人的现在和将来,穷绌或者通达甚至生死存亡之命运的大事情,故而不敢藏拙。”
吊胃口。而且越是吊得高效果越是好,就象钓鱼的话不要用蚯蚓,而要用大象!
“如此严重?”公子震撼到不安起来。
“若有一言浮夸,廉树但求自裁于公子阶下。”
“哦?!!!哈哈,廉树,你也太言重了,你我寻常百姓之家,怎么做军中豪迈之举?那好,你有何见教啊?”二公子站起来,亲切地拍拍严树的肩膀。
“不敢,公子,我想请问,那天和小弟一起押解来堡中的几个流民现在关押何处?”
“流民?”士节没有印象。
“还在水牢里。”二管家小声说。
“哦,对,还关着!”
“公子!这几天泡下来,他们还能好得了吗?以后必将留下残疾!请公子开恩,马上予以释放!”
“不惩治他们一下,给点儿颜色瞧瞧,他们能老老实实地在我庄中呆下来做活儿吗?”
“公子,可惜呀,太可惜了!”
“什么意思?!”
“公子,我要走了!”严树摇晃着脑袋,痛心疾首:“一样,简直跟我们家一模一样!”
“什么一样?”
“失败之理,破落之道。”
“嗳?廉树,你说清楚啊。”
“公子,我说了也白说啊。”抬脚做出走的姿势,脸上是不可救药的鄙视。
嘿嘿,越是聪明能干的人越是怕这一招啊。
“来人,给我抓住他!”
应着话音,马上就有二管家领着两个贴身的强壮家丁推门冲进来,把严树抓住了。
“随便公子惩处!”严树把架子摆得十足。
二公子转到了严树跟前,喝令三人松开严树的胳膊,又把他按回椅子里。
“呸!你小子!什么意思?怎么说了也白说啊?”
“公子,你大错特错了!根本就无法挽救,所以,我只能伤心地看着这一切的变迁了!”严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姬士节被严树弄得愈发稀奇,急不可耐。“说呀!”
严树缓和了情绪,说道:“我听说姬二公子是个开明通达之士,懂得经典,深明世事,所以,在县尊可怜我要放我回家时,我主动要来姬家堡,目的就是要瞻仰一下姬二公子和姬大员外的风采,学习些为人处世之道,不料,大失所望!”
“嗯?”二公子平静地点头:“你说。”
二管家在一边担心地盯着严树,生怕他有什么过分的言语出来,因为严树毕竟是他带来的,要是惹了祸,他当然也免不了干系。
“知道孟尝君否?”
“然也!”
“知道他的门客冯爰以薛地赋税和债务买民心地故事否?”
“然也,哦,廉兄弟莫不是责怪我对下人手段强暴?”
“是啊。”
“这有何碍?历来家主都有权利处置家奴啊。这么多人没有霹雳手段怎么镇压得住?而且,我比起父亲来说,已经是柔和绥靖之术啦!”二公子不以为然地说。
严树在李继迁寨子经常询问民风民情,对当时的形势相当清楚了,所以,胸有成竹:“公子,听说过没有?时位之移人!”
“嗯。”
“一个人的时机变了,地位高低贵贱的情况变了,他的性格,习惯,作风也必然随之而变!一国之情亦然!我大明早一些年的话还可以,可是,现在是大厦将倾,大乱将至的衰乱之世啊。公子,在乱机将至的时候,我们的修身,齐家之术还能株守成规吗?”
“危言耸听耳!国家形势虽说有所不靖,却也新皇新气象,民富兵强,我等少年人不能如此偏激!”二公子摇了摇精美的竹扇子,似有所动,却又竭力装作漫不经心。
“一家一国,道理相通,刘璋治蜀以宽而庸暗,诸葛亮治蜀以猛严而平静,关键是时世不同,现在我大明实行仁和之法的道理难道还真的需要我讲吗?”
二管家急忙上前扯住严树的胳膊:“小子,你是发疯了么?你在我家秀才公面前卖弄什么?”
二公子把手一挥:“好,士节愚钝,愿闻其详!”
严树轻哼一声:“我流浪多时,深知农民之苦,现租种之田,上等田地着,田主得七至八成,农人仅得二三成,下等田地者稍好一些,来年种子农具投入又需若干,于官府徭役租税又需若干,农人所能留余实在有限,而农人养家糊口,礼尚往来之需,又不在少数。所以,农人拼死劳作,不能得温饱,所以,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流浪,成为流民大潮!据我所知,仅我延绥(注:当时和陕西不是一省)一省,总人口不足二三百万,就有流民三四十万众!放眼全国,情景更将严重!现下各地大小贼寇蜂拥而起,渐渐有坐大之势,与秦末陈胜吴广之事,汉桓黄巾之起,元顺至正红巾之变相若!或许三五年之后,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必将引爆浩大民变!还有,我大明边境一直不靖,女真铁骑已经连夺我辽东辽西数十城池,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养成大患,天启新君年少,宫廷之内屡有动荡,我国我家正是内外交困之时,若现在还不振作,到那时节,则悔之晚矣!”
二公子已经变色心动,但是又颇不服气地说:“农人之苦固然,可是,马上就酿成巨变还不至于,再说,这些事情该朝庭大员们治理,你在我面前大张伐挞岂不是明珠暗投了么?”
“肉食者鄙,公子想必知道曹刿之言!”
“那你要我一小小布衣,昏昏荧虫能做什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公子贵为一堡之少主,又素习经典儒训圣喻,怎么能置身事外,坐亡败之时,犹唱*之花?”
“哦,说得有些道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嗯?这句话说得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这句话真好!廉树,想不到你有如此妙语佳句!”姬士节连连夸奖着,乐得屁颠颠,一下子就忘了主题。
严树心中暗笑,这句话乃是后来大师黄宗曦所说,这里先借用了,侵权之处还望黄老先生原谅一二。
“公子,我一个下人,也知道这些国家治乱大事,又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是国家混淆撼摇,这姬家堡诺大的产业岂能完善?这满门的家口岂能安存?此事大矣,公子以为是耶?非耶?况且,今日之事,又不要公子从戎疆场,舍却身家性命,移泰山而填北海,只是举手之劳耳!”
二公子迟疑片刻,慨然说道:“廉树兄弟,你的话很有些道理!想我姬士节,好歹也是读书种子,天朝秀才,焉能不知这些大道?你说,我该怎么做才不辜负圣贤之教?”
严树嘿嘿一笑:“那还不简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累善德!目下之急事,一,马上放了那几个流民,愿留则留,愿走则送,二,核定所属田地租金,能降则降,三,定期施放斋饭,赈救贫乏。四,力戒奢侈,清静节约。”
“好,那几人就先放了,不过,其他事项,还是等禀报了我爹才能定夺。”
“那姬老爷呢?”
“这个,家父,有恙在身,一直在内宅修养,已经多年没有出来主事了。”说着,姬士节就简单地讲述了他父亲性格失常,残暴猜忌的事情。
“原因在哪里?”
“不知道!数年来已经延请医生无数,花费银子无数,就是不能治疗痊愈。反而愈加严重!”姬士节苦恼地说。
严树叫他好好回忆一下,还连连举例子启发他。
姬士节涨红了脸犹豫着不说。
严树见好就收,暂时搁置之,提起另外一件事情:“公子,那天夜里我等巡逻到后院与前厅交接之处,恰好也遇见公子,听楼上有女子悲惨呼救之声,却是为何?”
姬士节的脸变了一变,阴暗着又不吭。
二管家尴尬地着着急,却没有办法,他见公子这样器重严树,和他非常投缘,再也不敢轻易喝斥。见场面紧张,赶紧上去岔开话题:“公子,您,该用饭了!”
姬士节叫上了饭菜,然后挥退众人,犹豫再三,终于说:“廉树兄弟!你见识高远,器量非凡,绝对不是池中之物!富贵之通达,将来必然!现在我以兄弟相称,不会玷污你之耳目吧?”
严树心里微微一乐,“公子太抬爱了!咱吃饭倒不着急,小弟十分愿意听闻姬大员外的病历,因为,小弟家里也略通歧黄之术,尤其是擅长于情志方面!或许对令尊大人的治疗有帮助!”
姬士节早已对严树刮目相看,这时听了,绝对相信,又心里苦楚,闷得难受,就开始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姬员外患病的原因和症状。
十年前,姬家员外为人还十分诚恳,随和,只是年轻风liu,喜好颜色,那时,他已娶有五房夫人,老大即是大公子姬士保和大小姐的母亲,二房没有生育,三房是姬士节的母亲,四房是二小姐和三小姐的母亲,老五最小,长得也最妖艳,倍受姬员外的呵护宠爱,不料,一天夜里,她居然和一个家丁裹了金银细软私奔了!姬员外知道事情后气得吐血,情绪急剧恶化,又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抑郁于中,情志发生很大变化,为人生冷淡漠,又脾气怪异,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用极为严酷的手段惩罚家人,想尽办法折磨几个夫人,后来还一再新娶了五房夫人,几个夫人都被他折磨不成样子,又被驱除了家门。他自己也一再轻生,数次绝食,数次投井服毒,几回都差点儿死掉。
“公子,那天夜里的哭声是?”
“恐怕是九姨又被罚跪了挨打吧?”
“打?”
“七姨就是被父亲失手打残的!”
“打伤人就没有被官府纠治?”
“我大姐姐和叶向高叶大人家的公子结了亲,官府都对我家特别照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况只是打伤?也就算了!”
“他这样凶残,难道你就不恨你的父亲?”
“父为子纲,做子孙怎能乱了人伦?再说我父亲他发病时凶狠,可清醒时总是后悔莫及!我们对他心疼还来不及,哪里又能恨得起?说来,连我的第一房夫人也是因为被他家法惩治太重跳了井寻死的!”说着,姬士节的泪水潸然滴落。
严树气得跳了起来,把桌子一拍:“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家伙,留着他还能有什么用处?为什么不干掉他?”
姬士节吃惊地看着严树,好象不认识他。
严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和失态,又想到自己的前生手上也沾染有人命鲜血的,追究起来也不是干净人,马上就惭愧起来:“对不起,二公子。”
“少年性情,我岂能不知?”姬士节苦苦一笑。
“我几天来见你一直闷闷不乐,原来有这等心事,好了,这事情包在我的身上了!”
“什么?你包什么?”
“包令尊大人的病呀!”
“你会治病?你知道这病?”
“嗯,令尊的病以我看来,是狂躁性抑郁症,是精神病的一种!小弟的祖父恰好精通这一类病症,所以,小弟依渊源之家学斗胆放言,一个月之内,让令尊大人的病根本好转!”
“精神病?”
“嗯,是精神异常。”
姬士节腾地就站起来,兴奋得两眼炯炯放光:“若是廉弟真的能救治了父亲大人的病症,小弟一家感恩戴德,报答不尽!”说完,对着严树就是深深一揖。
“哪里。我不求回报!只要公子能对家人和农人们好一点儿就成!”
“想不到你自身艰难,还能有如此心肠!”
“见笑。”
“可是,要是你真能治好我爹的病,我们家必将履行诺言。”
“诺言?”
“是,我母亲在佛祖神位前许诺说,谁要是能治好了他的病,他就将我三妹妹许配给他!这一点儿,我家人都已经同意,连我三妹妹也没有怨言。另外,父亲也说,姬家的家产可以给他一半!”
严树看着士节诚挚的面容,忽然觉得面前打开了一扇金光闪闪的大门!
漂亮妹妹?巨额财富?怎么一直往我的眼前跳?
“我倒不在乎什么钱财之类俗物,姬大哥,你要知道,精神疾病确实很难治疗!我也不敢保证就行,只能试试吧。怎么,现在就让我见一见令尊大人?”
今天可谓收获不小!圆满成功!三言两语就搞定了姬二公子,将来在姬家还用怕什么?哈哈。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抑郁症患者,正是自己拿手的好节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