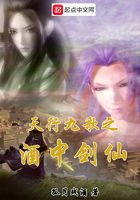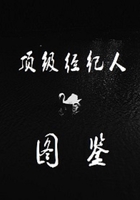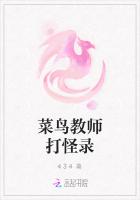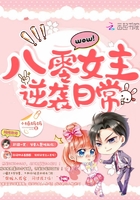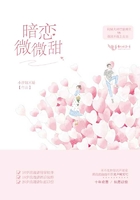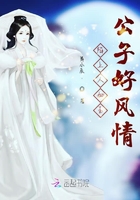范敬宜
仆尝谓友人曰:“予心中之长者可谓多矣,有可尊者,有可敬者,有可亲者,有可慕者,若四者兼而有之,则南阳袁公耳。”
何谓可尊?德高望重,而不居功自矜也;何谓可敬?清正廉明,而不孤芳自赏也;何谓可亲?谦冲平易,而不随俗自薄也;何谓可慕?博闻儒雅,而不恃才自炫也。一言之,曰自持,自牧,自重,自律。人生至此,庶几无憾焉。
予生也晚,于袁公心仪久矣,然长处江湖之远,缘悭一面。迨逾天命之年,奉调入京,始得识荆,乃知谋猷筹画之国士,实为恂恂笃行之学者,心益重之。自此常得忝列末座,坐沐春风。初闻其纵论经济,于邦国发展大计了然于胸,如数家珍,为之叹服。继随公出访东瀛,见其折冲樽俎,挥洒自如,有周公之风,为之心折。及读其诗文,气度雍容,深情远想,非寻常笔墨,为之击节。始信古人所谓君子立德立言,洵非虚语也。
公平生无他好,唯潜心于经济研究。著述等身,皆利国济民之策。政务之馀,乐与新闻记者交。报刊不问大小,有求无不慨允,畅谈竟日而无倦色,故记者咸以良师益友事之。是以访谈之篇连年不绝,或论国是,或论经济,或论人生,或论艺事,闳中肆外,寓庄于谐,非学养深厚不能臻此。丙子之年,为公八十初度,友人坚请将其历年访谈八十篇结集,曰《袁宝华访谈文集》。即将付梓,公嘱仆为序。窃思无含英咀华之笔,岂敢为名山之作赞一辞?然转念公以忘年之交相许,不厌浅陋,委以重托,又不敢有负雅望。遂商诸同好,录其所述,竭尽鄙诚,恭疏短引。览者倘能藉知公之道德文章于万一,则予愿足矣。
1998年11月
附 和袁宝华同志《八十述怀》
范敬宜
1996年10月22日
揽镜不嗟白发新,
人生八十犹青春。
骅骝伏枥念疆场,
松柏经霜存赤心。
越陌度阡身不倦,
兴邦济世情弥深。
夜闻鼙鼓思良将,
未敢含饴弄爱孙。
致袁宝华(摘录)
邹屏
2001年8月20日
近五年来,因为打电脑,用手写字渐渐别扭了,就请原谅我:不手写信吧!你的文集第三、四卷,昨日收到,放下手中活,连续看了一晚加半天,顿生感想。文如其人。读你的文集,我想起来了《******选集》。你的为人,也近乎周总理,总的是一个“正”字。
你一身正气,一生勤恳,廉洁自律,不走极端,不吹牛,不拍马,有正道的人情味。
你一生是正面人物,背叛本阶级,坚定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服务一生,在今日,仍然依靠工人阶级,不忘工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你一生是正步走路,紧跟党的领导,循规蹈矩,不偏不倚;你既反对老教条主义(王明型),又反对新教条主义(抄袭西方、照搬外国);既反“左”,又反右(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很不容易呀,过去******只反右,不反“左”,因为没有比他们更“左”的了;现在有个理论家写了一本书,他们只大力反“左”(把******也划入“老左”),而不反右,可能没有比他们更右的了。你有篇文章肯定了邓老的天安门平乱和批判《****》,这是正确的不偏不倚呀!
你既搞改革开放,思想上又继承正统,你著作中引用了不少毛主席的话,你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首创者归于毛主席,这就对了。******的思想基础也是******思想,不能只信奉邓而搁起毛,也不能只说毛的老话(毛主席大部分的话,至今仍是一针见血),而不执行邓的新话。******是一个难得的“**********”后的接班人,他是一致拥护的党的领袖。他眼光敏锐,既反“左”,又反右。1989年是他防止了苏欧式的剧变;他提倡劳动致富,强调共同富裕;他再三警告,防止和平演变。他贡献巨大。——话扯远了。你正确地贯彻了邓的路线,不搞形而上学,不偏不倚,不像有的人各取所需,把完整的******理论片面化。
你一生是正人君子,守了晚节,不像有些人做官就要发财(那些一心搞私有化的人,像叶利钦一样,就想自己发大财)。你官至中央委员,但你仍遵守“老三篇”中说的:我们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你是“一二·九”干部的佼佼者。
有以上几个方面的“正”字,最终你会成“正果”。
你的文集对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很有功,现在已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了。你的学风、党风和文风都是******思想培育出来的正统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你文章简短、精悍,事多,多说,事少,少说,不像极左和极右派他们写的文章(讲话)都是成套格式:第一部分,歌颂党中央和上级领导,罗列一些指示和金口玉言;第二部分,他所提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某个伟人或某些大人物说过,某先进国家如何如何;第三部分,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努力下又如何……文章又臭又长,他一篇比你五篇还长。他再长,也没新意,而且,还看不到、摸不着其中的活思想、真观点。文章也仅仅当做一种商品,它的内涵是钱、官、地位。
致袁宝华
阎东超
宝华同志:
二月六日手书奉悉,很高兴!
《八十述怀》我未收到,是一大憾事。值得欣喜的是李蕤(赵悔深,安义兄的好友)及时函告,他信上说:“我读后,感到十分亲切,寥寥八句,把一生的经历、抱负、理想、操守,都抒发出来了。而且从诗的艺术技巧来讲,既凝练而又生动,思想深刻而又含蓄,都是难得的。我反复吟读,爱不释手。因此,将此诗剪报寄上,供欣赏……”
联想,您1984年、1988年的三首诗词,个别知交索读转抄;经安义、时萍两兄复印几份,后来我将珍藏的复印件纳入《乡贤赞》,引起重视。《八十述怀》境界更高,行家李蕤的评论诚恳恰当。可惜安义、时萍两兄不能共同吟诵欣赏了!
李蕤信最后说:“安义兄生前时常和我谈宝华的情况,我对宝华非常敬佩。如你写信为他祝寿,盼代为致意。”
《八十述怀》,我和我的老伴金明珍及女儿都很喜爱。拟请您给我书写一帧小条幅,我将交荣宝斋精裱,作为纪念,如何?读剪报远无吟诵手迹的亲切感人。
谨祝时祺!
东超上
1997年3月1日
附 黄鹤旧雨——记袁宝华同志事
阎东超
1988年2月
1988年元月宝华同志应武汉市委邀请来汉参加一个座谈会,他抽出一天时间(1月21日),到汉阳看望魏时萍、时灵君夫妇,到武昌看望李新章同志,到汉口看望我。他比往年开朗,更加朴实、谦逊,一身军大衣,保持学人气。时年七十二,健壮如六十岁。畅谈欣快,对我们颇多启发。所记是三家四人的共同感受。
黄鹤忆旧雨,高驷犹布衣。
促膝斗室宽,曙光破寒翳。
古稀白发人不老,从容豁达今胜昔。
微微春雷百卉萌,欣欣向荣万象新。
江入龙年益澎湃,南枝红梅吐清馨。
致袁宝华
李蕤
袁宝华同志:
您好!
栗栖同志从北京回来,带来您八十寿辰时和战友们唱和的诗集,看到您亲笔写的签名,内心非常激动,并由衷对您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们没有交谈过,也没有通过信,但在我们心灵中,您早已占有很大的位置,并不陌生了。我从1932—1935年在开封前营门“第一师范”读书,您在高中,那时便知道您的名字。“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您为救亡奔走呼喊的声音和身影,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以后,从阎东超、赵其田、张了且、栗栖等同志的言谈中,对您的战斗一生,更加了解也更敬仰了。过去所以没有敢写信联系,主要是您担当着中央领导要职,日理万机,不敢打搅您,怕分散您的精力和浪费您的时间。这种心情,想能理解和谅解的。
您和胡昭衡的唱和诗,我在《人民日报》早读到了。感情真挚,思想深刻,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战斗一生却仍保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读后掩卷深思良久,“正气张弛系念深”一句,蕴藏的思想感情是千丝万缕说不尽的。在这一点上,我有共同的感受,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但愿这种“正气张弛”的局面早早改观,精神文明也能尽快抓上去,我们就放心了。胡昭衡同志与我是小同乡,我们都是荥阳县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以“李欣”的全名发表不少文章作品,以后从政,政绩斐然,但也从没有见过面、通过信。近年他离休之后,又成为杂文界的领袖,为杂文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也喜欢杂文,对他的文品、人品及对杂文的见解,都是赞成的。请见面时代致对他的敬意。
我今年86岁了。碌碌一生,无所成就,从事文学近60年,但顶多只是一名老“勤杂工”。今年春天,又突患胃癌,在北京*******动了大手术。幸医生手术高明,经过一段悉心治疗,恢复情况尚好。如无意外,也许还可以再活几年。但这种病是随时可以复发的,我也不害怕,随时准备着。多少好同志好战友,都已先我而去。自己能活到今天,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也就不错了。
阎东超、金明珍夫妇,我们常通电话,东超耳杂半聋,说话听不清,步履蹒跚,出门也难,但他仍奋勇不怠,写一些回忆录之类。他有一篇推荐河南乡贤的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谈到您,想必读到了吧!
第一次通信,不揣冒昧,啰啰唆唆,写了这么多,耽误您的时间,请多见谅。
祝健康长寿!
李蕤
1997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