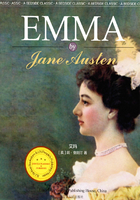像是遇上什么好事了,今天喻倩有些兴奋。
本来我今晚是有个饭局的,但临下班前喻倩突然打来电话,死活要我陪她去吃饭。我说去不了,谁知她竟说人都在我楼下了。推开窗一看,果然见她从的士里探出半个身子,拼命向我招手。我只好草草收拾一下,拎上包下楼。
什么人请客,这么急呀?害得我衣服都来不及换一件。我拿出化妆盒,匆匆往脸上补点妆,喻倩却笑我自作多情:又不是要你去会情郎,打扮什么呀?告诉你,这个人你可夺不走。
我这才注意到喻倩今天的扮相不一般。浑身香气熏人,衣着焕然一新。头发是新做的,脸上也抹得白花花的,嘴上换了层夺目的金属唇膏,脚上也难得地套上一双亮闪闪的高腰皮靴。原来是你要会情郎,让我当灯泡呵?
喻倩咯咯地捶着我,那我还要你去打岔呵?
不等我多问,她就抱着我咬开了耳朵:老实告诉你,这顿饭我比你更怕吃。感觉就是个鸿门宴。所以,你可要给我保驾护航。
你说谁呀?我见过他吗?
没有。我都有十多年,对了,至少有十四年没见过许丰了。也压根儿没想过这辈子还要面对他。可是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的情况,而且听起来还了解得相当详细。上午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扯了半天,然后一定要请我吃顿饭叙叙旧。而且他还说,尽管是断断续续的,但他已经在省政法学院工商管理研究生课程班学习两年要结业了。而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你说搞笑不搞笑?更搞笑的是,我家那口子,居然正好是他们那个班的法学教授!我以往吃的、用的土特产什么的,好些就是许丰送的。
搞不搞笑,就取决于你们原来的关系了。我说。
原来的关系就更搞笑喽!
此话怎讲?
我结婚过来之前,不是在老家电视台当过一阵“民生大观”栏目的编导吗?许丰那时候就是我的搭档。他在部队时学过几天摄像,回来就跟着我扛机子。前前后后,就那么风里雨里、朝朝暮暮地相处了有一年多吧;老实说我对他是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人倒是个挺勤快也挺厚道的老实人。可他那时瘦不拉叽也成天不哼不哈的,年龄小我三岁,又是我的“部属”;而我那时一门心思想出点大名堂,心里哪还装得下他呀?不料他却有了心思。当然,这也是我在那一刻才猝然意识到的。
事后想起来,我的反应也太过激了。害得许丰……尤其是后来那结局。唉,提起来真不是滋味。其实他还真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怎么个不错法嘛?
喻倩的眼中掠过一丝怅惘,沉默了一会才缓缓地说:年头太久,许多事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这人沉稳得很,处世不事张扬,心地却很善。记得我们采访过一个贫困小学,回来后他悄没声息地按月寄三百块钱去,帮助几个失学女孩重新上学。直到他离开电视台后,那几个从小学毕业的女孩联名给台里寄来一面锦旗,我们才知道这事。
他很敬业,也有正义感。有几回我们要曝光一些单位,遭到对方围攻。一看苗头不对,他总是把我推得远远地,喝令我快跑,自己反而往前闯,抓拍了不少关键镜头。因此也经常让人揍得鼻青面肿,甚至成了大花脸。但他不哼不哈,左躲右闪地护着机子拼命拍。有回他让人推进污水沟里,臭哄哄的泥水咕嘟咕嘟直往他脖子上冒,满头都是腥臭的浮萍,他就是不扔机器,英雄高举炸药包般,拼命挺着它,直到我把机器接过去。
至于对我的体贴和关照,那就更多了。许多方面我都被他宠成了习惯。比如我爱睡懒觉,早餐经常顾不上吃,但一到台里,桌上总是摆着他给我备好的早点,我吃得心安理得。干我们这行的应酬太多,我又经不起人家灌;每回都是他拼命为我代酒;我大醉时往往他也云里雾里地飘了,却总是他把我弄回宿舍去,洗涮、呵护,从没有趁火打劫碰过我一根指头。
唉,人与人真是很怪的。他越是这样对我吧,我还越不觉得多稀罕。似乎他天生就该这么对我,我天生就该让他这么关照着。说起来,也怪他感情过于内敛。平时连一点铺垫式的暗示都没有,简直连正眼看我都很难得,我哪知道他会有那种心思呵?说到底,人真是性格的产物。许丰的个性中有一点很鲜明,就是他有时会偶尔露峥嵘。火山似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来那么一下总爆发。比如有回台里卡掉我们一个费了很大劲才做成的专题。是我的眼泪刺激了他吧,也没跟我通个气就悄悄上楼去找主任。结果一巴掌把主任的玻璃杯拍得粉碎,自己的右手掌也被玻璃割得肌腱断裂,差点没废掉。
那天在电梯里,我也是那么着,毫无先兆毫无心理准备也毫无兴致地就突然领教了他的“喷发”——快下班的时候,我们从外面回台里放设备。也许是受了某种刺激吧——一楼到三楼的电梯里挤满了人,我缩在角落里,他怕我挤着,双臂撑紧电梯壁,使劲环护我。我习以为常,埋头斟酌着手里的稿子,也没发觉从四楼开始身边就没有一个外人了。就在电梯继续上行了几层的时候,他的双臂突然从电梯壁上落下,那么有力地箍紧了我。有一个瞬间我觉得气都喘不上了。可直到他的舌头拼命往我嘴巴里拱以后,我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你干嘛?我含混不清地吼出一嗓子,嘴被他堵得更严了。
我一阵厌烦,顾不得多想就挣出只手来,甩起来就是一巴掌。啪一下脆响后,他触电般痉挛了一下,立刻放开了我。一只手却本能地捂住了脸颊——这倒也罢了,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电梯门开了,下班等电梯的台长和几个部主任,一个个瞠目结舌地目睹了这一幕……
如果第二天台长不找他“了解情况”,如果我能够及时和他谈谈,化解一下的话,也许他不至于就此离开台里。其实我清醒后也曾感到有点内疚,当晚也的确给他打过电话,但他的手机关机,我也多少还有些羞恼,没站在他的角度多想些问题,结果,等知道他辞了职后,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时不时地,他那清峻而不苟言笑的神情还会在我眼前闪那么几下。再听到费翔的“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时,鼻子竟也会有些酸——那时候这首歌正红遍大江南北,每当工作顺手或情绪比较放松的时候,我总能听到极少唱歌的许丰反反复复哼着这几句歌词。
这么看来,就是你的不是了。我不客气地责备喻倩:说明人家还是有种种暗示或者说是感情的流露的嘛。自己不解风情倒罢了,还抽人一巴掌!要是我,才不来请你的客哪。
我说的嘛,我说该我尽地主之谊,人家非不让嘛。喻倩有些讪讪地说:好在一顿饭对他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听说他后来混得不错。辞职后就回了浙江老家,把他父亲开的一家模具作坊弄成了一个在江浙、上海都很有些市场的汽模公司;又自掏腰包到大学进修,说明他还是蛮有头脑的。
这倒要归功于你那一巴掌了。正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
你看你看,那就是他!
的士在“希尔顿”对面等拐弯信号的时候,喻倩激动地指着酒店大堂前一个高个儿男人让我看:
许丰!她尖着嗓子大喊起来。
可是许丰没听见她的招呼。他正和身边一个娇小的女人说着什么,来来往往的汽车和它们的笛声、卷起的尘埃及烟雾吞没了喻倩的声音。
不一会,许丰身边那女人上了一辆别克,驾着它离去了。我清楚地看见许丰向车里抛了个飞吻,而喻倩的眉梢也随之高高地耸了起来。
我们的的士随后驶到,许丰一抬头,正好和我的视线打了个照面。我多少有些意外,许丰比我的想像出色多了。按喻倩的介绍,我估摸他也快四十岁了。但看上去不过30多岁模样,长得眉目清朗,相当精神。他的眼睛不大,目光却很深邃,举止也彬彬有礼,且很自然。我估计他身高不下1米80,虽有些偏瘦,但一看就做工考究的褐色西装、暗紫色带浅纹的长领带,使他浑身透出一股颇有几分飘逸的富态感。
我不禁偷眼审视了一下喻倩。忽然觉得她比好几年前我们相识时苍老多了。虽然精心修饰掩盖了不少沧桑,毕竟跌进四十岁了,脂粉已填不平眼角的皱纹。不笑还好,一笑那两颊的肉也明显松垮下来。偏偏喻倩为了冲淡什么吧,还呵啊呵地笑个不停,一开口就把许丰的脸给弄红了:刚才那女孩是谁呵?二奶,还是小蜜?
怎么会呢。许丰的嗓音有点让我失望,低沉而远没有想像中的轩昂:是我那个嘛。
你老婆这么年轻?不是二婚吧?
怎么会呢。
大款嘛,什么不会发生。
我算什么大款嘛。
怎么不让她跟我们一起吃饭?
她昨天刚过来接我。过去在这里读的硕士,也要去会几个老同学。
硕士呀,那比我出息多喽。
我暗暗扯了扯喻倩衣襟。却刚好让许丰看见了。他无声地笑了:没关系的。要是她不这么和我说话,那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姐了。
听见没有?大姐!我说。
我当然是大姐。我比他大三岁哪。
说话间,许丰十分谦恭地伸出手来,将我们让进电梯。许丰揿了39层,说了声那里的观光餐厅挺有味道的,就不出声了。咝咝地滑行声中,喻倩也突然不说话了。但她却暗暗地捅了我一下。我心领神会。油然感到自己的作用。如果就他们俩个,此时此刻,会说些什么或想些什么呢?我悄眼看耷拉着脑袋的许丰,似乎没什么异样。也是,都说时间会抚平一切沟壑。何况他毕竟已是个成熟而事业有成的男子汉了。若还会计较当年的什么,今天就不会请喻倩吃饭了。
点菜的时候,许丰对小姐报一个菜名,喻倩就叫一声不要不要,或者随便点几个清淡点的就行了之类。总之是反对他点那些贵的或华而不实的菜肴。我理解喻倩。况且我也很了解,她的口胃向来是很朴的。平时她最爱吃的反倒是鸡头、鸭颈、毛血旺之类粗菜。显然许丰对此也有数。他特意大声点了一个臭豆腐煲,还颇有几分孩子气地冲喻倩眨了眨眼睛。
喻倩一下子乐了:你也没忘记我们赶完片子,大老晚的在路边大排档上啃龙虾吃臭豆腐的好时光呵?
怪的是许丰像没听到这话似的,并没有接她的腔,顾自埋头翻着他的菜单。喻倩向我吐了吐舌头,好长时间没再开口。
结果,最终买单的时候,那一席三个人的菜,连两瓶干红加鲜榨果汁等,一共花去许丰1800多块钱。小姐用金光闪闪的托盘把帐单送到许丰面前时,喻倩一把夺过来先看了一下,也不假思索就气急败坏地冲着许丰嚷嚷开了:许丰你真是!太没必要了!我们是什么关系呵?值得你摆这种不上档次的款爷谱吗?
许丰舌头有点大:怎么是摆谱呢?这种地方就这个价嘛。而且也没几个菜,怪你们吃得太少了。
还少呢,你都快把我灌醉了。
我知道你酒量的。依着我是要喝茅台的。
嗬!有得这么破费,还不如给我们俩买件衣服呢!
这还不好办吗,一会我们就上商场部去转转。下午我才看过,这儿的商场还是有些上档次的东西的。呶,这条领带就是在那里买的。
不管喻倩说什么,许丰始终一副不愠不恼、照单全收的好脾性。偶尔还会露出他那很少见却颇有几分动人的憨笑。看得出,他对喻倩的这种作派非但熟悉,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吃这一套的。
下楼时,许丰也正儿八经要带我们进商场,但喻倩不肯,他向我摊了摊手,也就没再坚持。
这都是后话,不说也罢。但席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却不能不说一下,因为这才是我要把这个本来没多大意思的故事写下来的真正动因。
虽然十多年没见面了,俩人的谈吐却很少涉及过去。也许是先前俩人通过电话了,他们似乎都没有叙旧的欲望。偶然涉及,也是三言两语就中断了。但我看得出来,喻倩倒没什么,许丰显然是有个结在。
但大家酒喝得真不算少,所以气氛还是比我预想的要宽松。尤其是许丰,他的话确实不多,也很少见他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但情绪还是不错的。他几乎一直在静静地然而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俩东拉西扯些杂乱无章的琐事,很少插话。但看得出他的酒量还是相当可以的,所以也一直在喝酒或者给我们敬酒,一直在大姐长大姐短地为我们俩殷勤地布菜。
我还捕捉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即许丰对关乎到喻倩的话题总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某种特别的兴趣,听得相当专注;只是他的视线一旦和喻倩正面相汇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闪开去。而他喝酒的时候,那酒杯却经常会在唇边多停留片刻,视线从嫣红的酒液上沿射出去,悄悄地驻留在喻倩脸上。
我又一次感到岁月在喻倩脸上留下的痕迹太过明显了些。他不觉得吗?或者说,而今的他,会作何感想?
喻姐你是想炒房吗?
我和喻倩正就时下颇为风行的打肉毒杆菌“毒针”美容的事谈得来劲,许丰忽然插进来这么一句,让我和喻倩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炒房?那是你这号人的事。我这种工薪阶层做得来这种事吗?
那你干嘛不把新房装起来,趁早享受一下呢?
喻倩回过神来:那也要装得起呵。买房的按揭就够我们受了,一下子怎么装得起来嘛?
我想起来了。先前喻倩说过她先生享受到一套高知房的事情。跃层式,近两百平方米,价钱很优惠,但也付了80万。一年多了,一直空关着。原来许丰的思维还停留在那里。
你估算过吗?在这里装修那么套房子,大概要多少钱?
没算过,我暂时根本没这个计划。
我说:我知道,我才装修过房子。像她那么大的,没20万下不来。
许丰哦了一声,说:你还是把它装起来好。
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股认真的韧劲。我开始意识到什么了,而喻倩却还是不以为然:
我抽疯啊?那又要贷一笔巨款,我可享受不惯这种日子。
你不用贷款的。
不用贷款钱哪儿来?你给我出呵?
我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喻倩直直地蹦起来,一手指着许丰,脸却看着我,想笑,那松松的面肌却是歪扭的:听听,听听,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要帮我装修房子!
那可真要20万呢?我的心也莫明其妙地狂窜起来。
20万我有的。许丰的声音依然很平静,神情也不卑不亢的。喻倩却一下子蹿到他身边去,捏起拳头在他肩膀上咚咚捶了两下。许丰埋头一笑,端起酒杯往嘴边送,却被喻倩一把夺过去,一饮而尽:看你都醉成什么样了,还喝!
这点酒,我怎么会醉呢?
不管醉没醉,不许你再说那种胡话了。
好好,我不说了。许丰的眼神有些黯淡。兀自抓过酒瓶,哗哗地将空杯倒满,一饮而尽。
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提起这个话头。
分手时,我见许丰用夹在胳肢窝下的包悄悄碰了喻倩一下,便识趣地闪开了身子。但许丰并没说什么了不得的话。就听他说了一句:那我明天就回去了。
好的,祝你和美丽而可爱的硕士太太一路顺风、幸福美满。
喻倩也真是的,还特别把“硕士太太”强调了一下。好在许丰没怎么在意,他多少有些心不在焉,迟疑了一会才说:万一我有什么事没走成的话,能不能再见到你……你们?
能呵,喻倩说的话还是那么直不窿通的:你能晚点走更好,中午我请你们吃酸菜鱼。不过可别再把你太太给支开呵。我这人快人快语,她不会讨厌我的!
可是,就这么个乐乐呵呵、活泼爽朗的喻倩,一夜之后再出现在我面前时,活像挨了谁一闷棍似的,笑不出来了。
我说过的吧?我说过这人有时候会犯傻,会突然爆出一股邪气来吧?
我倒觉得她自己有点傻。脸色苍白,一绺头发乱糟糟地垂在右颊上,也不知道捋捋。总之一副慌慌张张、心事重重的样子,弄得我也不安起来。
我问她出什么事了,她却嘘嘘地要我小点声,挽着我胳膊说上楼再说。可电梯门洞开时她又不进去了:你办公室有别人在吧?那不行。说话间,两只眼睛骨碌碌地东张西望着,仿佛有人正追杀她。一只手则始终捂紧挂在胸前的坤包。
我说那就到我们接待室去,那儿好像没人。
喻倩却一把将我拽进了楼梯口的卫生间,挨着格子看了一遍,确信没人后咚地一脚将门踢上,这才放心地吁了口气,从包里摸出个信封递给我:看看、看看,你仔细看看是什么?
谁给你的情书,随随便便就让我看?
许丰呗!刚才特地摸到我单位来,把我叫下楼却什么也没多说,塞给我这个信封就走了。我还真当是情书哪……喻倩拍着心窝,还一个劲地抹冷汗:差点没把我吓死!
信封里除了一张质地硬括的纸片,什么也没有。我狐疑地抽出纸片一看,不由得也作起了深呼吸。
那是一张银行本票。金额是人民币二十万元整。
哇噻,这世上还真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啊?
还美事呢,这要让我老公知道,不把我掐死啊!
那你怎么办?
我给他宾馆打电话,说是退房走了。打他手机又关机。说着,喻倩又拨通了许丰的手机:你听听。
我听到的是:sorry,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