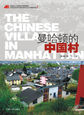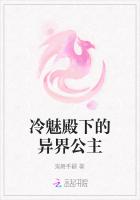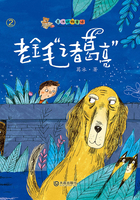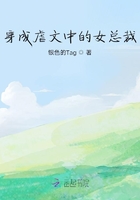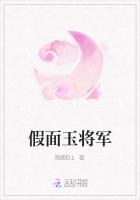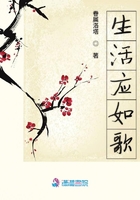曾国藩也听说了,但他有些不相信,这等事也不好向同僚打听。但过了些日子,有件事倒是真的——新皇帝准备出自己的文集了。
这战火连天、外忧内患的时刻,咸丰一面摆出广开言路的架势,一面却尽干些让人笑话的事。曾国藩觉得这新皇帝与老皇帝相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他想想罗泽南的话也对,尽说些隔靴搔痒的话,根本就触动不了这位治国无方的新皇上。于是,他的牛劲来了,作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我要直谏!
他那典型的湘乡二愣子性格发作了,上了第三道疏。疏名叫《敬呈圣德三端防流弊疏》。指出新皇帝三大毛病。原文,大意如下:
尊敬的皇上,想来想去,我要给您提三点意见。您上任不久,但毛病不少。首先是为人谨慎。当皇上的太谨慎了不好,你看历史上的唐高祖唐太宗,他们就放得开。您要管大事,不要尽管些鸡毛蒜皮。第二,您太好名了。年纪轻轻就出版您的文集,前面的皇帝都是三四十岁以后才出,您好名也太早了呢。第三,您遇事要多与大臣们商量。不要什么事都是一个人做主,用人要用刚直的人,不要听信那些阿谀奉承、吹牛拍马之徒。
原文的语气要比翻译的强烈得多。
这道奏折简直是指着皇帝的鼻子,教训这位才登基的新主子。古往今来,谁不喜欢听好话呢?何况是握有生杀大权、无人制约的皇帝呢?所以,年轻气盛的咸丰帝气歪了鼻子。
史载:咸丰“掷折于地”。一般人这样盛怒,就是准备动手了;皇帝这样盛怒,就是准备杀人了。
曾国藩直谏咸丰,这过程一直是个谜。历史学家至今一直没有解开。
巨大的受恩,让曾国藩对大清充满了极端的感激之情。忠于这个王朝成了他的信仰。道光在世时,他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弟子接连得到提拔,从一名普通翰林十年间一跃成副部级领导。因而,他相信道光是公平的、无私的、圣明的。维护爱新觉罗的江山,是他做臣子应尽职责。好好的大清江山,在道光手中还能维持,按咸丰这个儿子的治理,很快就会国将不国。于是,他不怕杀头,一定要冒死说真话。
其次是父子俩的对照,他不忍看咸丰这样瞎折腾。道光是个什么人?尊贵如皇上,却是一个极力提倡节俭的圣明君主。道光请大臣赴宴就是一碗面条。他规定只有自己生日、皇后生日、祭祀天坛才准杀猪。他平时上朝穿的衣服补丁叠补丁,以至于大臣们先要把衣服弄旧才敢上朝。而新皇上呢?上任才几个月就耗资出什么文集,屁股还没坐热,就到处选美。这真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不给他直爽地提点意见,他以后还会变本加厉。还有,有人背后说自己是穆党,一定要洗清这种印象。我是什么穆党?我就是一个忠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算什么鬼鬼祟祟的穆党,我历来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君子,连皇帝的缺点都敢讲,连死都不怕,还穆党,你见过这种自己跳出来的穆党吗?总之,湘乡人的牛脾气来了!
咸丰读了折子,肝火之盛可想而知。
一个皇帝要杀一个人,如杀小鸡,至于罪名,信手一抓就是一堆,连“态度不好”都是一种罪。咸丰把折子掷在地下,恨不得将这个曾国藩立即传来问罪。他对曾国藩不是非常了解,但也有所闻知。
历史演绎出很多版本,有的说是当时的首辅连夜进宫,说服了咸丰,有的说咸丰上朝时,众人力保。
历史的真实,往往尘封在当事人的心底,直至带入坟墓。
咸丰为什么没有杀曾国藩呢?
或者说,谁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呢?
可能的意外答案是:洪秀全之乱救了曾氏一条命。
洪秀全从1851年1月开始,率领这支由农民、矿工、无业游民组成的暴动队竟然把向荣率领的清朝绿营打得屁滚尿流。
对于朝廷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向荣历来有军中悍将之称。他为人狠毒、敢于拼命。连这样的拼命三郎都斗不过洪秀全,咸丰才觉得这伙暴民不可小视了。于是,他赶紧起用一个在清朝军民中极具威望的大人物。经他业已平反,后世称之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出马。
林则徐似乎也决定出山,为这个朝廷尽他最后的努力。
但是不到一月,一个惊人的消息再次传到紫禁城。
林则徐在行军路上死了!
他还没有与洪秀全交火,就病死了。
咸丰速调两广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李星沅上任不久,也和林则徐一样,病死军中。
咸丰既而又忙起用周天爵为广西巡抚。结果被洪秀全打得大败。
咸丰被洪秀全搞得昏头转向。
这时,新任广西巡抚邹鹤鸣主动请缨,说:让我来收拾长毛吧。
咸丰下令前线各部概由邹巡抚指挥。但邹巡抚是个文人,戴罪领兵的向荣根本不鸟他。邹巡抚被太平军围住,向荣懒得去救,还骂道:操******,老子让你去充英雄。结果可怜这么一介文人,被洪秀全的兄弟们乱炮轰死。
咸丰被洪秀全搞得一团糟,前线军事连吃败仗。将领死的死,伤的伤,几个月时间连换了四五任指挥官,不是去见了阎王就是被撤职惩办。朝野各界一时对新皇帝的治国能力产生了莫大的怀疑。
真是应验了那句俗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雄心勃勃的咸丰,被洪秀全连甩了几个耳光,顿时颜面尽失。
这个时候,咸丰要杀曾国藩,他有什么理由?
曾国藩说的,哪一点又说错了?即使说错了,他也是为了大清江山。敢于这么直爽地说皇上缺失的人,早就把生死置于度外。既然曾国藩不怕死,你杀了他有何用?
咸丰在内宫不停地踱步,虽然火冒万丈,却也不得不冷静权衡。
杀之,足可以解心头之恨,但会背上一个杀忠臣的恶名。不止于此,在这个人心向背的关键时刻,要了曾国藩的命,忠臣就会离心离德。
但凡幼稚的人都在想,当皇帝是天下最不受气的人。其实吃政治这碗饭,小官怕大官,大官怕皇上,皇上怕得罪一大片。凡是想吃这碗饭的人,一定要有顽强的心理素质,要低得头,做得小,忍得一时之气。
咸丰抓起一个花瓶狠狠地砸在地上,一位太监跑过来,惊恐万状地望着他。咸丰挥挥手,说:走开。
另一位懂事的太监,轻手轻脚地把碎片扫干净,退了出去。
夜风,轻轻地吹拂着这个深宫大院。
坐了不知多少时辰,咸丰觉得有些凉意。他站起来走出宫门,来到庭院。一轮明月正挂在中天,多美好的天空。那位懂事的太监走过来,说:皇上,休息吧。这月亮好,托您的福,明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咸丰突然有了一种放松感,心想:何必这样与自己计较呢?如果太计较、太冲动,哪里能长久地享受这美好的日子呢?他回到宫内翻出曾国藩的奏折,用朱笔批道:着军机处拟复。
过两天,军机处代替他起草了一个答复:“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批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固直言也。”
看来军机处的大臣们,也并不认为曾国藩有什么大错,认为曾氏不过是直人直语。咸丰把送上来的答复看了两遍,余恨未消,划掉“固直言也”,改成“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
一个迂夫子!咸丰在心里骂道。
名声大震
上完这首指责新皇帝的折子,曾国藩像大醉之后清醒了一样,再读原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但事已至此,覆水难收,你再去哀求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豁出去做两手准备。第一是把这份奏折公布出去,先取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那时候没有报纸电视,所以,他把折子抄了若干份,分送给在京好友,让他们事先知道这么回事,免得自己死了还死得不明不白。然后又把这折子抄正,寄回老家。要让家人明白,湘乡人明白,万一免职杀头,他曾国藩不是养了什么“小三”,或者查出了什么经济问题。他纯属是忠于朝廷,向皇帝说了直话。
第二就是等待免职、勒令回家、充军或者杀头。
免职和杀头这种事,在历史上有过很多先例。皇上一怒之下杀忠臣屡见不鲜。但是这种被杀的忠臣,绝大多数都是换了皇帝就要给他平反昭雪的,而且还要树为后世楷模。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到世上,不就是为了流芳百世吗?如果是免职,则再度起任的机会基本上是铁板钉钉,而且一旦东山再起就等于英雄卷土重来,人气只升不降。你看林则徐不是平反了吗?一下成为举世无双的大英雄。
曾国藩想清楚了,坦然了。他相信咸丰不敢杀他,最多是免职。
虽说不怕杀头,也不怕免职,但曾国藩还是在诚惶诚恐中度过了一周。一周不算长,但对他来说度日如年。不过,等那个漫长的黑色星期天一过,早有内部消息传来,皇上的批语还算温和,只是认为他有点迂。
这是最好的结局。
一份奏折,几张薄纸,收获的却是舆论赞誉。
曾国藩冒死上书从京城传到各省,从官场传到老百姓耳中。一时,朝野一致称颂他确实是一位硬汉子。
陌生人见了面,开口问:你是哪儿人?
对方自豪地说:湖南人。
陌生人就翘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你们湖南人硬扎,出了个曾国藩。
曾国藩赢得了天下第一硬汉的美称。尽管一夜之间拥有了广泛的民意,但在官场上并非就能一呼百应。官场历来是个特殊的场合,尤其是高官们,正义与否,不是他们的首选,利益与个人命运才是他们处事的唯一准则。
很多人都在徘徊观望。
他们想,咸丰也是一个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特别是衣食无忧的上等人最重要的是面子。何况九乘之尊的皇上?曾国藩拿皇上垫背,成就自己忠臣美名,皇上能咽得下这口气吗?
他们深知:历史上凡是伤皇帝面子的人,皇帝迟早要找个借口出了这口气的。
深谙官场之道的人,表面上对曾国藩客客气气,私底下却保持着距离。曾国藩也体察到了这种难以言说的气氛。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学了乖,再也没有如此直爽,如此鲁莽了。他他学会了一种技巧:首先颂扬,放肆拍马,然后提出建议。
这种微妙,同样体现在咸丰身上。
那种类似于骂人的奏折事件发生后,咸丰也收获了一个圣君的美名。普天之下,人民都知道了新皇帝度量之大。竟然有文人写诗吟颂,诗曰:谁个忠臣敢犯颜,湘乡人氏曾国藩,谁个大度如神明,当今圣上第一人。
这不是乱扯吗?哪个诗人会写出这样低劣的诗,顺口溜一样。
其实在权力场,很多文人都写过顺口溜。
舆情如虎,咸丰也得收敛收敛了。而今又是多事之秋,列强窥于外,暴民乱于内,自己的名声很重要。所以凡是涉及到这个湘乡人的事,都得慎重处置,要做得油光面光。
不久,有一个好差事正巧落在曾国藩头上。皇上这时就有权决定这好处给还是不给。给,按原则办;不给,随便找个借口。
按照大清的规矩,各省举行会试,即举人选拔考试,朝廷均得派一名有名望有学问的官员前去该省当主考官。这主考官,管着那一省秀才晋升为举人的晋级大权。这招生办主任一职,难道不是个美差吗?
这美差人人做梦都想。
于是,大清就出台了一个政策:有资格的人参加一场考试,谁考了个第一,谁去!
曾国藩竟然考了个第一。
然后就按组织程序报上去:从翰林院报到吏部,吏部报到军机处,军机处大臣中,分管教育这块的内阁大臣签上“请皇上阅处”。皇上可以签“照准办理”,也可以签上不同意,请第二名递补。至于不同意的借口很多,或者说早定了要派这个人到某地去调研一下;或者说现在有人告这个人的状,暂不宜去,等等。反正,不受监督的人永远是对的。
咸丰没有卡曾国藩,于是曾国藩欢天喜地。
这也向天下官僚传递了一个信息:当今皇上确实圣明!曾国藩还是顺风顺水。于是,曾国藩离京赴江西当主考的前几天,在京与曾国藩有交往的官员今天这个宴请,明天那个拜访,曾国藩更是有宴必赴。
当主考官,灰色收入多多。老家不太宽绰,小家庭也过得紧紧巴巴,能这么顺顺当当捞一把“灰银”到手里,真是一件快乐的事。再说,去江西主考,也可顺便回湖南老家一趟。于是,他打了一个报告给咸丰,说十多年没回家了,这次前去江西主考,想顺便回家看一看。咸丰也准了他的假。
离京前,他兴奋得铺纸提笔,想写一首诗。左想右思却想不出什么好句子,又把以前写的诗翻出来看,忽见多年前写的《岁暮杂感》,一时觉得很合适自己心情。
他不禁轻轻地吟唱起来: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这首诗作于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当时曾国藩进京参加会试不中,因第二年有恩科,遂留在京城寓居于长沙会馆等待第二年的考试。在此背景下,因思念家乡,作了此诗。
岁月消融,一晃十多年。此刻的境遇,与那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但心情却是一样的。
一个人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故乡永远是他心头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