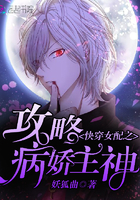两次筹钱
1838年,林则徐受命前往广州禁烟。他被委以钦差大臣之职,正准备干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
是年,还有一人也要干一件大事。此人叫曾子城,后来叫曾国藩。他也要干的大事,跟禁烟、通商、海轮、工业革命这些事毫不搭界,他只想考中进士。
与林则徐这位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的钦差大臣相比,曾子城除了一肚子八股外,几乎要什么缺什么。他眼下最缺的就是一样东西——银子。
1834年冬,曾子诚进京参加会试,落第。他此后便留住在京城的长郡会馆读书,等待第二年的恩科,不料恩科也落第,只好打道回府。通过一年多的苦读,他发起了第三次冲锋。
去一趟京城不易。生活在湖南湘乡乡下荷叶冲的曾家,虽有百把亩薄田,但那时候的生产条件低下,光景过得并不怎么如意。农忙时全家都要下田耕作;农闲时大人要种菜养猪、纺丝织麻,小孩也要帮着干活。例如曾子城就得带着弟弟去十几里路外的蒋字街帮人推板车,或者赶集卖自家编的竹篮。
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曾家的掌门人——曾子城的祖父曾玉屏,却很有远见。曾玉屏决心把长孙(儿子曾麟书不太争气)培养成一个光宗耀祖的人。于是就一心送孙儿读书,当孙儿二十四岁中举之后,曾玉屏举全家之力,送曾子城进京会考!
考了两回不中,这次是第三回了。又要打发孙子赴京赶考了,但曾玉屏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没钱。
越穷越借不到钱,这条法则自古如此。至亲至戚虽然很穷,但都来凑一把。如曾子城外婆家几个老实舅舅,把猪卖了凑了点钱,曾子城的岳父欧阳先生也把多年积蓄都拿出来。
但是,还差一截。
不是没有任何办法。比如,在当地还是有些声望的曾玉屏只要放下面子,到荷叶第一富户人家进门一拜,人家也许会借给他。因为中国人看重下跪。
问题是曾玉屏也要尊严。
如果曾子城再次名落孙山,人家就会拿这个当笑话。
如果曾子城考上进士,小则知县大则尚书,倘若官运通达,拜相封侯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旦官越做越大,今后就可荣及父母,泽被子孙。父母也会被朝廷赐封各种称号,比如光禄大夫,一品夫人等等。试想想,这么一个未来人人敬重的家庭曾给人下过跪,那是何等的耻辱?
唯一可以体面地接受是地方上的富户,认定曾子城有出息主动上门送上一笔银子,曾玉屏就驴下坡,说些无比感激的内心话,那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奇迹没有发生。
要理解荷叶富户们:这是一笔风险投资。帝国农民的小农意识有几千年了,凡是风险投资,绝少有人愿意。
到了快要赴京的日子,曾家猪也卖了,牛也卖了。曾子城的母亲江太夫人纺的麻布也卖了。但还差一笔钱。
曾玉屏决定去王姓表弟家坐坐。
虽说这表亲隔得远一点,但毕竟是亲戚,家里也富有。
曾玉屏到了王表弟家,叙过亲情然后就把话题往孙儿身上靠。说子城的八股越做越好了,子城很懂事,上次回家一路上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套二十三史。王表弟也顺着曾玉屏,说子城这回肯定能中。听着这话,曾玉屏就顺势开口向表弟借钱。
王表弟一听,惊呼道:你何不早说?我刚刚向上坳里四爷买了五十亩田。
无比失落的曾玉屏跌跌撞撞,黑夜里举着火把独自回了家。他召集家人再次商量,最后他掷地有声地说:把上坳丘那三十亩田典出去,有钱再典回来。
这是一个割肉的决定!年轻的曾子城感到沉闷,赴京那天,祖父和父亲送他出了荷叶冲,一直送到通往湘乡县城的官道上。临别他强作欢颜地笑笑,然后消失在两代人牵挂的视野中。
路过长沙,这座他曾经求学过的城市,也引不起他半点留念。曾经站在湘江边写过很多意气风发的诗篇,此时,他半点诗意也没有。他有的只是一股无形的压力。
1838年,北上的曾子城有些沉闷。道光帝的苦恼,林则徐的万丈雄心,此刻都与他无关。他只是荷叶冲里走出的举子,一步一步地朝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目标进发。
好在上天及时给了他一个机会。
二十八岁的曾子城在这一年的会试中,终于如愿以偿,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会试后,他改名曾国藩。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被亲自主持考试的道光皇帝拨至第二名。
不管列位多少名,只要中了进士就行。公元1838年的状元叫钮福保,但后世知道这个人的没几个。不止是钮福保,凡是历史上的状元,让人记住的实在不多。
朝试后,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所谓庶吉士,就是在翰林院当“研究生”,毕业后就可进入翰林院任七品编修。
此时曾国藩已进入“准七品”行列。考试完毕,曾国藩请假回到了老家。
衣锦还乡吗?
只说对了一半。确切地说,与去京城考试前面临的困境一样——缺钱!
前番是进京赴考缺路费,这次是长住京城缺安家费。
如果曾国藩像现在的富家子弟一样,他就根本不必回乡来筹钱。给家里一个账户就行了。家里实在太穷,根本拿不出钱来让他在北京安家。白居易有诗说:长安居不易。作为一个新晋进士,他不是缺一点点钱,而是缺一大笔钱。
安居乐业,住是第一。北京寸土寸金,不说买房,租个房子也挺贵的。清朝政府一律不给官员分福利房,你有钱就买,买不起就租,租不起就滚。
其次是衣食。去北京安家,他必须把家属带去才有人给他料理生活。居家费用也是一笔大开支。
应酬是一笔更大的开销。曾国藩已进入官场。官场讲人脉:你来我往,结成圈子,互相照应,才有出路。应酬的费用越多越好。相比起来,房租还算一碟小菜,应酬才算得上“加州空运牛排”,是个无底洞。
曾国藩的工资收入大约相当现在月薪二千。试想想,这二千要租房、要生活、要应酬,怎么够上开支?
所以,曾国藩决定回乡筹钱。
当然这次是衣锦还乡,与一年前筹集赴京路费完全是两码事。回乡就像办喜事,人家会主动送钱上门。
果然如此。回到家乡的曾国藩,几乎天天有人来拜访。湘乡县令、地方乡绅、中里名流,反正凡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恭贺,顺手送上伴手礼。比如他的同学朱尧阶住在五十里外的江口,用船运来了四十担稻谷。这朱尧阶算得上曾国藩的一个铁杆朋友,每年都会送四十担稻谷来。
不过地方乡绅名士也只有那么多,两个月后差不多该来的都来过了。请了一年假,闲着的曾国藩开始游学。也就是主动地出去走走,访客会友,积累点人脉关系。他觉得自从他们大界曾氏从衡阳迁湘乡以来,几百年没人中过进士,借此机会要修一修族谱。
这给游学找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修谱是穷人富人都感兴趣的事。只要姓曾,除了穷到揭不开锅的人家外,都会出银子。也不管你游学多远,天下反正到处有姓曾的。
这方法很灵验。曾姓族人得知新科进士来修族谱了,往往大鱼大肉接待,走时族上会送一笔钱给他。当然,曾姓之外的人送钱给他,也大有人在。比如衡阳县令、都转盐运使等人借机送上程仪银。
如此这般,曾进士边吃边喝边接银子。一年下来,扣去费用纯挣了一千五百两银子。
一中进士,身价百倍,但家中用度也大起来。原来曾家没几个贵客来,那些粗木家什看着都挺顺眼。现在县府官吏、乡绅商贾要来,一些打眼的家具一定得换。原来穿着的粗衣麻布,现在连曾玉屏老爷子也得细袄皮帽,仿佛不如此,就不像个老爷。甚至曾国藩去岳父家,也得坐上八抬大轿。
所以在离家之前,曾国藩仍然需要借钱。他在1839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记道:“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在曾进士沉溺在个人与家族的“小我”成功中,西方科技发明进入一个井喷时代。1839年,法国发明了摄影术、美国解决了橡胶制品的定型和发粘问题、德国创建第一个电磁单位制、英国有了自行车、瑞典发现了化学元素镧……
这一切不关荷叶山冲什么事。在神州开始快要陆沉了的1839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夜,曾家沉浸在巨大的家族成功中。曾国藩在这年六月初三的日记中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以至曾国藩认为他“趑趄嗫嚅,村鄙可怜”。
只要帝国大厦不倾倒,他家的荣华富贵就在前头。
此时的曾国藩浑然没有半点感觉:这世界快要变样了!
从迷茫到破局
1839年底,曾国藩把妻儿带到了北京(这年年底,他的大儿子曾纪泽出生),在棉花胡同租了一处房子住下来,开始了京城生活。
他开始找到了一种非常有意义而又有成就感的生活方式。
京城确实太大、太繁华,可游历的地方实在太多。
登山、游园、会友,参加各种沙龙,曾国藩的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他最忙的一天会了十三个朋友。
但是,这种游乐与他在湘乡乡下的游乐不一样。自从他中了进士后,在湘乡,他碰到的都是恭维,听到的都是奉承。与这班京城的读书人在一起,若是聊起吃喝玩乐,他几乎算个门外汉。朋友应酬吃完海参席,有的人买起单来,无论多少银子眼皮都不眨,而他揣着游学筹措和向别人借来的钱,常常心疼得要死。
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有一次,他到朋友家中去玩,这位朋友是个富二代,除了妻子还讨了小妾。
那小妾不仅长得妖艳白胖,要命的是抹胸穿得很低,两只酥乳像要冲破束缚似的,活蹦乱跳。
曾国藩的眼睛当时都直了。想想夫人欧阳氏,一副女生男相,简直觉得白活了。
曾国藩见识越多,幸福感就越少。
偌大的京师,纸醉金迷。辚辚的华车碾过,那是富贵人家的车马;姣美的女人回眸,那是他人的妻妾;红红的花朵出墙,那是官家的豪宅。
与在湘乡享受人上人的待遇相比,曾国藩觉得在京城,他这个进士只是一粒尘埃。
曾国藩唯一可以安慰的是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他自恃有才,文章写得好,时时写首什么诗,名义上请别人指教,实际上是炫耀一下自己的文采。
他想听到恭维与赞扬,但别人真的会给他指教起来。有一次,他与一位张姓进士为一句诗争了起来,张进士说:你这个水平,还是先多读读《楚辞》才动笔为好。
在湘乡,谁敢这么说他?
但现在,别人不仅敢说,而且口气里含着不屑。
人家对他不屑,他又能拿人家怎么样?除了争执几句,总不能挥拳相向吧?
他一向自恃的诗文,在京师众多才子中,也不见得出色。曾国藩有些丧气,加上无度的应酬、喝酒、吃海鲜、吹牛、熬夜……他生病了。他的病很奇怪:白天没事,每到晚上全身奇痒难耐,双手抓个不停,抓得遍体鳞伤。这里一块血痂,那儿一块血痂。他去看中医,医生说是血热血燥,叮嘱他一不能喝酒二不能吸烟三不能吃海鲜。服过几剂中药后,稍好一点,医生又叫他静养。于是,曾国藩学会了打坐。
奇痒弄得他经常通宵难眠,家中经济也捉襟见肘。游学挣得的那一千多两银子,用于路费、安家、交际,眼下是塘干水尽了。有一天回家,妻子欧阳氏说:刚才陈佑说要走,说上个月的工资还没付给他,这个月又快月底了,你也没跟他说一声。曾国藩心情本来不太好,就说:我说下个月就给,他怎么这么小气呢?第二天,等仆人陈佑来了,曾国藩说:过了这个月,我就付钱,你找夫人做什么?
陈佑把扫帚一甩,说:上个月说这个月,这个月说下个月,你说话算数吗?
曾国藩一咬牙,说:好好,我下班回来一定给你。
一路上他又急又闷,寻思着向谁开口,好打发这个恶仆走人。他把朋友们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说也怪朋友这么多,可要找个开口借钱的人,还真想不出谁来。这京城就是怪,越要借钱,越借不到钱。不仅钱借不到,还让人疏远你。
到了翰林院,曾国藩进屋就抹桌子。一位同事见曾国藩穿的袍子比较破旧,指着他的袍子玩笑道:你这抹桌布也该换了。曾国藩正在气头上,和同事大吵起来。
真是斯文扫地!
这样糊里糊涂的日子,很快让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在堕落。
一个困顿的新科进士,没钱没权没地位,甚至连学问这块唯一值得光荣的金字招牌,在别人眼里也是一堆烂货。
在老家,他的才学有了进士这名头,作的诗文再差也有人恭维;在京城,他轻易不敢把作品拿出来示众,因为学问好的人不计其数。
总之,这么一位在老家备受殊荣的才子,在偌大的京师实在算不上一只什么鸟。
对于一向好胜的曾国藩来说,备感失落。
经济窘迫、无权无势,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曾家,左邻右舍、亲朋戚友,却把他当成大官。
有事找宽一(曾国藩的小名),成了曾玉屏在亲戚朋友面前吹牛的口头禅。果然,真有这么一位不谙世事的亲戚把几年的积蓄取出来,屁颠屁颠地来到了北京。
来人就是曾国藩的亲舅舅,排行第五,人称南五舅。南五舅进门就说:宽一,帮五舅找个事做吧。乡下实在太苦了。
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哪能替舅舅安排工作?曾国藩说:五舅啊,这事我做不到。
五舅笑道:宽一啊,为舅不会出你的丑,也不会为你的难。就到你单位煮饭,当个烧火佬,这不就你一句话?
曾国藩脸色尴尬,说:五舅啊,这京城不比乡下,我说话不算数。
五舅大惑不解,反问:你舅舅不会干别的,就当个烧火佬。这个你放心,火要旺,心要空……
曾国藩满脸羞愧,说:五舅,你不懂京城的事,这里……
五舅大失所望,说:你嫌五舅老实,不懂京城世事,是乡下人。会丢你的脸?好,我走,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