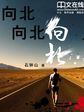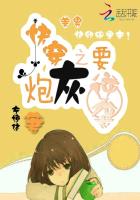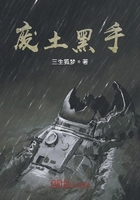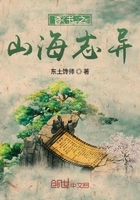皇帝也骂大街
衡州练军正如火如荼。有一天,曾国藩却接到了王錱的来信。王錱一直被曾国藩派在湘南剿匪。曾国藩以为是王錱报来的军事秘况,打开一看,却是一封“辞职信”。
王錱在信中说:自己本来就是个读书人,在湘南连打了好几仗,现在身体有点问题,觉得还是回家读书做点学问为好。因此向曾国藩告假。
曾国藩看出了端倪。王錱连打了几个胜仗,觉得自己军事才能十分了得,有了这点资本,就扮俏了。
这点小心思立马被曾国藩看透了,团练刚刚起步,组织不能分裂。曾国藩立即修书一封,对王錱不吝夸奖之词。然后,恳请他留下,共同完成剿匪大业。
是不是王錱喜欢撒撒娇,让别人觉得他很重要?
不是,因为王錱听到了一些消息:衡州扩兵,资历老的安排带两营兵,但内定王錱还是带一营兵。
听到这消息时,王錱几乎气个半死。他想:老子当年练团时就想称王,现只带一营兵?带十营兵,对老子来说也是小菜一碟。****二巴叔,面铺不要老子,老子去粉铺。于是,他干脆就投奔了骆秉章。
这让衡州湘军高层惊讶不已。按理说,骆秉章应该劝说王錱回到曾国藩手下,但骆秉章偏偏收留了王錱。
骆秉章为什么偏要收留王錱呢?
只有两个字:利益。
你曾国藩扩军,找我要钱要粮。花钱给你养人,不如我自己养人。
不仅要收留王錱,我还要查你的账,审你的开支。有一次,曾国藩打发人往省府去提火药。省府不但不给,反而派出审计组进驻曾部,先查查你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火药。
曾国藩只能忍。火药不足,还可以土法上马自己造,最要命的是粮草不足。一顿没吃,忍一忍,两顿没吃,挺一挺,三顿没吃,各奔前程。
队伍扩大了,筹粮更困难。
曾国藩不是什么神仙,办法只有两个:一劝二抓。
他办起了征粮委员培训班。教委员们第一手:软功。凡是有钱人家,富户商贾,要求委员们多做思想工作,洗他们的脑。洗脑不成的,那就一个字:抓!
委员们哪里有这么多工夫苦心婆心作思想工作?一抓了之。于是,全省之内,富裕人家都被抓得鸡飞狗跳,连左宗棠的小舅子也被抓起来了。
左宗棠忙写信来,请求放人。
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态度是:不能放!
左宗棠只好亲往衡州说情。曾国藩好饭好菜招待左宗棠,就是故意装聋作哑,绝口不问左宗棠为何而来。左师爷只好拉开窗口说亮话:我那小舅子不知何故被大人扣了起来。
曾国藩笑道,你的意思就是要我把他放了?放了他,明天我这儿的人就会全放假。我怎么好向皇上交代?气得左宗棠恨恨而走。
有些史学者因此推断: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源于这件事。
也许这是真的。如果放了左家小舅子,这一万多将士真的都会走掉。因为只要有人敢抗粮不交,其他人就会步其后尘。
军马未动,粮草先行!
雄心勃勃的曾国藩认为:只要把这支兵练好了,成为大清倚重之师,何愁粮草?他计划用两年的时间,把这群农民训练成一支戚继光式的劲旅。
形势不等人。他这锅半生不熟的饭,马上就要端出来给饿极了的朝廷充饥。
1854年春,太平天国北伐军已攻占天津,京师震惊。西征军溯江而上,战船万艘,连江翩跹。
很快,安徽重镇庐州告急。这时候,礼部侍郎宋晋上了一折:“曾国藩乡望素孚,人乐为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路夹击,定能速殄贼氛。”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前同事向朝廷建议,速派曾国藩出省打仗。
面对南北危局,咸丰急召祁寯藻、载垣、端华、肃顺、穆荫、杜翰等六人进宫里议事,商议曾国藩出兵救皖。
因为之前还没有团练出省的先例,所以除了肃顺,几乎是一边倒,大臣们都不同意曾国藩出兵。
是他们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吗?
非也!
反而是他们太看重自己的“国家”了。上面六位大臣有四位是满旗人。满旗入关以后,有个规矩,重要的军事首长都是满人。现在,曾国藩一个汉人,竟然手下统领近两万兵力,这是破坏了祖宗的规矩。
首席大臣祁寯藻道:湖南粮库本来就不足,若是要湘勇出省,则粮草必须由湖南安徽两省供应。现在安徽粮库已空,就只能由湖南一省供给。那湖南绿营的粮饷从哪里来?一旦有事,谁来保省?
大臣载垣立即赞同而且还加了这么一句话:守城剿匪,兵为主,勇为次。
其他人见老大祁寯藻定了基调,一致响应。
首席军机祁寯藻明明知道除了曾国藩这支机动队伍外,从其他地方调兵都不能解燃眉之急。
但是,他反对。
他反对的理由很奇特——因为他是个汉人,又是首辅,如果他支持,他想咸丰肯定会认为他支持汉人军事集团坐大。
其实他是打错了算盘。咸丰这一次是铁了心让曾国藩出兵。因为江南江北两营,均分不出兵力来支持湖北安徽。湖南绿营的兵力也不充足。所以,目前可调用的,只有曾国藩这支湘勇。
咸丰确实无兵可调,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七八十万武装力量。几千里疆防要守,北伐军要堵,西征军要堵,各地的土匪起事要剿。
从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来说,湖北安徽的战事,总不能从东北以及两广调部队吧?那等援军赶到,人家早把城攻下来了。
咸丰道:诸位固然为国家着想,但事已至此,唯湘勇可用,不必拘泥祖宗体例了。
祁寯藻反对得更起劲了,说:曾国藩一介在籍侍郎,素不知兵,平生最好空谈,不可深恃。
他认为,汉臣放肆贬低汉臣,皇上就会认定他绝对忠诚。
次次玩这套路——等于夜路走多了,总要碰到鬼的。这回咸丰发火道:不得再议。祁寯藻遇事不断,罚半年俸禄。
内阁立即集体转弯子,马上拟定圣旨。圣旨道:现在安徽逆匪,势甚披猖……吕贤基业经殉难,江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着即赶办船只炮位,并前募勇六千,由该侍郎统带,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这么长,核心就是一句话:请曾国藩速出兵救安徽,钦此。
曾国藩料定有这么一天来,但根本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他雄心勃勃,对八旗绿营的无能深恶痛绝,也无比坚信,他才是与太平天国抗衡的第一人。但是,他又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不打无准备之仗。接到圣旨,他召集大家开会。
意见纷纷。有人说圣旨不可违,有人说水师根本上不了战场。两派争执得非常厉害。曾国藩说:仓促出兵,无异送死。我等绝不能出兵。
这不是抗旨吗?
该抗的时候就抗,该软的时候就软,这是曾国藩的一条原则。
他说:一是时间太仓促。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二是不能草率出兵。炮火暂时没到,水勇操练不熟。三是我与湖广总督吴文镕商量了,最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合作,统一行动。
罗泽南说:涤帅考虑周全,我认为应立即向皇上奏明。
曾国藩即令一个叫李元度的幕僚拟稿。
李才子才思敏捷,很快就把奏稿拟好送来了。曾国藩看过,在上面添上一句:欲出省剿匪,最早也得明年春上。
写完这封主折,曾国藩略为沉思,对李元度道:你再拟两个贴子,一是要粮,请皇上再在湖南漕米中给我们三万石,二是督促吏部落实顶子。
所谓顶子,就是曾国藩向皇上曾经提过建议,制定了一条政策。捐钱的,给顶六品至九品不等的官帽给他(不实授官职)。但吏部很不得力,这张没有多少价值的“执照”迟迟不发下来。
曾国藩叮嘱道:吏部再不落实,就没人相信我了,也无法募到赞助款。这一条要特别强调。
李元度领了任务,一个时辰又把两个附折拟好了。
曾国藩浏览一番,笑道:好笔力。一面叫亲兵将奏折送省,请骆中丞拜发,一面对李元度说:次青,来,我们下盘棋。
曾国藩好动围棋,有空就和幕僚们下几盘。李元度也下得一手好棋,所以常和曾国藩切磋。
李元度道:皇上肯定还会下旨来催,不知涤帅有何对策。
曾国藩道:别管这些,看子。
李元度一看,曾国藩早已把黑子布在中间。
咸丰收到奏折,火冒三丈。国库那么空虚,我拨银子给你;漕米不准动用,我破例拨粮食给你;内阁不同意你出兵,我力排众议。
你竟然是这个态度,不听调遣?
咸丰火气上来,干脆不用军机处代笔,自己亲自拟旨,他写道:现在安徽特别急,等到明年春上,还要你去干吗?我知道你这个人,尚能激起一点天良,所以才命你去解燃眉之急。但是今天看了你的奏折,你也太自大了,几个省的军务,你一个人能胜任吗?请问你的才能,担当得起吗?
写到这里,咸丰想起祁寯藻说的“曾国藩一介在籍侍郎,素不知兵,平生最好空谈,不可深恃”。更加气不打一处来,恨恨地教训道:平时你就自由散漫,自视甚高,以为天下就没几个人“能出其右”。到真正要你做事了,未必像你平时说的那么好听。这不是让天下人笑话吗?
这已经不是什么圣旨了,全不像一个上级对下级的态度,倒像叉腰骂大街的老妈子。
咸丰坐了一阵,等气稍稍消停些,心想,骂完了,不给粮也不给顶子,说不定就把曾国藩骂到洪秀全那一边去了。于是,捡起要“粮”要“执照”的两个附件。一个批给了户部:用粮是军需所备,你们查清一下要多少。一个批给吏部尚书贾祯:请予落实。
不久,曾国藩就收到咸丰的回复。他没想到咸丰骂街水平这么高。自从三年前冒死直谏以后,他就懂得了一条真理:不能跟皇帝对骂。别人可以修炼成圣人,唯独这位没人敢监督的皇帝修炼不成。
他给这位气急败坏的主子又写了一封情况说明暨效忠信。
他说:尊敬的皇上,收到您的圣旨,您真是谆谆善诱,说得周详备至。您看见我怕事,加以教导,您考虑到我过于矜持张狂,又严加惩戒。跪诵之下,我真是感悚莫名。
上面这番话,全是客套,下面这段才绵里藏针:
不过,目前的实情,恐怕皇上还有些不知道。所以,我还得一一说清楚。一是从广州买的大炮确实没到,二是粮饷确实不足,三是合省联动,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是我与几省主官共同商量的意见,所以不是我轻狂,四是安徽只是战争的局部,湖北才是战争的重心。现在不能为了局部而影响全局。目前我正准备派部分兵力援皖。
这封奏疏,如果写到这里还不足以打消咸丰的疑心,神来之笔就是如下这句话:
与其将来毫无功绩,犯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说白了,既然你这么责备我,甚至怀疑我,我就赌咒。不是我不出兵,我是现在出不了兵。我晓得你要骂我,不如先让你骂,免得到时打不赢,让你来处分我!
咸丰收到这道回折,显然为曾国藩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无可奈何之下,他也不得不安抚一下曾国藩,回了一道谕:“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钦此。”
这意思就是:你是个好人。忠君爱国之心,不止我一个人知道,大家有目共睹。
好吧,既然你赌咒说确实没做好准备,我也不强求。
安徽实在危急,曾国藩与江忠源又素来要好,在京城时就经常在一起游玩,就差没喝过血酒拜个帖了。现在,明知不能救江忠源于水火之中,但是,他还是派了一千人速往安徽。
1854年1月,太平军扑向庐州。庐州是当时的安徽省会。朝廷没有机动兵力可调,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接到了庐州知府胡元炜的求救信,胡在来信中说:庐州城防坚固,粮草充足。巡抚一来,庐州就可以保住。
江忠源率部星夜赶赴庐州。
但这是一个早已预设好的阴谋。
据史料记载:江忠源发觉胡元炜是内奸时,已经晚了。太平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江忠源派人把胡元炜一刀结束了性命。当晚,太平军攻入城内。天明时分,太平军一拥而入,势如洪水。布政使刘裕鉁率领一千余人突围,中途战死。江忠源身受七枪,转战至水闸桥,投古塘尽忠。随行陈源、邹汉勋,同知胡子雝,县丞兴福、艾延辉等人,亦紧随其后投水,副将松安,参将马良、戴文渊等人,则掣刀自刎。
此时,曾国藩派出的一千援军刚到岳州。接到从岳州快马报来的消息,曾国藩仰天长叹,抽笔挽道: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这位湖南老乡的音容笑貌浮现在他的眼前:江忠源是位富家子弟,从小就染上了赌博与逛窑子的恶习,但为人直言直语,急公好义。别人不太喜欢江忠源,曾国藩在京城却不断提携他,经常周济他。
这么一位好朋友死于叛徒的圈套之中,让他尤其伤心。但是,贪生怕死,勾心斗角,此时的官场恶习在战争面前更加淋漓尽致,展露无遗。不久,令曾国藩更加悲伤的消息传来,他的师座——湖广总督吴文镕再一次重演了江忠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