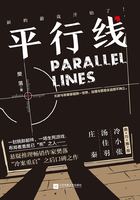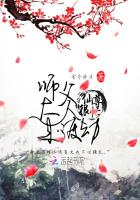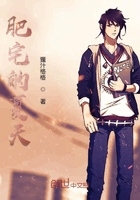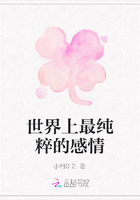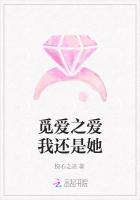陈兴云
这是我的第一个长篇,也是自己垒砌的一座苍莽的高山。码字前我不知道如何穿越它。因为二十来年拉拉杂杂写下的诸多文字,充其量不过是自己堆积的土丘罢了。谁知“高山仰止”,就是几个寒暑——因为都是业暇,从时间上说也就难得了。
写作之初只在内心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没有过多地考虑框架结构、章节篇目,因为我相信“文无定法”。彼时,一旦打开电脑浏览开来,便徒然生出几分困惑,我不知道这样写下去算不算小说。有句俗语,称作“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别无选择地硬着头皮写下去。那是一次艰辛的漫长旅程,总的状态是写得很苦,主要是时间的零散通常导致思维的断层,有时感到有些悲壮,也有些苍凉。不过一旦进入了写作状态,更多的是才思泉涌、感情飞扬,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幸福,别人无法理解更无法体验的幸福。用一个令人脸面发烫的关联词来形容,也可叫做“自慰”。
主题定在官场类上,并非当今官场小说怎么火暴,也并非人们对官场多么关注,而是自己半生就在所谓的官场待下来的,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感受,环境、人物、世俗、心态、灵魂等等,对于我来说,都潜流着一张苍白而真实的投影——有人说过,作品其实就是作家生活的影子。于是就为主题的敲定找了一些理由。但是有一点自己至今仍然没弄明白,这便是时下一些人关注官场,甚至胜过了关注自己的老婆孩子、爱情亲情。其实我理解的官场,仅仅是一个官场而已,它跟一个企业、一个社团,以至一所学校、一家医: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存在,一种社会形态,一个多元化社会构架的分支,这个分支与其他分支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不一样的是生活平台不同,服务对象不同,工作性质不同。而在现实中,有那么多人之所以厚此薄彼,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官场更有特权,更能急功近利,更会使一些人飞黄腾达,或者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其实我不这样认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权力无所不包,谁说企业、社团、学校、医:就没有权力呢?现实当中,有一种现象叫做“小科长现象”,意思是说,实权中的小科长,有时并不比没有实权的“大局长”少什么。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化”。对于一个法制社会而言,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谁滥用权力,成本与风险都是相同的。我不赞成人们把官场和腐败对应起来,也不同意一些人认为官场和酱缸是等同的,谁能保证其他社会阶层和领域就没有腐朽和没落呢?那么写官场究竟写什么,我以为既不是解谜,满足部分人的窥视心理;也不是挖掘腐败,和他人同仇敌忾;更不是引吭高歌,把它作为政治工具。我以为写官场,首先要抱着一个平常的心态,以平常的思想和感情,去写这个特殊平台的人和事,以此去形成自己把握生活支点的独特思考。这里的人和事可能是平常的,是普遍意义的,也可能是特定的,是特殊意义的,当然思考也可能是简单的、复杂的,或者是沉闷的、清醒的。
小说是什么,小说是文学的一种式样,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塑造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多层面地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生活。因此从这一定义上说,小说不是政治,小说家也不是政治家,小说的使命只能是描写社会形态,透视社会生活,留给人们思考。任何夸大了小说作用的立场,就如同夸大了小说家的能量一样。
官场又是什么样的呢,以我的“平常观”而言,官场芸芸众生,异彩纷呈。就人而言,它里面有政治家、改革家,有领导干部、普通公务员;就人的道德特性来说,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也有玩弄权术、钱权交易的腐败分子,还有谨小慎微、不卑不亢的一般工作者;就事物的形态现象来讲,有大起大落、波光云谲,有大浪淘尽、世态炎凉,有朝秦暮楚、我行我素,有按部就班、默默无闻,等等,如此而已。著名作家、评论家张韧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不一定表现为包揽人间的一切,而在于他是不是有其独到的敏感点”。
小说是一种艺术创作,内核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因此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和事都写进去。如何遴选和取舍,要看小说的需要和小说家的水平。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潜意识里过多地充斥了官场的无奈与悲凉,也许自己对这种感观比较敏感,它使我见识了这方面的人事沉浮、虚幻飘渺,这样又反作用于这种潜意识。在我看来,官场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官场中人整天生活在这张网里,游离不出心灵深处的桎梏,感到有些事的确难办——禁锢的体制,人为的障碍,偶然中的必然,都导致了“当官难”的哀叹;还有些是难做人的,难就难在心累,官欲太强,权欲过高,利欲熏心,老想人模人样,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此饱尝煎熬,饱经风霜,甚者丧失理念,染指奴性,有的耗尽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甚至透支了自己的生命,结果到手后,才发觉不过如此尔尔,这些都是极其悲凉的。究其根源,我没有研究过,但我以为用劣根的、封建的礼制与吏治的使然来搪塞,毕竟与现实相去甚远。我十分怀疑曾流传一时的“不好好学习,长大你只好去当官”那句训诫的逻辑性。当今官场已远非封建社会的权力场,在这里,精英荟萃,群星云集,不乏远大理想、真才实学的清官,也不乏睿智豁达、执政为民的好官,倘若他们不为官,而是去引领一个企业,也许会成为一个成绩斐然的企业家;去指挥一个军队,或许会成为一个功勋卓著的将军。那么为何还会出现官场的种种无奈与悲凉呢,我想,这正是一个小说家留给读者仅有一点的思考,尽管这些思考也许是非常沉重和痛苦的。
作家头脑一发热,额头就会发光。小说家不解决社会问题,小说家只解决小说本身的问题,这是他的唯一。解决好小说本身的问题,人物塑造是第一位的。在这部小说里,因为定格在反映一种特定平台下的权力角逐的无奈与悲哀,所以就有了主要人物柳子奇、苏阳波、温一达、九月、甘骆、郦景元等等。在这些人物的构架和塑造上,我扬弃了“高大全”和“坏透顶”式的框子,因为它不是政治小说,也不是“样板戏”。在我看来,对于人物非白即墨的描写,不符合人性化,更缺乏人情味。通常情况下,人具有两重性,就如人是血肉之躯,首先应该具有动物的本能,其次才具有一个社会自然人应该具备的东西,包括道德修养、思想品质、喜怒哀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子奇是一个睿智豁达、受人尊敬的好官,但他也有自己薄弱的一面,比如比较注重个人感情,工作经验相对不足;相应的,温一达却是一个人人嗤之以鼻的贪官,但他曾经也是一个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的好官。在这些变化里面,蕴涵了一个哲学范畴的问题,那就是事物并非是孤立的、静止的、绝对的。当然,在这部书里,我精心构架的人物还不够丰满,甚至在个别人物的塑造上还有硬伤,包括在其他诸多描写和叙事方面,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空转”和回避了一些非常好的小说元素和故事情节,这都给本书留下了一些无法弥补的深深的遗憾。
走过了漫长之旅,穿越了高山的苍莽,虔诚的文学情结与浓厚的创作欲念如花蕾绽放了,但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轻快,就像这部小说一样,带给自己的始终是铅一般的沉重,我想这归根结底应该是对作品本身的过多苛求,以及对作品之外的种种思考。
最后,我要特意感谢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王蓬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汤亚竹先生,他们或为本书写下简洁深刻的评语,或为本书的修改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