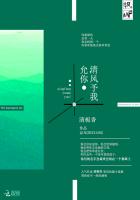国歌、国旗、国徽,同样的庄严和神圣。可我对于国歌,却更有一层复杂激动的感情,因为它讴歌东北,为抗战而生。许多东北人每听到或唱起它的时候,都有流泪的冲动,这是一种难舍的乡情,还有深厚的爱国感情。
吉林作家乔迈在《岁月物语》中说:我长到了十一岁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假使我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那么我会很幸福。世上称得上幸福的人大概是两种人:傻子和健忘症患者。
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绝其语。日本实行奴化教育,用日本东京时间计时,妄图泯灭东北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东北一切日本化。
我有许多本伪满教科书,当时东北人是“满洲国人”,不是中国人。更不是日本人,因为没这个资格和水平。要称日本为“友邦”、“亲邦”,否则就是“思想犯”。日本投降后,许多东北人发誓不再说日语,互相监督,再说打嘴巴,终于改了过来。
中国人都熟悉《最后一课》。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赔款25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都德参战,痛心法国的惨败,1873年创作了《最后一课》。
课文里说,小弗朗士逃学到野外游玩。“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画眉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剧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韩麦尔先生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绿色礼服。小弗朗士后悔没有好好学习法语,他听得极其认真,连镇里的成年人也来学习。下课时,韩麦尔先生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最后一课》由国学大师胡适翻译成中文。
我在中学里学习了中文和英文的《最后一课》,依稀记得那时听课的朦胧感觉。日本也教,但日本没有类似的历史,无法体验那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酸楚和感受。如果说有,日本鬼子就是那些普鲁士士兵,而我们东北人则是教师“韩麦尔”,是镇上居民“郝叟”,是“小弗朗士”。那是我们的“最后一课”啊!
东北也曾是“阿尔萨斯”和“洛林”,拥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矿,同样被来自东方的侵略者垂涎欲滴几番掠夺。
那时,我没意识到汉语是多么动听,多么优美。如果在沦陷时,我接受奴化教育,不会想象祖国历史多么伟大光辉,祖国意义和份量多么重要。有时我以小人之心恶劣地揣测,普鲁士军队占领小镇后,小弗朗士学德语一定会很生硬和蹩脚。韩麦尔先生还敢讲法语,还敢在黑板上写“法兰西万岁”吗?他也会学德语吗?所有猜测因为《最后一课》是虚构的小说而毫无意义。毕竟是都德替“韩麦尔先生”教法语,替“小弗朗士”认真地听法语。
当时人们不爱学日语,痛恨日本人,就连小孩玩游戏时都爱当中国人不爱当日本人。喊“大日本帝国万岁”时,学生们就借机喊“万岁”的谐音“完事”。强迫学生向东方天皇“遥拜”,学生就称这是日本“要败”。强迫对阵亡日军默哀,人们就小声说:“小日本快完蛋了!”德惠宋克恭老师告诉学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同关里人是兄弟。”敌占区流传一句话:“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两年用不着。”
1932年3月12日,沈阳一小学庆祝“满洲国”成立,学生喊:“中国万岁!”鬼子恶狠狠地叫道:“谁敢再喊,我马上杀了他。”一阵沉默过后,一个三年级小学生振臂高呼:“打倒小日本!”屠刀向他砍去……他是年仅十岁的高麟府!
1935年11月25日,日本宪兵队在新京、哈尔滨逮捕一百多名有反日倾向的学生,塞入车厢,然后炸毁。而在安徽芜湖,74名小学生因反日被处死。可见,哪怕是孩子也不放过,恰恰是孩子才更不应该放过。这就是殖民者的心态。
1998年4月,在长春义和路旧书市场上,我见到一位老人张济。他曾从事公安工作,从小受过殖民教育。像往常一样,我见到老人都有意打听日本人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一头飘浮的白发是流淌着那段历史的滔滔松花江。他对我讲述九岁时经历的一个故事——中国顶天立地,就如同沉沉暗夜里的一道明亮的闪电,放出瑰丽的光芒。我周身的血液呼地一下沸腾起来,感慨良久,当时脑海中就闪现出:最后一课。
1938年,张济正上小学,那时老师上课用日语、日文讲授,不敢讲是中国人,否则必受严惩。他当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一天,一位身着青衣的男地理老师第一次告诉他们,中国是祖国,日本是侵略者,并且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一个直抵黑板上下沿的“中”字,巨大而苍劲,并用手指着“中”字说:“中国顶天立地!”可第二天,老师就再也没来。老人沉痛地说:“可能被害了!”
由于年代久远,老师的年龄、名字及其它情况,老人都不记得了。我始终坚信,这是我听到的最有价值、最为生动的真实故事,这是一篇足以流传千古的爱国主义篇章,即使最出色的文学家也无法创作出能同它相媲美的小说,任何的努力都将苍白无力。仅仅为了这一个讲起来不到一分钟的故事,我在长春这五年也值得。
东北人对于国家的爱,民族的情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落实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战行动之中。
1932年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借口“护侨”决心直接出兵进攻哈尔滨,命关东军第3旅团长谷部照少将率第4联队、炮兵大队及坦克2辆,从长春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去哈尔滨作战。
日军28日晚上8点50分,从长春宽城子车站出发,第二天也就是29日一早就赶到了老少沟。这中间100公里路程,日军用了10个小时左右。
老少沟位于德惠县的东北,边上就是松花江大桥,中东铁路从这里南北向通过,而松花江则东西向流过,老少沟这里有汽船码头,因此也是一个水陆交通要道。如果日军进攻哈尔滨,那么必定经过老少沟。东北军独立第22旅663团陈德才部驻防老少沟,严阵以待。
1月29日早晨8时许,日寇先驱装甲列车行驶到松花江南岸的德惠老少沟附近大路堑内,遭到东北军伏击。日军的纪录中明确写着,“在老少沟附近遭到敌人步骑兵五六百人的抵抗”。
我军炮火猛烈,日寇死伤惨重,陈德才团对铁轨进行了破坏,日寇被阻不能继续进犯,经过反复较量,最后突出包围,29日夜间赶到三岔河站。列车从老少沟运行到三岔河(今扶余站),之间仅仅25公里,日寇用了十几个小时,可见遭到了顽强的阻击。日军早晨开始战斗,到29日晚上,也就是差不多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才到三岔河车站。以此推断,陈德才团的抵抗大概迟滞了日军半天的时间。陈德才团破坏了铁轨。这点在日军的报告中都有提及,也在这张明信片上有所显示。不过日军出来两列火车,头一列就是装着抢修材料的。陈德才团尽管奋力阻挡,但却没能彻底挡住。
第二天,敌长谷部旅团司令部及大岛联队本部乘坐的第二列车在黑龙江双城脱轨,死伤数十人,车上所载野炮十多门全部翻落于路基下面,多数被毁。31日拂晓,又遭到伏击。
很遗憾,东北军最终从东北完全溃败,这时东北义勇军力挽狂澜,顽强抗击日本的侵略。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爱国军民自动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他们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使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
1935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留学日本的田汉参照日本的进行曲,为片中主人公创作长诗《万里长城》拟写最后一节诗稿,后来被作为影片的主题歌词,这便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看到歌词后,青年音乐家、共产党员聂耳于1935年3月中旬开始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最后在日本东京完成作曲,4月下旬《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同缴获敌军三八大盖打击敌人,终于成为不朽的抗日号角。
2002年秋,在沈阳收藏家詹洪阁藏品中见到日军731军旗等许多珍贵的日本侵华罪证,还有一套1934年日本陆军恤兵部编辑、大正写真工艺所印刷的日军战死名册《从军满州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上有金箔照片,装饰精美,可谓价值不菲。费尽苦心,我书中终于找到与家乡有关的记录:“步兵第七十六联队陆军步兵营长清水口松二昭和8年6月3日,吉林省德惠乡骑涉场战死。”
以前,我从没有发现一个死亡在德惠的日军的名字。清水口松二,典型的日本名字,还有些古典的诗意美。清水口松二,他以死赎了在我的家乡的罪孽。骑涉场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从没有听说过。清水口松二在这干了什么,什么样的战斗,打死一个步兵营长,而没有士兵,我更无从考证。
昭和8年6月3日应该是1933年,美丽的夏季开始了。义勇军风起云涌,恐怕清水口松二就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了。为了击毙一个清水口松二,谁将成为烈士我无从知晓。让我们重新走进历史,寻找那失落已久的热血。
田汉和聂耳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歌颂了东北义勇军。德惠义勇军当之无愧,至少能拥有国歌一个音符或一个笔划。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胜利就有牺牲。九一八不抵抗,或少抵抗,东北人的面子东北人丢掉,还需东北人自己挽回来。从不抵抗到抵抗,东北人实现了精神和血性的回归。
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之际,沙俄侵略军也洗劫了我的家乡德惠八大股子。梳着辫子的德惠老百姓有力地打击侵略者,但是450人就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德惠,县中学师生不胜悲愤,训育主任李郁华老师进行题为《破巢之下岂有完卵》的演讲,大家失声痛哭,会议不能终场。11月,德惠县成立抗日救国会,李郁华任会长。
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30万人。他们大都是胡子土匪发展而来,哪怕光着膀子也要冲锋陷阵,没有那些政客冠冕堂皇的理由。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歌颂了东北义勇军奋起御侮、同仇敌忾的英雄形象,号召全国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德惠义勇军当之无愧,至少能拥有国歌一个“音符”或一个“笔划”。
王辅臣,是清末秀才,人称其为“王三先生”。1932年2月,接受吉林省政府主席诚允委任,担当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之职,县中学训育主任李郁华任政训部主任,最盛时队伍达2000多人,军旗为李郁华、李英华的妻子绣制,红地黄字:“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1932年9月5日,德惠义勇军攻打县城,保安总队防守顽固,日军飞机前来助战,攻城失利。
这一时期,罗明星率领“三江好”义勇军攻打德惠火车站,缴获枪支80余支、炮弹13箱、子弹1万多发,有人因此说最早的铁道游击队在吉林。
1932年10月,“占江南”领导德惠义勇军伏击200多日军,经过四个小时激战,歼敌40多人,缴获30多支枪。
1930年代上半期,由于思想复杂,意志不坚,加上叛徒、汉奸出卖,德惠抗日义勇军仅一年就失败了,连他们的足迹都无处可寻。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但是许多德惠优秀儿女依然前仆后继,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太行山麓,热血化作朝霞。他们牺牲时还年轻:李英华、李郁华兄弟是22岁、28岁,抗联师政治部主任陶净非30岁,八路军某部参谋长胡乃超32岁,八女投江的女战士所在抗联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37岁。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中,战斗英雄杨林25岁。
2003年正月,我见到德惠义勇军司令王辅臣的后代,他们都对先辈被冷落感到寒心。德惠烈士陵园白雪覆盖,展室里空空荡荡,墙上介绍王辅臣等抗日英雄的事迹,图片上覆盖着参差不齐的塑料布,确实寒酸一些。工作人员都很热情,领我参观。说本来德惠烈士陵园在市中心挺好,但是地方被法院占了,只好迁出。我听说迁陵时损失一些遗骨,他们证实“拉了一大半截子卡车,多少糟尽点”。还说缺乏经费、资料,没办法,希望我多宣传,我说家乡人理所当然。
李郁华、李英华兄弟二人是德惠县最早传播革命思想和抗战理念的仁人志士。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李氏兄弟目睹东北大好河山惨遭铁蹄践踏,就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并先后在黑龙江抗日战场献出了自己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家乡人民称赞为“一门双烈 抗日二杰”。
李郁华牺牲多年后,其女儿李雪琴始终惦记宣传父辈的抗战事迹,弘扬抗联精神,但因身体欠佳、家事操劳未能如愿。女儿去世后,外孙李洪泉等后人继承先辈遗志,搜集整理抗联先烈史料,并希望世人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李洪泉还深情地写道:“碧血丹心赴国难堪称先烈,白山黑水颂英魂昭示后人”。
无独有偶。2002年,我在沈阳结识了一群义勇军将领的后代。他们大都来自农村,穿着朴素,言谈不多,说着一口辽宁土话,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和尊敬。透过他们的眼神,仿佛看到先辈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英姿。他们目的不过分,就是要求给前辈一个烈士称号,并享受烈属待遇。然而我至今也没有见到他们谁达到了目的。
高鹏振,土匪出身,报号“老梯子”,寓意步步登高。1931年九一八时,因伤在沈阳养病,亲眼目睹日军侵略,义愤填膺。9月27日,成立“镇北军”,竖起兴中抗日大旗,这就是最早的抗日义勇军。200多人后来发展成千匹铁骑,驰骋辽西,与日寇激战,但是3000多人也曾被16个日本兵吓得跑出60多里。
1937年5月,高鹏振负伤,被叛徒杀害,年仅40岁。房子被烧,5名亲人被害。儿子被迫隐姓埋名,改名叫张汝,由于特殊的经历,胆小怕事。解放后当教师,被批斗,晚年家境困顿,儿子因车祸没钱治而落下残疾。我看到82岁的张汝在病床上写的亲笔信:“岁月流逝,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今思亲人,不禁潸然泪下,千言万语,欲诉无从,心绪已乱,写不下去了。”
共产党员王立川受党组织派遣,改编高鹏振的义勇军,创作《血战归来》讴歌义勇军抗日事迹,1933年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田汉看到后,振奋不已,写出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王立川后来在苏联间谍左尔格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不幸在齐齐哈尔被日本宪兵逮捕,英勇就义。
听到一个笑话,一抗日英雄被日军逮捕,灌辣椒水,上老虎凳,没招。日军使美人计,他将计就计,拥美人入怀,还是没招。日本人无计可施时,他建议还使美人计,日本人勃然大怒,狠狠打了他一顿。
高鹏振部下陆子然骁勇善战,被日军刺刀穿透身躯,奇迹般生还,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1962年死于政治迫害。陆子然之子陆德新为父亲写传记,从他嘴里我了解一个故事类似于那个笑话。主人公姓范,高大英俊,报号“野狼”和“二里半”,意为枪准,杀鬼子狠,二里半内弹无虚发。
当时鬼子诱降,让义勇军攻打东北军驻守的锦州。王立川、陆子然、野狼三人诈降,鬼子好吃好喝供他们,并送上三个美丽妖艳的日本女人。惟独野狼享用,玩了三天三夜,把日本女人搞得吱吱乱叫。他说:“日本鬼子祸害多少中国妇女,我他妈的也报复一下,尝尝日本娘们的滋味!”
这种行为似乎不象传统的共产党员式的抗战英雄,但他的确是英雄,大大的英雄。大家要理解野狼,他既然诈降,就得做出土匪状来,否则会使日军生疑。何况他本来就是土匪,即使平民百姓不也有七情六欲吗?他们成功地诱骗了鬼子许多枪支、金钱,又打鬼子。1998年,野狼故去。2002年,最早的义勇军中健在的还有王玉楼。
王玉楼,辽宁黑山县人,1913年出生。属虎,9月初生日,村里属他年龄最大。
1930年,王玉楼受地主迫害,被逼卖了地,换了14支枪,参加了高鹏振的土匪,报号“大快车”、“草上飞”,意思是跑得快。按辈份,高鹏振还叫他老舅。17岁任警卫小队长,管100多人。
九一八后,他在锦州见过张学良,一起吃住。张学良鼓励说:“弟兄们,有我张学良就有你们,中国人不能亲日!”王玉楼每月军饷是张学良发的27块大洋。
他和战友每人骑两匹马作战,一匹负伤或战死后再换乘另一匹。第一仗打死24个鬼子,缴获24支步枪,3挺歪把子机枪。他共打仗几百次,能在马身上打枪,2、3里地外能用枪打在马身上。在辽宁康平、法库一带,杀得日伪军警狼狈不堪。
一次,抓住30多岁的日本铁路技术员中桥,用绳子捆住。中桥喉咙被勒得喘不过气来,王玉楼可怜他,准备为他松绑。中桥却兽性发作,一脚踢在他裆上。
王玉楼一看火了:“杂种操的!我让你踢!”就抄起棒子,打塌了中桥脑袋,血往外喷。王玉楼说:“活埋!你们日本活埋多少中国人!”随后一枪把中桥打在坑里。
彰武战斗中,王玉楼和一个战友肠子被打出来,喝水都直往外流。高鹏振认为伤员是累赘,就把战友给活埋了,还让王玉楼交枪,他怕被活埋,就说:“我死也枪不离手!”心想,“谁敢碰我,我他妈地就用枪把你们全都突突了!”
他自己把肠子塞回去,伤口用鸡皮包上,庆幸的是,40天好了。伤痕如金灿灿的勋章一样珍贵。
王玉楼后来加入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他说见过杨靖宇,我有些不信,怕他记错了。他说:“杨靖宇挺和蔼,大个子,高鼻梁。”我说能有多高,他郑重地说:“比你高多了!”杨靖宇一米九。
2001年秋天的王玉楼
1933年抗联攻打哈尔滨日军仓库,王玉楼在撤退中被俘,被以“反满抗日”之名关进监狱。
中国警察用刑,上铁床和滚钉板,灌凉水。日本次长坐在太师椅上乐得直拍巴掌。王玉楼对警察说:“咱都是中国人,你不该这么狠!”他始终没交待根据地位置,手指被打断至今还歪着。
他至今还恨汉奸。我说:“你现在见着汉奸怎么办?”他眼睛一瞪:“我整死他!”“你能打过吗?”我问。“我暗里拿把刀,也得捅了他!”老人坚定地说。
王玉楼在监狱里被迫做军用皮鞋、马靴。后来还修丰满水电站,日本投降才出狱,回到阔别10多年的家乡,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文革时说他欠日本人民血债,他十分气愤。
谈起自己的生活,老人感叹:“抗日一生,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块钱也没给。我不图钱,最主要不平衡。张学良到我眼前,也得给碗饭吃!”他说要去国务院说道说道,地址都打听好了,国务院在北京长安街道南有招待室。有人曾许诺为他办英雄补贴,拿走1000元“活动经费”,这几乎是他全部积蓄,一去了之!老人有些失落,就喝起了闷酒。不过老人也自豪:“死后我也甘心,我没当亡国奴。是中国人,做中国事。”说了能有20多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始终拥护共产党,死后做鬼也是共产党的鬼。”
老人经常动情地想念战友,梦里还与他们欢笑,最后醒来时才发现都已远去,只剩下他自己了。他就经常哭。
我离开他家时,他执意送到门口,小三轮车拐过墙角,我还见他向我张望。我有些神伤,也许不会再见到老人了。
落日余辉,渐渐褪尽,暮色袭人。我离开这块当年义勇军出生入死战斗过的热土,耳边仿佛又回响起那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聆听的旋律,雄心勃勃地走向远方。
国歌作者田汉还写诗,精练地刻画了义勇军光辉英勇的形象。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