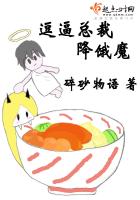赵兴东本来和田翠蛾说好今天去贾柳沟问油价,不过在林强家耽搁了大半天,而且现在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需要跟田家商量商量,就径直往田家来了。
进了门,田氏母女正在等他,不等赵兴东坐下,田母就问道:“兴东,今天跑的咋样?油价问清楚了没?”
赵兴东接过田翠蛾递过来的毛巾,擦了一把脸,这才说道:“姨,这油生意怕是做不成啊!”
田翠蛾一听这话,先有些急了,忙问道:“咋回事兴东?昨天你还说他们村正发愁油卖不出去呢,今天咋就不成了?”
“姐,你先别急,听俺给你慢慢说。”赵兴东说完,在脸盆里摆了摆毛巾,又在盆架上挂好,走到桌前坐下,这才不紧不慢的说道:“俺在县城有个叔,是在政府工作的,今天俺想找他借个自行车,也好去贾柳沟呀。结果俺叔问干啥用,俺就说了。哪知道俺叔一听是这事,就急了,拉住俺说了大半天,这不刚才说完,我就急巴巴过来通知你们了。”
田母听了问道:“兴东,听你这话,今天压根就没去贾柳沟?那你叔是不是也不同意咱卖油,啥理由吗?”
赵兴东接过话道:“姨,是没去成。”然后就把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说了一遍。田翠蛾年轻,原来倒卖东西,无法无天惯了,根本就不知道违反统购统销政策的后果,但田母年长到底是中年人,一听赵兴东这话,一怕大腿叫道:“哎呦!这昨天光急着给小蛾找活干,咋把统购统销的政策忘了,唉……这以后可咋办呐!”
田翠蛾虽然不懂政策,可见母亲也如此反应,知道赵兴东说的不假,寻思着自己倒卖一尺布票就丢了工职,要是倒卖国家专控的油,那还不枪毙啊。越想越郁闷,脸一下阴沉起来。
赵兴东见母女二人没了精神头,急忙劝解道:“姨,姐,你们也别急,这还有其它路数。俺叔说,中央从去年开始调整政策,要花大力气搞经济工作,这国家专控物资咱不好弄,咱可以搞其它农副产品呀,我看鸡蛋就行,这城里人吃鸡蛋的多,咱们去乡下收些鸡蛋来卖,也赚钱。”
田母听了这话一思量,也觉得可行,转忧为喜道:“对呀,这鸡蛋县里一直供应不上,商场、供销社、国营副食店都缺货,也就是最近开张的乌四集自由市场里,有些农民在卖,这生意能做。”
田翠蛾好歹在商场工作了两年,对鸡蛋紧俏的原因,有所了解,补充道:“国营单位进的鸡蛋,主要都是来自国营养鸡场,可产量太低,根本不够,我们商场原来要是进了鸡蛋,也是内部职工先买,这职工哪个不是自己买完,还要给亲戚朋友买,最后就剩不下多少了。这些剩下的鸡蛋,个头小不说,破的也很多,就这从来都是当天卖光,不带剩的。这鸡蛋生意有的做!”
赵兴东还有个疑问,就说道:“俺记得小时候,供销社也到农村收鸡蛋,后来就没见供销社的再来过,这是为啥?”
田翠蛾有个同学在供销社上班,给她说过这事,所以大概知道一些原因,就解释道:“供销社的职工,也都是国家职工,谁愿意走村转巷的挨家挨户收鸡蛋,这可是个脏活、累活;再加上浪费巨大,有他们自己偷吃、偷拿的,还有路上碰坏的、搁臭的,供销社是收一次鸡蛋,陪一回钱,最后也就不收了。”
赵兴东听了供销社赔钱不收鸡蛋,高兴的说道:“那没人和咱们争了,这好、这好。”
田母想了一下说:“不对,还是有人和咱争!”
田翠蛾、赵兴东一听,都有些急,异口同声的问道:“是谁?”由于意外的同时间说同样的话,两人都有点差异,彼此看了一眼后,相对一笑,竟然生出点知音的感觉。
田母倒没注意两个小年轻的表情,自顾自说道:“农民自己呗!有的农民自己到集上卖鸡蛋,还有的跑到城里,拿鸡蛋换粮票、布票。”
赵兴东知道有些农民把鸡蛋换成粮票,再添点钱,用这些粮票去国营粮店买点粗粮,以弥补家里口粮不够吃的窘迫。当然也有直接拿鸡蛋换粗粮的。应该说,农民拿鸡蛋换什么的都有,反正是家里缺啥,就换啥。
田翠蛾听了母亲的话,不以为然道:“妈,您还真打算把这生意独霸啊!就咱们这点本钱、这点人手,能做多大啊!有的农民自己卖鸡蛋,就让他们自己卖呗,不影响咱们。”
琢磨琢磨闺女的话,田母觉得也对,这鸡蛋市场大着呢!哪是自己可以独占的?不由讪笑起来:“中,小蛾这话没错。那咱合计合计,看这具体咋弄。”
赵兴东还是一如既往的想先听别人的意见,招牌式的微笑挂在脸上,没有先说话。田翠蛾倒是觉得前途似乎又光明起来,抑制不住兴奋,率先说道:“妈,这买卖简单,我和兴东收鸡蛋,您老给咱卖。”
田母听了心疼女儿道:“这兴东还要念书,平时收鸡蛋主要靠你,你一个女娃家,咋干得了这活。鸡蛋又沉、又不好拿的……”
牵扯到自己,赵兴东不好说话,没有知声,但田翠蛾受到昨天自杀的刺激,反而生出些泼辣,倔强的昂起头,带着自信说道:“妈,不要小瞧你闺女,我就不信,我这么大个人,连几十斤鸡蛋都收不了,这男人能干的事,我也能行。!”
听了女儿信誓旦旦的话,田母心里是又欣慰、又难过,叹了一口气,说道:“小蛾,娘觉得你真长大了!”说完眼角不禁一热,涌出两行泪水。
看着这对母女,赵兴东心里也颇感慨,这就是亲情啊!联想到自己的孑然一身,不由的有些神伤。
田翠蛾见两人都默然不语,岔开话题道:“兴东,那你就礼拜天多辛苦、辛苦,只要鸡蛋能收上来,咱肯定是不愁卖的。”
“中,姐你放心,咱自己的买卖,俺咋能不上心呢!”赵兴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那这个收购价定多少呢?咱们到那些村子收呢?路线都咋走?得好好合计合计。”
说到具体经营,三人都来了精神,热烈讨论起来。
当时的农村,因条件、政策限制,没有什么有规模的养殖业,农民家里有几只鸡,也都是散养的,这些鸡和主人一样,平时都在土里刨食,营养、管理根本谈不上(现在都是精饲料圈养,管理严格)。所以每天都下蛋的鸡,只在传说中存在,谁家能有只两天就下蛋的鸡,那可都当宝贝,左邻右舍都会羡慕的要死,通常的鸡是三、四天才下一个蛋。并且受气温影响较大,天热下蛋多,天冷下蛋少,不过要赶上酷暑,鸡也不下蛋,受了惊吓的鸡,也不下蛋……总之一句话,鸡蛋产量很低。
要想收到鸡蛋,而且想多收,只有提高价格,因为农民是最实际的人。毕竟农民到城里卖鸡蛋,不仅要在市场里蹲一天,还要受尽城里人的白眼,如果农民觉的自己卖鸡蛋,多挣不了几个钱,肯定愿意把鸡蛋让人收走。但收购价太高,自己就没了赚头,因此合理的收购价,是生意成败的关键。至于卖价相对简单,随行就市即可。
田母一直做家庭妇女,到底对柴米油盐了解的多,又是长辈,最终以她的意见为主导,定出了粗略的框架,并对工作简单分了工,头三天,主要以市场调研为主,确定好收购价,以及了解周边村庄鸡蛋的产量。毕竟毛主席都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嘛。
第二天一早,田翠蛾先到街道办开了介绍信,毕竟将来走村串户收鸡蛋,不拿介绍信的话,容易惹麻烦。然后骑上自行车,带着干粮和水壶,以及为和村干部们拉上关系的香烟,开始对县城周边的大型和中型村子逐个进行调研。
而赵兴东则要发挥自己是农民的这个有力条件,在自己村里、亲戚村里、同学村里,广结人脉,建立起基本的收购体系。
田母也没闲着,不仅要做县城市场的调查,并且要准备好各类用具。三人约好,三日后的晚上,再在田家碰头,定下最后的事宜。
赵兴东还是天不亮就起床,练完功然后洗漱一番,带上出门用的东西,跟学校看门老汉招呼了一声后,就赶往长途汽车站。
八月末的清晨,此时已经大亮,县城街道上空空荡荡,半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偶尔的轻风吹过,一丝清凉中带着些许寒意,让人在舒爽的同时,身体也不由轻颤。赵兴东享受着此刻短暂的宁静,心头涌起的却是对未来的渴望……
坐上第一班车的赵兴东,早早拿出了英语书,默默念着令他咬了无数次舌头的洋文,让坐在他旁边的老汉,着实在心里面,把这个学生摸样的娃娃夸了个遍。枯燥的旅程在近两个小时后结束,幸好赵兴东的村子就在公路边,下了车,他没有先进村子,而是沿小路走到了村里的坟地。
野草丛生的坟地里,堆着些大大小小的土包,每个土包上的杂草都有半人多高,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在其间,凄凉中透着一丝绚丽。坟地旁树林里,偶尔传来的老鸦叫声,让这里更显得肃穆、冷清……
赵兴东已经记不太清楚哪座坟头是属于母亲的(墓碑通常在周年时立,不过穷苦大众,也就只有在心里,给先人们立块碑的能力),费了半天心思,才找到那个在别人眼里的女疯子的坟。立在墓前,他显得很平静,想着这个并不疼爱他,他也不敬爱的女人,想着她的偏执,想着她的坚强……
许久,赵兴东叹了口气,上前将坟上的杂草清理了一翻,从布兜里拿出个白面馍,放到墓顶,又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起身离去。
赵兴东对母亲没有多少感情,奶奶和父亲健在的时候,赵兴东只感觉到母亲对弟弟妹妹们的疼爱,这让他嫉妒;而母亲把弟弟妹妹送人时,让他心凉;母亲开始捡废纸时,他也抱着希望,可母亲整整十年的坚持,最终让他厌烦;最后和彻底疯掉的母亲相处的半年,让他无奈。要说他对奶奶的感情,远远超过母亲,可是奶奶的坟头,已经被十几年的岁月平整消失了,他已经找不着了,村里人也说不清了,也只有在他的心里祭奠一下了。
赵兴东边走边想,年底就是母亲的周年了,虽说自己不过母亲的周年,村里人也不会笑话自己,毕竟是孤儿,哪有能力过事呢。(过事——就是指操办结婚、丧葬、做寿、周年祭奠、三年祭奠等事情,通常要大宴亲朋,耗资甚重。)可他心里明白,过事都是过给活人看的,过的越隆重、越气派、越奢侈,大家才会对过事的那家人另眼相看,如果不过事,或者过事时太寒酸,是会被人瞧不起的。赵兴东在村里压抑了十一年,需要出口气,需要为自己赵家正名,尽管在去年父亲平反时,他也在村里“反攻倒算”过,不过他知道那是小孩子的瞎闹,不会被人看起的。所以他要给母亲过个排场的周年,要彻底恢复童年时,在村民面前拥有过的优越感。因此,这次回来赵兴东不仅是要搞收鸡蛋的事,还要筹划这事。
进了村子后,赵兴东带着招牌式的微笑,和乡亲父老们打着招呼,逗着光着屁股满地跑的半大孩子,浑身上下透着一种亲切、一种优雅、一种大度,这种村民们没见过的气质,使的很多乡党围着他,给他介绍村里半年来的变化……
赵兴东尽管觉得这种变化,实在不值一提,可还是满脸愉悦的应承着,等走到支书家门口,围着的众人才纷纷散去。支书早被喧闹的人声所吸引,来到了院子门口,见是送他话匣子的赵兴东,忙笑着招呼他进屋坐。
支书家正屋三间,偏房两间,院子十分宽敞,整个桩基地是四间桩子的大桩基,足有一亩半地大小。中间那间正屋用作堂屋,算是待客的地方,东屋支书两口住,西屋闺女住。前院西边有两间偏房,一间儿子住,儿子年初当兵去了,房子现在空着。另一间做库房,堆着家里的粮食和杂物。偏房对面是个没装门窗的简易厨房,里面垒着灶台。正房后面自然是后院,有茅房和猪圈。本来还养着猪,不过姑娘上班后,嫌臭,现在也不养了。
三间正屋原来都是土房,后来在外墙上箍了砖,算是半土木、半砖木的房子;厢房却是一砖到顶的瓦房,是正宗的砖木结构,这是给儿子结婚预备的新房。至于厨房、茅房、猪圈都是土房。仅从建筑上看,支书一家绝对是中原地区的殷实户。
两人进了堂屋后,在屋正中的八仙桌两边坐下,八仙桌挨着后墙放着,墙上是毛主席与华主席两人的画像,八仙桌上放着话匣子,和一个缺胳膊少腿的茶壶。茶盘倒是崭新的搪瓷盘子,上面摆了四个玻璃杯子,不过大小形状各异。支书的婆娘拿了一个最大的玻璃杯子,然后抱着茶壶给客人倒了一杯凉茶,殷勤的招呼着。(茶壶把断了,可不得抱着。)
赵兴东发现支书家除了这个新搪瓷盘子,倒和年前没什么变化。支书却发现赵兴东和半年前已经很不相同了。
………………………………………………………………………………………………………
作者语:1.当了两年多太监,(实际累计起来是入宫35个月),俺的写作意图也发生了变化(看来这太监当的不仅是在生理,现在连心理都扭曲了)。
2.原来为钱为名写书,整天想着点击率,不够纯洁(仅指本人)。现在是为了啥写呢?主要是打发时间,顺带提高一下文笔(这半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了,写个几十个字的句子,都要组织半天)。
3.因为动机的改变,所以作案手法也就发生了变化。本书将脱离YY(意淫),向现实主义靠拢。
4.写作的初衷,倒没丝毫动摇,即试图展现复杂难测的人性。
5.谢谢支持俺的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