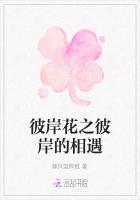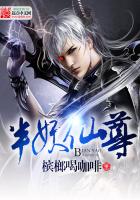对香菱的命运结局,始终伴随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从阅读心理来说,既为香菱躲过夏金桂的暗算而欣慰,又为夏金桂“施毒计自焚身”报应结果感到解气;从审美层面来说,为“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深感遗憾,它极大减损了悲剧的沉重感、震撼力。如果续作者遵循曹雪芹先生的最初构想,让香菱惨死在夏金桂的阴险、凶狠的手段之下,则契合了曹雪芹先生“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的原意,那将产生厚重的悲剧美学效果。
然而,《红楼梦》续作者为迎合读者中国式的阅读心理,把曹雪芹原先的构想完全推翻,另起炉灶,编排情节:先是在第八十五回安排薛蟠打死酒保张三,被拘押在监,腾挪时间、空间、情感,为夏金桂勾引薛蝌、陷害香菱进行创造条件,这一构想应该是很好的创意,是与曹雪芹原先设想相吻合的最好卯榫点,夏金桂嫁给薛蟠,就意味着香菱悲惨命运的开始,香菱生命的坐标轨迹,随着时间变量的延增,其遭受折磨的强度、深度也相应增加,直至生命结束。无论薛蟠在家,还是薛蟠被关押,都不会影响香菱最终命运的轨迹走向,如果说有影响的话,也只是影响香菱遭受折磨的强度、深度的振幅大小,影响香菱生命轨迹的长短。续作者选择薛蟠离家外出,在酒店打死酒保张三,被监禁拘押期间,夏金桂整治、折磨、陷害香菱,应该是更能体现夏金桂的狠毒、凶残,也符合“最毒莫过妇人心”的谚语,更符合当时的环境:薛蟠杀人在押,薛姨妈一心筹钱、托关系,疏通关节救儿子,无心关注生活琐事,她几乎与儿媳夏金桂互不来往,夏金桂及其丫环的信息也轻易传递不到薛姨妈耳朵里,在这种情形下,香菱就像任人宰割的羔羊,任凭夏金桂折磨、蹂躏,其惨死已在意料之中,也更加顺情合理。如果薛蟠在家,夏金桂折磨、蹂躏香菱,即使薛蟠不加以干涉,他会经常到薛姨妈处回话、商谈事情,薛蟠无遮拦的嘴,会无意中透漏香菱与夏金桂的紧张关系,或者香菱如何可气、可恨,金桂如何惩治香菱等言语。如果实在过分,薛姨妈会出来干涉,香菱被蹂躏致死,就得想出更加适合的环境和理由。令人惋惜的是,续作者没有珍惜已有的奇思妙想,而是中途改道易辙,在金桂设计毒害香菱的过程中,又画蛇添足般的添加了宝蟾偷偷将两碗汤更换位置的情节,导演了夏金桂害人不成反害己,最终落得“施毒计自焚身”的悲惨结局,香菱则阴差阳错逃脱金桂的暗算,保住了性命。把一幅美好绝伦的裸体油画,续作者给她画上了内裤、胸罩,令人哭笑不得。如果更深层次解读续作,就会更加清楚续作者对香菱生命轨迹的构想,他不是没有领会曹雪芹“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的创作构想,也不是没有把控好与曹先生创意的契合点,而是完全颠覆曹雪芹先生的创作架构,按照自己的审美定式,迎合读者心灵祈求的圆满结局,在金桂与香菱互换生死之后,又在第九十七回安排薛家上下疏通关节,把薛蟠打死张三定为误杀,为薛蟠出狱铺平道路;为了能够让薛蟠出狱,与香菱结为夫妻,完成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在第一百一十九回又设计了皇帝大赦天下,薛蟠赎罪出狱。出狱后,他对自己先前的言行、秉性进行了彻底反省,立志痛改前非,由薛姨妈提议,薛蟠决定将香菱扶正的情节。就情节本身来说,前因后果互有照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因果链,可以称得上是“完美”。但是,光鲜亮丽的表层包裹着粗糙暗淡的实质,沉重的表象遮掩不住内质的轻飘。虽然形式是一个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但就审美效果而言,却是索然寡味,这不能不说是创作中的败笔。
“注释1”甄英莲,即“真应怜”。“甄”谐音“真”,“英莲”谐音“应怜”。
“注释2”霍启:即“祸起”,预示灾难从此始起。
“注释3”冯冤:即“逢冤”,遭遇冤枉。
“注释4”甲戌双行夹批:二字仍从“莲”上起来,盖“英莲”者,“应怜”也,“香菱”者亦“相怜”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莲"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58页。
“注释5”农村方言,此处指为达到某种目的纠缠不休。
“注释6”《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375~376页。
“注释7”《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620页。
§§文静端庄的薛宝钗
——判词: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曲词:
[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那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