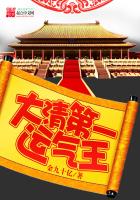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他生于黄巾起义不久,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十三岁之前,一直跟随其父于军旅之中,亲历曹操的雄才大略与丰功伟绩,也在东西南北的游历中丰富了见识。他自幼聪颖好学,又有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十岁就能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又爱好民间文学,熟识乐府与俳优小说。他在兄弟中才能最为突出,起初曹操以为他是“最可定大事”的人。十三至二十九岁期间,他定居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城,那是他一生中最为舒适愉快的时期。作为贵公子,依恃着曹操的宠爱,凭借着自己的高才,生活也相对安定,文人也比较集中,过着斗鸡走马、游宴驰猎的贵游生活。吟诗作赋,多为游宴应酬文字;浅唱蹈舞,主在嬉戏娱乐。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对曹植等兄弟常怀猜忌,并连续不断地进行迫害,先杀害了他的党羽丁翼兄弟,又经常改换他的封地,并派人严加看管,名为王侯实同囚犯。整天以酒为伴,以泪洗面,作诗以抒愤,发文以见志,在抑郁中度过了自己最后的生命旅程。他最后的封号是陈王,死后谥曰思,因此后人称之为陈思王。曹植虽不乐以文学创作名世,但是历史上他却因作品数量之多与质量之高,成为建安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家,有集三十卷。
高才。曹植的高才,在当时以及后世都是极著名的。“才高八斗”的称誉,藐视世人的谢灵运的倾心钦佩,唐宋以下许多大诗人的远慕,这些足见其“高才”之光。今人徐公持氏言曹植“集古今智慧、文武才能、雅俗技巧于一身,不诬‘天人’之称。”确实,曹植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虽然不一定文武兼备。以其文学才能而言,他的诗、赋、文各体均为建安成就最高者,也超越了前人。他的诗数量大(据统计有九十多首),无论其前还是同代人都没有过如此大量写诗的;质量高,其艺术成就更是对我国诗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说曹操、曹丕主要在运用乐府这种形式抒情写意,而曹植乐府与“古诗”,民歌与文人诗兼长,是乐府文人化与古诗通俗化的重要实践者。他的诗,主要是四言与五言,但还探索性地创作了楚辞体、六言体、三七言体、六五言体以及各种杂言体诗。曹植的诗歌不仅体式多样,题材也丰富,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各方面在他手下都是诗歌的好材料,这种拓展就有大才的气度。曹植也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辞赋作家,五十多篇的数量,是整个魏晋南北朝作家中现存作品最多的。无论对辞赋题材、语言锤炼、修辞手法等等都有很大的拓展与提高。曹植的文,描写、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灵动自如,辞采丰茂,气势宏大,情真意切。他的诗、赋、文都是建安第一好手。曹植还精通音律,他的许多乐府诗都是自度曲。能歌能舞,能雅能俗,经籍典故随口而出,通民间俚曲随乐而歌。况且他敏捷天纵,精警的作品顷刻而成,胜如宿构。
他的高才,获得了曹操的青睐,几度欲立之为太子;也得到了文人雅士的倾心,多有为之丧命。他的文采风流,称名于当世,驰誉于千古,成就了他建安风骨最杰出的作家,也使得他轻忽社会实务,疏于精思熟虑,因此在传统的功业方面不可能有所建树,以致为此抱憾终生。
纯情。曹植是纯情的文学家。他的情犹如赤子孩童,天真无邪,纯洁无瑕,没有一点社会污染。他眼中心中,是非善恶截然两极,判然分明:“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杂诗》)他后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明明是他亲兄迫害所致,身边的仆人属官公然对他大不敬,他还以为是这些人品行低劣,他与兄长感情疏远也以为是这些人从中作梗,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兄长会如此不容他(《赠白马王彪》)。他品评人物,也总是觉得别人都是纯洁无垢:“如冰之清,如玉之洁。”(《光禄大夫荀侯誺》)他称颂的鸟也都是纯净的:“惟夫蝉之清素兮,潜厥类乎太阴。”“皎皎贞素,侔夷节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蝉赋》)“饥食苕华,渴饮清露。异于俦匹,众鸟是惊。”(《鹊》)“嗟皓丽之素鸟兮,含奇气之淑祥。”(《白鹤赋》)因为他纯情,因此感情特别丰富细腻。他对妇女寄予深挚的同情。《弃妇篇》对无法把握自己命运以至于无依无靠的弃妇表达了真挚的同情;《出妇赋》以一个被另求新欢的丈夫中途抛弃的妇女控诉无情的不终;《闺情》《静思赋》等,替幽居女子抒愤;《七哀诗》代替思妇抒怨发叹;《妾薄命》更是以民间女子身份抨击魏明帝大量征发民间少女以供荒淫生活的事实。这种同情之作,在妇女题材比较多的时代也是很突出的。他对幼儿也充满感情,《行女哀辞》悼念不满周岁的女儿,《金瓠哀辞》悲一岁有余的首女,《仲雍哀辞》悼念“三月而生,五月而亡”的太子之仲子。作为贵公子,曹植还是真诚同情普通百姓悲苦生活的文人,《泰山梁甫行》描述了边海百姓的惨痛生活:“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以齐地的民歌形式生动表现了百姓因徭役繁重而不敢家居,只得逃入山林,过着禽兽一般生活。这样的作品,在文人中是很难得的。曹植的感情还给了自然界的虫鸟:“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挂微躯之轻翼兮,忽颓落而离群。旅暗惊而鸣远兮,徒矫首而莫闻。甘充君之下厨。膏函牛之鼎镬。”他的自序说:“余游于玄武陂中,有雁离缴,不能复飞,顾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怜而赋焉!”可见他确实是如佛家的哀怜天下所有生灵,对一只受伤的雁给予了“鸟道主义”同情与爱护。真是情之博,播于禽兽!
曹植的感情是真诚的,纯净的。他的“情”没有世俗气,对所有人,甚至对所有生灵都倾之以真情。他的情没有政治色彩和社会等级观念,无论是上流社会的人还是社会底层的人,对他来说都是同样的“人”,真正做到了博爱!这种博爱是可贵的,可爱的,是文学家纯真的情感。是魏晋名士“多情”特质的体现,但是也是造成曹植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自己感情真纯,心地纯洁,自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与他一般,兄弟是如此,朋友是如此,芸芸众生都是如此。我们在看到曹丕的间谍诬陷曹植以后,他作的自我检查,那种诚挚的反省与自责,有莫名的悲哀,明明是迫害,他还是对自己的言行作了深深的忏悔,根本不知原委。以这样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作家自然是伟大的,但是要在群魔乱舞,善恶并存的社会“混”就不太灵光了,更不要说在政治舞台上去表演了!
使性。曹植的行为举止一任自己个性,这也是非常突出的。他非常厌恶礼教,因为礼教就是用各种规范制度限制人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人的个性。他听到别人告诉他一个故事,一位男子喜欢邻家姑娘,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媒人,不成“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被有媒人的其他人娶走。曹植于是感而赋焉:“思同游而无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去君子之清宇,归小人之蓬庐。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拘!”“妾秽宗之陋女,蒙日月之余辉。委薄躯于贵戚,奉君子之裳衣。”尽管作品因残缺而难得其意,但是他反对礼教束缚,提倡婚姻自由的崇尚个性精神还是很明白的。他也崇尚超俗境界。“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求。棲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隐柔桑之稠叶兮,快闲居而遁暑。”(《蝉赋》)那种离群超俗之志,以蝉而出。他借鰕鳝出游,“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鰕鳝篇》)抨击社会上到处都是“势利”的庸俗之人。然而,社会众生唯利是图确也是其普遍现象,如他这样心纯情洁之人,自然难以适应社会生活了。他还无度,行为任性而有,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曹操规定,夜间不允许开宫门出入,但是他就不管,偏在夜里出去,以致曹操杀门人以立威。他饮酒无度,以致曹操欲任以重任而罢休。他对人毫无“防人之心”,在立太子的生死大战中,他根本没有“竞争意识”,一任别人从自己手中夺去了至尊位置,而毫无觉察。曹操在世期间,从无后虑,以致自己后来处处受窘;受窘时候也没有思虑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一味怪罪眼前的随从。他本来思想简单,心地纯洁,再任性而为,其严重后果不难想象。
曹植的使性,是相当彻底的,是有力度的,刚性的。屈原作有《橘颂》以明志,曹植也作有《橘赋》以明性:“禀太阳之烈气,嘉杲日之休光。体天然之素分,不迁徙于殊方。播万里而遥植,列铜爵之园庭。背山川之暖气,处玄朔之肃清。”这是一个与世俗相异,具刚烈性情,坚定不移的形象。他的《鶡赋》塑造了这样的形象:“美遐圻之伟鸟,生太行之嵒阻。体贞刚之烈性,亮乾德之所辅。”“甘沈陨而重辱,有节士之仪矩。降居檀泽,高处保岑。游不同岭,棲必异林。”坚贞刚烈,不同流俗,而且“期于必死”。这样一种善斗又置生死于度外的猛禽,不是曹植那坚持自己个性,置利害生死于不顾的自我写照吗?他“履先生之正路,岂淫径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九愁赋》)他决不愿意为了利而牺牲自己的正气,决不愿意为了避免责罚而低声下气,他的使性有着自己的人生原则,有着自己的人格准则!
曹植的这种个性及其坚定的表现,在魏晋名士的人格史上具有很高的示范意义。他的这种精神以及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正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体现,使建安文学在曹操之后多了许多刚烈之气,坚贞之情,钟嵘言其“骨气奇高”的“建安之杰”,良有以也!
简放。曹植的简易疏放也是很突出的,《三国志》本传言其“性简易,不治威仪”,“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所谓的简易疏放,其实与其纯情与使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言行处事一任自己好恶,不作细究深思,与世俗的“三思而行”,计虑利害得失不同。曹植的简放,与其贵公子的地位与身份有关,也与他逸群之才有关,与当时社会风气关系也很大。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纯情与使性的性格所决定的。他的简放表现很多,如无节制地饮酒。建安文人饮酒成风,这是历史事实,有曹操的禁酒之令与孔融的言行等等为证。作为曹氏集团的中心人物之一,甚至可能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人物,饮酒无度显然是不妥当的,不应该的。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所围,曹操欲以曹植为南中郎将领兵救曹仁,可是“植醉不能行受命,于是悔而罢之。”(《三国志》本传)饮酒无度以致他基本不能担当重任,在政治上完全是个无用之人。这就决定了他政治前途暗淡。此次醉酒,据裴松之注所引《魏氏春秋》当与曹丕有关:“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招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这样更可见曹植性格的简放已经到了毫无头脑的地步。他也参与斗鸡等浮华勾当。建安后期至魏明帝时期,魏国境内还算太平,社会上流行斗鸡,狂饮,清谈等等所谓“浮华”风气,曹植肯定也是其中一员。他作有《斗鸡》一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斗鸡情景,《鹖赋》虽不是着重描写斗鸡的,但是对飞禽的搏斗过程写得淋漓尽致,可以相见他对这个玩意儿的熟识。他喜欢娱游,几个或者一大群文人,带上一些侍从,或饮宴,或郊游,或嬉戏,随兴所至,有时还兴犹未尽地写诗作文。他还喜欢各种民间俚曲俗舞琐谈,认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与杨德祖书》)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文学美学观念。他的乐府诗,有许多就是当时的民间歌曲,自己所拟也颇具民歌风味,至于喜闻民间的“小说”俚语,也是有史可征的。这些表现,我们可以称之为兴趣广泛,也可以看做观念解放没有贵族陋气,从性格来说,实际上就是简易疏放,随行随性,没有人为的节制与限制。这种行为方式,对后代名士影响很大,放达或放诞是魏晋名士的基本特征之一。
壮志。曹植一生念念不忘建功立业,至死未变,这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这固然有时代的原因。建安直承东汉,汉末名士忘身救汉的精神与之距离不远;儒家“三不朽”思想对文人的影响依然存在;曹植的前辈和同辈都在努力建立不朽的功业。这些应该是曹植立志不朽的外部原因。其自身的性格也是重要因素。他具有刚烈不易的个性,因此当他早年立下宏愿,在百折不挠的个性力量支持下,很难因时势的变化而改易。比较清楚地表达他志向的是著名的《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未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对这一段言论,人们历来都很重视,只是理解有相当的不同。其实,他首先是因赠送自己的辞赋作品给杨修看而发的议论,因此一定程度上有谦虚的意味在。其次,曹植是站在“位为藩侯”的立场,以曹氏政权的中心人物之一的责任与义务来谈自己的志向的,因此将为国家、为曹氏政权建立实际的不朽功勋置于首位应该是恰如其分的。用今天的话语来说,身在其位当谋其政,当为其事。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曹植纯情天真的表现。当然,他把“辞赋”这样的文学创作看做远不如建功立业那样重要,虽说有时代的局限,但今天看来毕竟是观念上的保守。
曹植的志向高远。他未冠时所作的《登台赋》云:“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将齐桓公、汉文帝这样的史有定论的伟人都不足其观,可见其胸襟眼界之伟。从他所写的大量对古代帝王赞颂之作看,他眼中的盛世应该是传说中的圣明之君的统治。“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因以蔑《韶》《夏》矣!”(《与陈琳书》)显然比儒家的文武世界还要高远。尤其令人感怀的是曹植对自己志向的持之以恒,坚定不移。他先后写过《求自试表》《自试表》,在曹丕、曹叡父子当政期间反复陈述自己希望一展宏图的苦心,还以《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等委婉曲折的象征手法表达自己的深衷。至于如《白马篇》这样用形象方式描写自己心中的理想人格的篇什就更多。曹植的内心世界,始终欲在可以铭刻金石的功业方面有所作为,不愿仅仅食王侯之禄而无尺寸之功,当然也不满意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家名世,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功业,因为他对文学创作只是喜爱而已:“仆少好为文章”(《与杨德祖书》),并没有当做自己的理想事业。问题在于,曹植的理想虽然有益于世,也合乎情理,但是他自己并不认识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现理想的主客观条件,而曹植显然缺乏这方面必需的条件。他是否具有这样的才能暂且不说,他不具备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基本素质,当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前人所论已多,尤其是曹操在世时候有实践理想的客观条件,但他没有也不会抓住机会,而完全失去可能性的时候,他倒是想去建功立业了,这样不识时务的人,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吗?
无论对曹植的远大而坚定的志向作何评价,他具有儒家的“不朽”之念是肯定的,这似乎与后来的名士大不相同。实际上,后来的名士们虽然追求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但是对苍生,对家族的责任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全然没有,而是因时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异。
好美。《三国志》本传的话很容易让人发生误解:“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靡。”视此,似乎曹植不爱华美。对此,应该有所辨析。建安年间,社会经济很长一段时间相当艰难,对曹魏来说,军事第一。此间,曹操严禁华艳,曹植的妻子曾因穿着华丽而被杀;又颁布禁酒之令。这些就是战时生活决定的。到建安后期,战事不那么频繁了,中原也渐渐恢复元气了,邺城的生活渐现浮华。这前后是很难同日而语的。《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敷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颂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焉?’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誺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亢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这一段文字所述之事,历来都以显示曹植非凡之才的例证。其实,事例本身具有多元信息,因此我们解读时还可以从此看出曹植爱好华美的个性。大热天敷粉,其粉饰的美化自不待言。曹植的敷粉,在建安时代属于较早的,后面要到正始名士时期,才有比较多的敷粉现象。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曹植几乎竭其所能,既有武夫所为之能,更有文人所长之才。有雅才,也有俗能。有历史评论,也有现实政事。有文赋,也有兵法。这样的表演,以美学标准衡之:华靡也!恰如文学表现中的“赋”法,极度地铺张扬厉。文学史上,曹植的作品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诗品》卷上)无论是“词采华茂”还是“体被文质”都是华美的同义词。曹植诗歌的语言华美,音律和谐,对偶整丽,时有暗合格律者,这些现象不可能纯属偶然,应该也有他自己努力创造追求的因素在。至于他的散文,相当接近后来的以华丽为主要特征的骈文,也明显可以看出他用功之处。
曹植爱好甚至可以说追求华美的审美意识,在当时属于少数派,但是到西晋就成为时代风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付之以行为,并成为人格特征的,那就是魏晋名士的风度。曹植的人格形象,后代的名士们相当仰慕,因此其影响之大就不待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