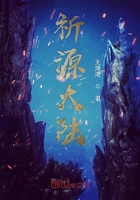那个夏天,19岁的石青遭遇爱情。
高考的第一天中午,石青午觉起来,出门赶考。他家在桂花镇的深处,家的旁边有许多邻居的家,除了房子还是房子,其中有一条长而窄的巷道通向外面的圩场。
石青出了巷道,眼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午后的太阳很大,白花花的阳光晃了他的眼。虽然是圩日子,但赶圩的人掰着手指头也可以数清楚,天气烤得买的卖的全都没精打采。石青买了一串酸萝卜,边吃边走去赶考。
考场很近,就在圩场旁边。石青手上的酸萝卜还没有吃完,人已经走进了临时作考场的小学大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人头攒动,比圩场热闹多了,大凡认识几个汉字的小青年都赶来参加这场游戏了。石青像一条鱼,在散发着汗臭的人群中游来游去。下午考数学,他需要借李四眼的脑袋用用。李四眼脖子细得像根葱,却顶着一只大西瓜似的脑袋,大蒜鼻上架着一副黑边塑料框眼镜。李四眼是个地主崽,脑水很足,数理化随便提哪壶都开。上午考语文,坐在石青前面的李四眼埋头苦干,答题答得有滋有味,对他屡次用钢笔戳脊背的暗示置之不理,第一个交了卷,临出考场还冲石青做了个鬼脸,差点让石青当场吐血。他找李四眼,就是要让李四眼明白,要是再名堂多,他石青的拳头不是吃素的,这个忙帮也要帮,不帮也要帮。石青找来找去,拨开了无数颗人头,什么样的脑袋都见到了,就是不见李四眼的脑袋,等一下进了考场再交代,那肯定是作弊,怕是用不着考了。石青走到他参考的那个教室,蹲在一棵桂花树下候着。距离考试的时间还早,石青相信自己的耐心也足够。只要李四眼一出现,李四眼的脑袋就会像读小学的时候一样,吃上五颗结实的“板栗”。等啊等,该死的李四眼就是不来。石青的手痒了,拿桂花树出气,摇得满树叶子乱落。一个教师模样的汉子过来吆喝,石青赶紧跑到教室的另外一面躲了。
事情发生了。杨柳,一个女声喊道。哎,一个女声应道。石青茫然抬头,他看到了什么?一个美少女。她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正跟几个女伴说着话。他看见她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缘故,她也抬眼望着他。他看到她的眼里一道亮光闪过,胸口立即有一种中箭的感觉,接着那种奇妙的酥麻迅速蔓延到了全身,如同小时侯偷酒喝醉的快乐。他想完了完了,这高考真用不着考了,还是回白岩村住茅房当知青好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个该死的时候会产生这种该死的感觉。在这以前,除了母亲和妹妹,他讨嫌所有的女人。有两个住他隔壁的同队女知青争相邀宠,一个帮他洗衣服,另一个必定给他煮饭吃。他一看到那两个丰满女人,浑身全是鸡皮疙瘩。那俩女人,一个口臭,一个狐臭,却偏偏往他身上凑,更是让他五官堵塞,几次差点昏死过去。有一天半夜,其中一个翻墙进来,爬到了他床上,吓得他一阵惨叫,夺门而逃。第二天半夜,另外一个也翻墙进来,爬到了他床上,再次吓得他一阵惨叫,夺门而逃。第三天晚上,他听到隔壁咯咯乱笑,两女人扯平了,和好了。然后,就是他的不是了,在队里落了个“秃尾猫”的坏名。
在这个夏天的中午,一个少女的目光穿过岁月,落在了石青长满青春痘的脸上。短暂的目光抚摩过后,石青的爱情被唤醒了。症状是石青傻了呆了,定定站着,他面前的人都已走光,少女不见了,考试的钟声响了又响,他还定在那里傻着呆着,全不是往日的石青。要不是李四眼叫了他几声,他可能会从夏天一直站到秋天,不用说考试了。后来,考试是考试了,可他身在考场,心却在梦游。他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答了些什么,一切都在恍惚中,一切都在梦中。接下来的几科也是这样,完全不在正常状态。石青草草考完最后一科,慌忙出来,把笔丢进了教室旁边的水塘,然后守在小学门口等那美少女出现。
考试结束了,考生们像刚出笼的小鸟,扑棱扑棱全走光了,但美少女并没有在他的眼里出现。有好几次,他以为就是那人了,可睁大了眼一看,却是另外一个人。他走进小学操场,四处张望了一阵,操场上一片空旷,没有一个人。又在看到美少女的地方站了小半天,也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病,摸摸额头晃晃脑袋,没有感觉有什么不正常。于是,他重新走回长长的巷道,走回镇子深处的家,躺在床上,从天光到天黑,又从天黑到天光,张着一对熊猫眼,19年以来第一次失眠,仅仅为了那美少女的一个眼神。
石青多次穿过巷道,走到小学操场上,看看那美少女是不是会再次出现,是不是能够再看他一眼,但每一次都以从原路返回结束。每一次走出巷道他满怀希望,每一次走进巷道他就想哭。他不明白这是不是失恋,也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只有一个想法,找到那美少女。但他又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到了美少女,他还是不能确定,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他的眼睛曾经给了他明白无误的记忆。他躺在昏暗的床上,望着渐渐发白的窗户,回忆着几天前的那段往事,以及往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那包裹在红衣青裤里的婀娜身段,那满月一样明亮的脸庞,那传情达意的双眸,以及那鲜花般的微笑,如同看了几十遍的老电影,在他脑海里连续不断地播放。这是真的,至少曾经是真的,即使是一个梦,那这个梦比真的还真。
简单地说,杨柳确有其人,是兴隆乡卫生院的护士。好了,足够了,石青一边说着一边背着一只洗得发白的黄挎包,包里放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