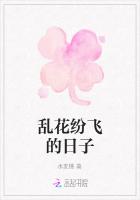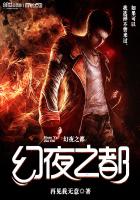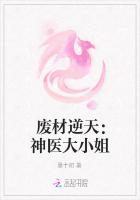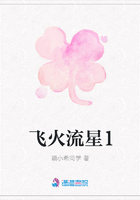写完最后一章,天边露出了鱼肚白,掩卷长思,欲罢不能。
动笔写这本书之初,我心中充满了惶恐和忐忑。百万三峡移民,各种人物、故事浩如烟海,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剪裁、取舍,从什么角度切入却费思量,颇踌躇。
一个移民的搬迁前后就有一个不短的故事,一个移民家庭的悲欢离合足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开始,我构思写一个移民家庭的“四世同堂”,12口人,重庆和湖北都有人物鲜活、个性鲜明的生活原型。
从写他们在峡江河谷半原始状态的生活开始,到全部搬迁到省外安家落户结束,期许以客观真实的故事反映三峡百万移民这一历史性的变迁。应该说,落一叶而知秋,用“一滴水见太阳”的文学表现手法,写出一个点、面或许更有助于深刻表现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
但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四世同堂”,就真能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三峡百万移民这场历史大变革吗?经过思考,我发现这个极富沧桑感的感人故事,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中,只是一个真实的局部和一个侧面,但不是我心中沉淀已久的“全部”。因此,我否定了这个令我至今仍难以释怀的方案。
浩大的三峡工程就像一个辉煌的“迷宫”,我不止一次从容地走进去领略奇光异彩,但走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处于一种不理智、不太清醒的状态。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出现这种困惑、怅惘和迷茫,是很想把三峡的事说个清楚,越想说清楚就越说不清楚。因为,你在三峡看到的“所有”都只是三峡的一个局部,不可能全知全觉。这,就是产生迷糊状态的症结所在。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四川省作家班的学习,作家们曾围绕“盆地意识”舌剑唇枪,展开过激烈的大讨论。
以写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庄园而轰动全国的著名作家陈之光先生,在讲课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成语叫井底之蛙,四川人有一句俗话叫“顶起草帽就以为是天”。巴蜀地区近年来出不了大作家,出不了扛鼎之作,就是根深蒂固的“盆地意识”在脑海里作祟。落后的意识不仅制约了盆地经济的发展,也禁锢了文化人的思维。观念上的陈旧,视野上的局限,必然导致经济文化的落后。
三峡夔门,是“四川盆地”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也是“盆地意识”的一个心理标志。
走出夔门,拓展视野,才容易突破“盆地意识”的束缚。名满中华的当代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巴蜀大地就有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走出了夔门?
古代有李白、苏东坡、杜甫、白居易等,哪一个不是走出了夔门?
当代有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李颉人、何其芳、马识途等等,这些作家中,又有哪一个不是早年就冲出了夔门?
只有走出夔门,摈弃盆地意识,突破峡谷的封锁,挣脱夔门的束缚,最后才能走向浩瀚无垠的大海!
陈之光先生的话一直在我脑际回旋……
这些年来,陈腐的观念、狭窄的思维、偏于一隅的地域视野、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自始至终统治着我的大脑,支配着我的行为。就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大胆走出夔门。
一个地处“夔门内”的人,一个“体制内”思维的人,在这种“双重身份”制约之下的我,能写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峡百万移民吗?即或能凑成篇章,又能“顺乎时代之潮流,合乎民众之需要”吗?
三峡工程防洪标准是“千年一遇”,对文学创作来讲,百万移民这个浩大的工程也是一个“千年难遇”的好题材。作为在长江边生活了一辈子的我,不写出一部作品,就愧对“一川流水,半江渔火”。于是,我决定扬长避短,用长篇报告文学的样式,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重点采写三峡移民之后的生存状态,写移民资金的幕后故事,写各级政府和移民工作者的殚精竭虑,写自己在移民工作中的经历和感悟。因此在本书中,为节省篇幅,就没有涉及三峡工程的起源、论证和决策方面的诸多内容。
本书主要是根据我在移民部门6年多“秘密卧底”体验生活的工作笔记和后来补充采访而写成,前后竟历经10年……
在这部书写作采访过程中,我得到了鄂渝两省市库区移民系统的大力支持,这是我首先要真诚感谢的一群从事着特殊工作的人。他们是王显刚、欧会书、周金华、阮利民、徐江、文立燕、沈来燕、彭亮、刘渝春、区阳祖辉、李奎、李善联、郎诚、杜华山、郭雪梅、严俸勇、周一川、晏承全、柯延斌、汪元良、荣以红、许腾芳、马小芹、刘磊等。
特别要感谢******三峡办公室的漆林、宋原生、******、乔英红和重庆市政府顾问甘宇平等同志,他们在百忙之中对本书的部分章节做了极为认真的推敲、修改、批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他们这种对历史、事实负责的态度使我感动不已。移民专家陈联德通读本书初稿,并对其中章节数次做了极为认真的修改。著名文学批评家、作家蓝锡麟、罗中福、王青山、黄济人、刘阳、火岛、李显福、张放、杨泥、傅小渝、熊建成、姚念兵等人,都对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修改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何事忠、易飞先、李廷勇、汪俊、缪超群、陈扬、雷平、陈荑茁、牟丰京、黄平、杨一等人,他们对本书的采访写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此,我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我采用了“三峡移民精神报告团”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本书对移民干部中退居二线的着墨较多,在职的着墨就少一些,个中缘由,想必读者诸君都能理解。此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前清四川移民史》、《巴蜀移民史》以及部分省市传媒记录的史料,在此向作者和有关支持单位一一表示感谢。
我国有8万多座水库,产生水库移民2300万人左右,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据。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产生的水库移民都不会有如此之众。因此,说我国是一个水库移民大国并不为过。如何安置好数以千万计的水库移民,让他们安心、安稳、安泰,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种长期的考验……
千秋万代事,民治为先,安民为天!
三峡水已蓄到了156米,库区沿江所有的港口码头、县城、集镇都修葺一新,一个个移民村,一幢幢移民房,移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从巫山、云阳、奉节、开县、丰都、秭归等全淹县城来看,竟然没有一幢是旧房子,这种现象在全国罕见。杜甫倘若重回三峡,定有“广厦千万间,寒士俱欢颜”的感慨。
库区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应该看到,库区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基础设施落后,产业支撑不足,经济发展缓慢,就业矛盾突出,社会事业严重滞后,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等异常艰巨的问题已日渐显现出来。看来,“百万移民世界级难题的最终破解还任重道远;广大移民安稳致富目标的全面实现还任重道远;三峡库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任重道远”。
三峡的早晨苏醒了,江流仍在缓慢而沉重地流动,树丛中小鸟啾啾地叫着,峡江新的一天又这样开始了……
我伸了伸懒腰,正欲掩卷,一位走出夔门的老人说过的一段话,突然在我耳旁鸣响起来:“我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擦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right岳非丘
right2007年1月于长江三峡库区